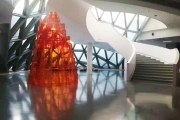我的全部猜疑都在追赶那匹远去的白马,我的全部困惑就像躺着的男人那样充满睡意。我所熟悉的苏新平突然变得陌生起来,仿佛心理相距得无限遥远。
顿时我又有了另一种感觉。
那匹白马一往无前地走向神秘,而那个男人只有梦境。也许我总是负担着猜疑和多思的几分沉重,我的疲惫我的困惑我的睡意才促成了我的梦境。梦境有时是清醒的极端反动。我却在梦中自由自在,但也随时躲避瞬间的惊吓,担心被什么唤醒。这很可能是理论癖与思辨癖的最明确的缩影与象征。而画家毕竟是画家,无须在梦中就可以自由自在地走向神秘。
我的感觉还在继续跳舞。显然这是一种精神的自我运动,无需画家应声而起。我总觉得这画中有值得劳神去猜度的内涵,那神秘的引力时时在起作用。这画蓦地让我觉得与实际的画家本人更加隔膜,好像苏新平一下子成了外星人,我们又偶然相会于一个互不熟稔的新星座。
我开始读他的画论。
"在《躺着的男人与远去的白马》一画中,一匹缓慢走向画面深处的马象征着蒙古族牧民那与四时并运的生活或劳动,无尽延伸的马桩乃是其历程的标志,画面下方躺着的人象征着无为的自然意识,思辨在睡,梦境亦不存在,人与天地的冥合却是人自身的状态,这不免有些伤感。"原位的苏新平努力要说清他作画的初衷,像一个神话传说的原型在自我申述,要与任何变异的理解奋力抗争。事后作者也说:"我曾多次试图解释我的作品,结果我发现解释作品远比再画一幅要难得多。因为它根本就无法解释。"记得徐冰曾说过:"作品交给社会如同把生灵赶入市场,它已经不属于作者自己了,它属于所有与它接触的人。"作品问世后免不了一任人们作精神上的切割。我开篇的臆想历程就是如此。
不仅仅在这幅画里,在其它作品中也是如此:他所画的那些人让我想起恩斯特·卡西尔关于人是"符号的动物"的说法。客观地看,他创造的那些人本身已不具有对象自身的特点。但我还是对苏新平原意的申述感兴趣。"他们的大部分时光是在沉默寡言的孤寂状态中度过的,欢腾和奔放乃是这一大的心理状态的一种补偿和平衡。"其实,苏新平所表现的人的孤寂并不限于大草原上的孤寂,也含有工业文明中的城市的孤寂,也是潜在无形的他自己的孤寂。在苏新平的眼里,人是孤寂的符号!他所创造的白马,也有同样的意义,都是孤寂的符号。在这个意义上借用古代哲学家的话,那就是"白马非马"。
苏新平的画距离他那原位的表述已经相当远了。我能从他那潜伏着总结意识的话中强化这种感觉。"回顾这些年的作品,我发现几乎全都运用了强烈的光,最初并不是有意识地这样做,只觉得画面的效果很好看。后来多次去草原,渐渐发现强烈的阳光常常给我带来一种莫名其妙的错觉,有晕眩、有虚幻,世界是凝固的,是不真实的,随之而来的也有神秘和恐惧。一种体验一次次重复,慢慢就很自然地出现在画面中了,并且是有意识地去做了,也终于感到这正是我寻找的,是我需要的东西。"他把对草原人的客观认识只作为一种不重要的精神因素残留在作品中,更多的空位已被无形的自我意识充分占据。他与人的距离感是比较含蓄的,表面上的随和又使他的确定性格具有了矛盾。他那沉静的固执却在艺术创作上帮了他很大的忙,外观上的若有所思总是躲避挑剔的暗潮。
苏新平作品中最舒服的状态就是生命的静态。远去的白马的确不具有"去"的表现,却与四周的五个拴马桩具有对等的竖立感,这是一种有着"行走姿态"的静止感。这是一匹骏马的假象,那种"行走姿态"仿佛冻结在空气中。苏新平毫无表情地向我们讲了一个没有逻辑连带关系的故事,不知是他把其中的含义和寓意人为地抽空了,还是在主观表述一个线索的时候无意中又让最初的思路走失了。我很喜欢目前的格局,即使对画家一般的创作心理曾经感兴趣的我,也故意不去看这幅画的原始草图。
苏新平把他主观上的草原状态与城市状态以一种"心力"叠压在一起,当然这已远远超过了加法的魅力。更重要的是他把自我状态也实实在在地叠压在一起。他是一位来自内蒙古的青年画家,并非蒙古族,只不过是在静观经验过了的生活。另一方面,他是以城市状态在静观草原状态的,他又是以个人特有的沉静的固执去触碰生活中的孤独感。他故意把画的背景处理成虚假的空间,非常平面化,任其单纯而又冷凝。它是虚假的而又是无限广大的神秘空间。尽管人、马、桩都是作为有透视关系的实体来安置的,但斜射的光线也无法真的把我的直感全然拉回到与记忆相关的生活中。
在这幅画中,天、地、人、马都处在毫无干系的分裂状态。这并非是从传统的文学性和故事性角度来看的。偶然的物象并置于一个永远都不存在的空间里,但那却是画家真实的精神空间。按画家的说法大概是"想象空间"与"物质空间"的综合:
物质空间指人们的视觉所及的实景。当这种实景转化为绘画图像时,就产生了一些方法和规则,如近大远小、近实远虚等等,我国宋代画家郭熙提出的"三远"透视法也是一种观察方法。西方的焦点透视和中国的散点透视都是某种习惯性的规则和方法,我们不能判定哪一个更真实。想象空间是一个不受瞬间视觉观察所约束的再造空间。这种再造空间又分为主动的再造空间和被动的再造空间两种,被动的如梦境、幻觉等,主动的再造空间是人们有意拼装、虚构的空间。一般来说,绘画的空间离不开物质空间和想象空间,只是侧重点不同。没有物质空间不容易引起和刺激观者的想象,而没有想象空间的陌生和迷惑也会使物质
空间显得苍白乏力。
难怪作者有次说:"一天中我最喜欢黄昏,夕阳下的一切那么单纯、宁静、美好,万物是凝固的、永恒的。"总之,在对自己的总结中,画家还是很理性的,努力用概念来表达自己。他没有回避纯技术性的问题,如空间问题。也不在琐碎的地方浪费自己的注意力。在绘画上,表达简捷、单纯,而又明确,因此也没有必要向别人一再说:"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那个意思。"这方面的轻松,他自己感受得也十分明显。"我发现同自己交谈,同作品交谈是那样地随心所欲,既准确,又明白,于是我开始同每一笔、每条线、每个画面交谈了。"
但他的劳顿显然表现在为排遣孤独感而作的坚定的努力上。尽管他已深知欢腾和奔放是对于沉默寡言的孤寂状态的一种补偿和平衡,但他自己并没有在表层生活做出瞬间的"如火如荼"状。画中的精神状态仍是实际的他自己,野性与他隔水相望,爽朗的笑声并不在他心中脆响。他也"耐惯了孤寂"、"慢慢品味孤寂"。如果说他理解的蒙古族有"对自然的顺化意识"的一面,而他自己却对自我的孤寂有着十足的"顺化意识"。他努力去解答物质空间里的生活,其实是想解答想象空间中那个无形的自我。我可以体会到这样的感受:
我一直试图用我能理解的、我认为最适合自己口味最富表现力的形式来表达我的感受。通过审视自己最初的作品,通过长期摸索和积累,我似乎发现了自我,或者说发现了自己的艺术个性,我曾努力追求和尝试的各种形式可能就是今天这个样子。
我走了一个圆圈。我所熟悉的苏新平原来是一个正在寻找最适合自我表达方式的苏新平,而这个与我心理距离很远的陌生的苏新平才是真正的他。因此,他今天的作品就显示了更确定的意义。在天地人中,人若不能与天地沟通,那自然是很孤寂的。在具有孤独感的人群中,人与人之间不能沟通,则更强化了个体的孤寂。不知是谁说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大于人与猴子的差别。"这种暗潮正在流动,于是不知不觉就把"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归入古典的幻梦之中了。那个说"天是我的衣服,屋是我的裤子"的裸人是否就不孤独了呢?
白马走了,孤零零地走了,也许会消失于虚无之中。天、地、人,还有拴马桩都沉静得让人难以忍受,非常孤立地存在于一个再造空间中,又把苏新平要说的话说了个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