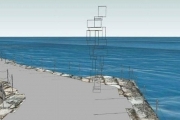从2006年12月25日开始,隋建国每天一次将一根细钢丝在汽车喷漆中蘸一下。他如此行动至今,油漆球的直径随着时间向未来的绵延而不断地一天天变大。他取名为《时间的形状》。这件关系到艺术家个人生命存在的作品,由于他本人每天的蘸漆行为而把物理时间对象化为在空间中的可见形式。对于隋建国而言,时间中的现在之维由他把细钢丝放入汽车喷漆中体现出来,就是放下去、拿起来的那一瞬间;其未来意味着:到未来某一天,当艺术家无法搬运钢丝喷漆球时,他作为个体生命与时间的关系也客观地由主动变成了被动。他将被动地拖入物理时间中完成蘸漆的行为。不过,即使如此,该行为的主观性依然存在,依然存在于他起初决定用后半生来完成该行为的生命意志中。该行为作品表明:人在现在所做出的任何决断不仅会影响其未来的生存,而且还将改变他在过去的生存。在象征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这沉重的钢丝球理解为在时间中的过去所形成的人类文化的传统,它很可能构成将来生存于现在之中的人类的巨大包袱或者祝福。同时,钢丝球直径的增长,也是过去越来越远离现在的明证,是时间在过去中过去的明证。其物理空间尺寸的大小,和隋建国这个个体生命的存在时间即年岁的长短相关。
从分析《时间的形状》中,我们发现时间以人在其中生成的事件为刻度。时间存在于事件中。根本就不存在没有任何生存论事件的时间。正因为如此,同样的“今天”或“现在”对于不同的人才产生了不同的意义。所有人都在相同的物理时间中,但他们在心理时间中的意识差异和由此生出的事件差异,而将同质的物理时间分割为属于不同心理意识生命主体的碎片。《时间的形状》所内含的艺术思想,在于它揭示了时间的生存论特质。其具体方式,乃是隋建国每天作为艺术家带着特定的生命情感把钢丝球蘸入汽车喷漆中的行为。由于后来形成的钢丝球与汽车喷漆本身的光滑性,它逐渐增长的形状基本上涂抹了艺术家本人每天怀有的任何具体的、丰富的生命情感差异。这也是时间的无情之一面。而且,艺术家与物(钢丝球)之间的关系,成为他作为人与时间之中的未来之关系的确定表达:反正,未来对于艺术家本人而言,那是一个沉甸甸的、甚至胜过他自身重量的钢丝球。在具体实施《时间的形状》的过程中,未来成为可以预见之物。换言之,人只有在行动中、处于事件的达成过程中才有他的未来。
隋建国:《时间的形状》
漆
2006年至今
隋建国:《大提速》展览现场
12屏录像
时长31分
2007
以时间为容器、将复制的空间盛入其中。这是隋建国先生2006年9月在《大提速》中所要表达的主题关怀。作品依据第六次中国火车大提速,实施地点为北京环铁这个有固定圆周的地方。列车以固定速度奔跑在上面,形成一种强烈的空间形式感。按照艺术家本人的叙述,他“用12部摄像机同时开机拍摄奔驰的列车,然后用12台投影仪把录像展示在展厅四面围合的墙上,于是列车就在面面中奔驰起来。列车在每一个单独的面面中出现的时间一般只有几秒钟,在它出现在另一个画面之前,它就是奔驰在拍摄现场的两台摄像机之间的轨道上。把所有火车在画面中的时间与画面之外奔驰的时间合起来,就是现实中这列火车绕环铁奔驰一周所用的完整时间。用这个方法等于是寻找到一种视觉形式把环铁周长9公里的空间给复制到了小小的展厅当中。”12台投影仪所展示的录像,源于12部摄像机摄取现实列车奔跑的一段时段。从作品的构成中,我们看到物理时间在依托于列车这样的人造物中被分割与再次连接的可能性。
隋建国:《中国制造》
装置,夜景,霓虹灯
长2000cm
2005
当然,如果艺术家的创作仅仅停留于追问物理时间如何在一段铁路周长中度过,那么,他所做的也不过是列车速度的勘测工作,不能成为一件艺术作品。当观众来到这件作品的展厅时,听到呼啸而过的列车从眼前逝去,大部分人也许都不会停留在思考列车如何在物理时间中度过的问题。在其意识生命深处,也许自然会联想到我们作为汉语族群的乌托邦梦想经验,一种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的“时代列车”与追求“进步”的记忆,一种从西方启蒙运动以降再由进化论推波助澜形成的“进步”史观,一种以速度、效率为标准的急功近利的近代人生哲学。事实上,在普遍的物理时间面前,任何族群似乎都没有跨越式地、大跃进式地发展的特权,正如任何人都只能一天一天地成长一样,正如列车除了在摄像机中奔跑外还需要在摄像机之间的现实空间距离中奔跑。当我们误把摄像机中奔跑的列车的时间当成现实中奔跑的列车时间的时候,我们只是在主观的世界中跨越历史而被客观的历史无情地抛弃了。事实上,除非客观地回到当初出发前的起点,否则,我们只会欲速不达。《大提速》的意义在于:物理时间的长短乃是人类的命定。人们可以主观地设想超越之,但在客观上依然无法摆脱它的绝对囿限。所谓“进步”,只能是一步一步地往前移动,无论个人的生存还是族群的发展都不会有例外。这或许就是隋建国在自白中流露出的他借助这件作品来反省现代化“神话”的意涵。这或许也是他的《中国制造》要传递的主题。
就个体生命而言,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现代化”的生存方式,只存在一种现代性的生存经验。“现代在人文价值体系中意味着人对自己当下存在的自觉,人从自然本能血缘的肉体生命存在转化为社会(历史)本质的精神生命存在。世界历史中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只是这种人的自我解放运动的必然途径。现代人对当下存在的自觉,不是以过去未来为视点直观当下,而是从当下存在中生起对终极信仰的呼唤。所谓社会中的个人,正是在当下存在中呼唤终极信仰、承受终极信仰临照的自我。个人绝对独立于他人面对人类存在。这里,人类无非是以终极信仰为历史信仰的个人集合,或者说,人类是终极信仰临在的选民。
作为人文价值理想的标志,现代化在时间逻辑中以现在的在上性承受终极信仰的临在,在正义逻辑中以人的人化.神的神化为法权正义的本源,在信仰逻辑中以终极信仰的历史化承诺人类历史的终极合理性。”【l】如果我们承认欧洲历史在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化过程中所经历的法律文化与基督教的洗礼具有普遍有效性,如果我们承认汉语思想传统的确在过去五千年来没有把华人的生存引入一种现代性的生存之境,那么,汉语族群目前正在经历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化似乎也没有任何捷径可选择。日本人在政治、经济层面的现代化与在文化层面的更多的反现代性的诉求以及由此在二战带给亚洲各民族的灾难阴影,就是对于任何所谓成功的地方现代性的控诉。
隋建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开始研究现代雕塑,是“在观念主义方向上走得最远的中国雕塑家”,其艺术“经历了现代主义(1987-1989)、材料观念主义(1990-1996)和视觉文化研究(1997-2007)三个时期”(黄专语)。不过,我们很难将《时间的形状》、《大提速》两件直接探究人与时间关系的作品纳入所谓的“视觉文化研究”的范畴。同样,他以钢结构、钢管、钢球等制作完成的《运动的张力》(2009)、《无题》(2010)等,也不止是关涉到视觉文化的问题。相反,它们企图挖掘人的身体如何感受在空间中运动的物体的潜能。或者说,观众原来仅仅以视觉器官来欣赏雕塑的方式能否转换为人的整个身体器官的方式。《运动的张力》中,展厅高处借助重力滚动的钢球在滚动中撞击钢管的拐角发出巨大的声响,同在地面上两个分别为230和360厘米直径的滚动钢球,再加上随时准备躲避的观众形成了一个偶在的、带有心理场景效应的互动空间。作品将时间的因素、观众的身体、球体的位移结合起来。共同改变着人的生理存在与艺术的内在关系。后者,同样是其在苏州本色美术馆入口处上空展出的《地平线》(2010)的主题。当观众从头顶上镂空钢结构四方体经过时,其身体不禁会产生一缕惊魂。
隋建国:《运动的张力》
钢结构,钢管,钢球等
2009年
今日美术馆
从隋建国个人的艺术创作史,我们似乎可以窥视到他的这种转向对于人与时间的关系之关注的缘由。早在十年前,他曾经发展出一种艺术创作的方法论,即艺术家主体如何从创作过程中消失、其存在仅仅体现于对对象的选择上。他的《衣钵》(1997)、《衣纹研究》系列(1998)就是这种方法论的实践结果。事实上,它们还有一种存在论的意义的开启,即它们探究的是人与历史的关系问题。中山装《衣钵》承载着20世纪一百年的中国革命文化,但同时是汉语族群千年传统的精神表达,一种总是企图通过革俞迅速建立人间天堂的乌托邦思想的表达;《衣纹研究》系列,不仅涉及中西艺术文化的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挑战我们如何在这个“混现代”的现实里直面西方文化一步一步走过的从前现代向现代、从现代向后现代的历史传统。那并非是一具《无常》(2009)的枯干的骷髅骨架,而是关乎我们每个人生存于未来的活着的过去。
隋建国对于时间问题的思考,也影响了他的学生。其中,王思顺的《不确定资本》(2010),就是非常典型的个案。他把代表资本的一定量的硬币熔化铸造成钢锭,然后卖掉,再把卖来的钱兑换成硬币熔铸成钢锭,如此反复循环……随着时间的推移,钢锭会越来越粗,资本在流动中的不确定性得到了形象的明证,同时也关系到人生之无常的哲学。当人把白己的时间性存在建立在货币之类物化形式的基础上时,其不确定性便显而易见。
隋建国:《无常》
综合材料
高10米
2009
注:【1】查常平:《日本历史的逻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6页。
注:本文节选自查常平著《中国先锋艺术思想史 第一卷 世界关系美学》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