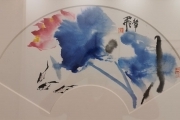破碎的现代性——“他们”笔下的都市生存意象
文:何桂彦
“现代性”(Mondernity)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由工业革命与现代化变革引发的,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领域反映出来的某些独特的时代症候。法国现代主义诗人、文学评论家波德奈尔曾对“现代性”进行过界定:“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与不变”。在波德奈尔看来,现代性应包含两个主要的内涵:一个指现代生活所体现的偶然性、瞬间性,一个是审美体验的即时性、短暂性。实际上,如果我们将现代化作为现代性的前提条件的话,那么,现代艺术则是现代性在视觉与审美层面的集中显现。
然而,问题在于,从一开始,现代性在政治、经济、艺术等领域的显现就不是统一的、和谐的,相反是矛盾的、砥砺的,因此,伴随着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现代性就呈现为一种破碎状态,而现代性的焦虑则成为一种主导性的社会和文化现象。事实上,仅仅从艺术领域来看,从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开始,“现代性”就是前卫绘画无法绕开的课题,但是,真正集中反映现代社会,或者说“现代性”所带来变化的,还是后来的印象派。虽然印象派的艺术家追求光色的表现,力求准确地反映源于当下生活的视觉体验,但就作品的主题来说,它们大多是围绕都市化的背景展开的。在T.J•克拉克、托马斯•克劳等批评家看来,印象派绘画的主要魅力在于反映了19世纪中后期法国中产阶级的日常休闲生活,其题材大致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表现中产阶级的休闲与娱乐,如马奈笔下的“野餐”、“郊游”、“马戏团”,雷诺阿笔下的“包厢”、“剧场”、“舞厅”等;一类则表现了艺术家在都市生存中所产生的焦虑与困惑,尤以德加描绘的“酒吧”和劳德累克的“舞女”题材为代表。继印象派以后,都市体验与现代生活就成为了西方现代绘画主导性的发展方向:一种类型是侧重反思,强调表现,作品充斥着悲观主义的色彩,像蒙克的《呐喊》、皮卡比亚的“机械”类作品,以及德国表现主义的作品;另一类则是对工业文明、理性精神、都市生存的歌颂与褒扬,带有浓郁的乐观主义情怀,如巴拉、波丘尼为代表的未来主义、莱歇代表的晚期立体主义、安迪•沃霍尔代表的波普艺术等等。
由于中西的现代化变革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作为“后发性”的现代国家,中国新时期的起步是发轫于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开放。但是,即便如此,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的“伤痕”、80年代初的“乡土绘画”,也包括80年代中期的“新潮美术”和90年代初的“政治波普”,其实都可以纳入现代性的维度下进行讨论。不过,都市题材在中国当代艺术中的集中涌现还是在90年代。虽然说80年代的时候,一批艺术家的作品已涉及到都市生存,如叶永青的《城市是一个处理人类排泄物的机器》(1985年)、毛旭辉的《水泥房间里的人体•正午》(1986年),以及张培力、耿建翌的早期作品,但是,只有“新生代”出现后,都市才真正成为一个重要的创作母题。
2005年,“他们”创作了“同一房间”系列。这批作品不仅让他们倍受美术界的关注,而且,对都市题材的涉及,也使其与90年代以来的当代都市绘画形成了一种潜在的艺术史上下文关系。实际上,“他们”早期的创作主要是观念作品,在中央美院读研究生时期,“他们”创作了《他们•公司》、《当代艺术四六级考试》、《中国当代艺术颁奖》,以及《图像聊天室》等。而“同一房间”系列油画的创作则成为了“他们”从观念走向架上的标志。当代人的生活以都市为中心,当代的许多问题也集结于都市。从切入和关注当代问题的角度上看,“同一房间”就是在当代都市文化的语境下生效的。粗略地看,从90年代中期以来,当代都市绘画开始逐渐呈现出两种主要的创作方向:一种是对当代都市人的生存处境、生命要求、存在状态的反映;另一种是直接表现都市本身,通过从城市化到都市化的变迁与发展,来反思、审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过,和上述两类作品的侧重点稍有不同,在“他们”的作品中,都市仅仅是一种文化表象,它们是图像化的、符号化的,起到是一种意义索引的作用。亦即是说,对于“他们”而言,都市的意义主要在于能为作品构建一个叙事背景,而且是在现代性的维度中凸显意义的。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文化景观,它们能成为中国梦、“大国崛起”等一系列宏大叙事的表征,这在《他们•国贸》、《他们•鸟巢》、《他们•歌剧院》、《他们•中央电视台》、《他们•星空》、《他们•外滩》等作品中可见一斑。
如果将注意力从室外转向室内,“同一房间”呈现出的却是一幕幕耐人寻味的情景。在“他们”的笔下,政客、白领、商人、无厘头的青年、京剧人物,以及各种时尚杂志、人民币、生活物品等均可以出现在同一个画面上,由此形成一个多义、混杂的画面叙事空间。虽然艺术家使用了写实的语言,但这种表达场景的手法实质与学院的写实主义并没有太多的联系,相反是介于现实与超现实之间的,因为艺术家追求的是一种蒙太奇式的并置与错位。事实上,从作品表现的内容来看,它们也是多元而丰富的,毕竟那些具有政治的、色情的、变态的、暴力的、孤独的、荒诞的场景都能成为作品表现的主题。如果说印象派画家对都市生活的反映主要是现实主义的话,“他们”笔下的都市生活则以后现代的消费社会为背景,其体验也是支离破碎的、片段化的。
当碎片化的生活业已成为当下都市人一种真实的存在,那么,生活本身就必然会夹杂着些许的荒诞。“他们”的作品正是对充斥在现实生活中的欲望与焦虑、繁杂与不安,无序与矛盾的反映。当然,这一切又是在现代化或者现代性的焦虑中展开的。在“同一房间”系列作品中,观众都会看到一个置于柜子上的电视机。与其说这个电视机是现实的,毋宁说是象征性的,而且,其所具有的意义也是多元的。它既可以表征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也可以看作是意识形态话语的工具。因为,它的出现不仅可以提示文化工业的生产与消费正日益支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而且,也能揭示意识形态话语对私人空间的潜在控制与不断渗透。与电视机一样让人无法回避的是,画面中总有一个背着身的神秘男子。对于观众而言,这个男子仿佛就是一个“他者”,没有自身的主体性,而且与画面中的人与事也不发生任何关系。然而,这个缺失了主体性的男子又是“在场”的。这无疑是一个悖论。很显然,由于对画面的叙述注入了观念的成分,由此,男子的出现使画面原本就具有的荒诞感得以强化。
如果从创作方法论的角度考虑,不管是碎片化的生存意象,还是画面弥散出的荒诞感,这一切似乎都与艺术家独特的图像叙事手法息息相关。事实上,伴随着今天数字与网络技术的发展,图像的生产与消费、传播与接受不仅改变了人们的视觉与观看经验,也改变了人与自然、人与现实之间的依存关系。而图像时代绘画的一个基本特征则是:以图像为中心,其意义也由图像来承载。从2004年创作的《图像聊天室》开始,“他们”就在探索图像的意义边界,以及不同的图像在同一个画面中所引发的叙事性问题。之所以说《同一个房间》呈现出的是一种碎片化的都市生存意象,原因就在于,艺术家将传统与现代的、西方与东方的、政治与消费的各种图像融入到同一个二维的平面上。由于每一个图像都有自身独特的意义,以及赖以依存的文化语境,因此,当艺术家消除了空间的界限、抹平了时间的印记,将不同的图像并置在同一个画面时,图像与图像之间的冲突与砥砺、交融与渗透,最终会形成一个多义的、矛盾的意义系统。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图像原有的意义逐渐被消解、被破坏,另一方面,新的意义又在碰撞与交融中不断生成。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些图像的时代属性的话,就会发现,在“他们”的作品中,同一幅作品中均可能会同时出现前现代的、现代的、后现代的图像。事实上,对图像叙事的强调,不仅让“他们”完善了自身的创作方法论,而且强化了绘画的观念性表达。更重要的是,艺术家对图像的选择是基于一种文化现代性的视野,而那些碎片化的生存意象也源于自身内在的“中国经验”。
应该说,“他们”对图像叙事的强调,与作品所要追求的对“破碎的现代性”的表达是完美统一的。换言之,作为方法的图像叙事,完全可以转换为作品的主题。随着对图像叙事这种方法的熟悉,在2006年以来的作品中,“他们”开始大量“挪用”西方艺术史中出现的图像。作为一种艺术创作方法,“挪用”就是指艺术家利用过去存在的图式、图像来进行艺术创作。但是,“挪用”并不同于简单的“模仿”,因为“挪用”背后涉及到艺术家深层次的意义诉求,以及创作方法背后涵盖的美学问题。在“他们”的作品中,这些被“挪用”的图像都是西方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时期的大师作品,它们的作者有马奈、梵高、高更、蒙克、夏加尔、毕加索、蒙德里安、马格里特、培根、达利、杜尚、沃霍尔、利希滕斯坦、约翰斯、琼斯、汉密尔顿、哈林、弗洛伊德等。当艺术家将这些图像与中国的少林和尚、样板戏中的人物、京剧演员、陕北老农、大熊猫等并置在一个画面空间时,图像的意义同样会形成一种混杂与矛盾感。很显然,艺术家对这些图像的使用,着力点并不在于讨论图像因文化语境的错位所形成的“误读”,也不在于建立一种艺术史语境中的“互文”性,相反,其深层的文化诉求,仍体现为拓展现代性的内涵,将其纳入到全球化与消费社会的语境中,进而去反思当下的社会与文化生活。
对现代性的质疑、对城市化的反思、对消费时代的批判均终结于2009年创作的《他们•失落的天堂》。《失落的天堂》以现实主义的视角、宏大的场景、恢宏的气势营造出一种独特的视觉奇观。和早期作品重视图像的观念化表达,如对并置、挪用手法的使用有所不同,这件作品追求的是一种宏大叙事的气度与史诗般的气魄。虽然艺术家没有明确地给出他们对都市生活的价值判断,但透过那些繁华的都市景观,我们仍能隐约地感觉到画面中潜藏着一种冷静的思索与批判。这种感觉来源于艺术家对视觉隐喻的调动。画中赤裸的女人体是作为欲望和消费的对象而出现的,类似于废弃的汽车。前景中的建筑废墟与背景中的都市相互印证,暗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都市化已成为一个势不可挡的发展趋势。而那些出现在画中的各类形象(世界名画、动物等)、人物(保安、模特等)与废墟的意象一道似乎都在说明一个事实:这是一个无序而混乱的世界,生机与毁灭同在,欲望与焦虑并存。
在2011年的作品中,“他们”的创作开始转向,有两个发展脉络值得关注。第一个脉络延续了先前对都市的表现和对现代性的反思。像早期的作品《他们•国贸》、《他们•鸟巢》、《他们•歌剧院》一样,最新创作的《上海上海》、《中国馆》仍然是对中国梦、“大国崛起”等话题的言说。如果说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标志着中国真正跻身于全球化的格局中,那么,2008年的奥运会与2010年的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则塑造了中国新的国际形象。不过,艺术家并没有对宏大叙事的“中国梦”流露出太多的兴趣,画面的叙述依然是平静而内敛的。对于艺术家来说,用一种冷静的态度去审视这些社会与文化现象远比单纯的歌颂与批判都重要。尽管如此,有两个变化仍然十分明显。一个是强化了“工地”所负载的意义。在这两件作品中,“工地”的意义是双重的,它既可以理解为建设,也可以作为一种意象化的废墟而存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现代性内部原本就具有强大的张力,并潜藏着一种深层次的危机。 另一个变化是画面中出现了一些建筑工人、保安,或者说“底层人物”的形象。这些形象的背后,至少表明艺术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始终保持着必要的距离。
第二个变化是艺术家强化了对自我文化身份的追问。早期的作品如《他们•金陵十二钗》、《他们•女孩与国画》就对这一问题展开过讨论。不过,在最近的作品《静谷三贤》、《泛远舟》、《游园惊梦》中,艺术家对自我文化身份的追问是在反观与凝视的视角下进行的。这是一种双重的观照。一种是画中人物与其置身其间的风景所形成的相互依存关系。和“同一房间”中的那个背着身的神秘男子不同,在《静谷三贤》、《泛远舟》中,画面中出现的青年并不是“他者”,而是正在凝神思考的主体。另一种观照是观众与画面的场景所形成的凝视关系。因为,对于观众而言,画中的人物与场景最终会成为一个客体,成为被凝视的对象。事实上,不管是从“三贤”,还是从戏曲人物形象所具有的文化指向性看,“他们”都希望将这种双重观照引向对传统的追思。反观既源于对现实的疏离,也源于对过去的审视。在“他们”的作品中,反观为作品赋予了一种时间性,一种距离感,并使其弥散出浓郁的怀旧意识。而对传统的追思,则源于一种文化上的乡愁。事实上,对于当代都市人来讲,乡愁是一种梦,而文化上的乡愁则是希翼为精神找到一个栖息的家园。很显然,这种乡愁不仅仅是属于“他们”,也可以属于一群人,属于70后的一代人。
虽然“他们”的作品在主题上涉及到诸多的话题,如对现代化进程的敏感、对城市化的反思、对消费社会的反映、对全球化问题的关注、对自我文化身份的追问……,但其内涵都是围绕着“现代性”展开的。和西方现代主义早期的绘画对都市化变革与科技理性进行直接的批判(如蒙克、皮卡比亚等),或者赞美(巴拉、波丘尼等)有所不同,“他们”的作品总体上显得冷静而内敛,其目的则是以现实主义的视角,去透视、反映、呈现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及其引发的诸多问题。如果我们认同波德奈尔所说的,“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的话,那么,“他们”的作品则契合了现代性的特征,因为它们是分裂的、破碎的、片段化的,同时也是异常真切和让当代人无法回避的。
2011年5月4日于望京东园
【编辑:耿竞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