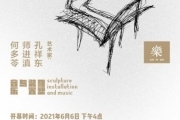何多苓 婴儿风 布面油画 100×80cm 2006
一 母亲
唐丹鸿(以下简称唐):我想请你谈谈你的母亲。前几天你的母亲刚刚去世,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母亲,你也做了很大努力想从这个事件中走出来,但我还是希望谈到这些话题:母亲,家庭,你的童年,以及他们是否在绘画方面对你产生过影响。
何多苓(以下简称何):高中时我想将来报美术学院,但是我父母认为画画是有点趋向于歪门邪道的专业,因为当时是比较流行学习理工科的,他们是知识分子,觉得学理工科起码可以发动经济,才算正路,而我就读的七中是很好的学校,还是重点学校,所以他们给我否定了。我也没有坚持,没想那么多。在七中的整个高中期间,我画画都是画耍,我现在还有留下来的图画本,一直留到前几年才弄丢的,全是钢笔画,哪天找一下我妈的遗物,看是不是我妈藏在哪里了。
唐:你那时都画些什么呢?
何:钢笔画,主要画些打仗的人,当时就画得很成熟了,像插图。也有临摹的。我临摹过一艘军舰,当时我对武器比较感兴趣,像所有男孩子那样对武器特别感兴趣。所以我就拿很细的钢笔画了一艘军舰,把所有细节全部画出来了。……画得很细,很得意,课间的时候就拿给班上的同学看。我班上有个废头子,他看了说:这肯定是印的,决不是画的。他说我不信是画的,说着说着他就用手指蘸了唾沫一抹,一下子就给抹花了。结果是我们暴打一架,我气得很。这个事情我印象比较深。那个时候我看了很多杂志,完全不是我那个年龄阶段的娃儿看的,什么《国际航空》之类,里面有飞机的剖面图啊什么的,画得非常细,我都全部临摹出来,当时这方面,虽然我没有正规画画,但是体现了后来画画的一些特点,就是对整体把握啊,对细节的关注啊,对形体的关注啊,当时已经有了。而且总的来说,虽然还没有正式学,但已经脱离了儿童绘画的阶段,已经画得很正规了。但是我始终没有在那个阶段认真地学过绘画,而且关注的东西仍然是《国际航空》啊、《知识就是力量》啊之类,一直喜欢科学,自然科学,现在都是这样。我母亲他们在那个时候也很忙,顾不上我。
上高中的时候我的成绩已经不算好了……就像现在我画画也会有很多东西干扰一样,我很容易分心做其他的事情,我始终有些时候对某件事情入迷,就影响我的功课。我高中的时候成绩不大好了,他们就生怕我考不起大学了,把我抓得很紧。根本不会鼓励我去画画,一直到了高二的时候,我当时已经有紧迫感了。在我就读的七中,那是个好学校,很多同学成绩都很好,立志考大学,我妈他们生怕我考不起大学,很焦虑,把我抓得很紧,我也有些焦虑,怕考不上大学,正在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来了,我很高兴,可以不考大学了,嘿嘿。有很多人很气哦,觉得遭耽搁了,我简直是高兴,觉得很好玩。所以说实际上我正式画画是一个很晚的事情,到文革中间才开始画的,画一些插图啊、想象的画,而且特别喜欢画想象画,不喜欢临摹,然后就……一直到下乡。
那会我什么都搞,拉手风琴、学作曲等,感兴趣的东西有点多,又喜欢看书、阅读,这些我都感兴趣。所以说,真正画画的时间并不多,而且还没有学过。一直到我认识了朱成,才跟到他们画点什么风景写生,那都不能算正式学。都是后来,知青调起来后,才开始画画的。当知青的时候,实际上因为我是我们生产队最后一个调起来的,我一直在队上耍,没有怎么出工。天天就画画、研究作曲,过得很自得其乐。
记得有一次,我妈从成都来看我,那会我妈都50多岁了,她是1917年的。她大老远地坐火车到西昌来看我,当时我不在我们队上,跑到其他地方去耍去了。有个同学跑来找我,说“你妈来了” 。我吓到了,心头还很不舒服,因为我一直不想让我妈看到真相,老是阻挡她来,她几次要来我都老是阻挡、欺骗她不要来,我只想报喜不报忧。现在她突然袭击来了,不给我任何准备,我又不在队上,心头很有点不安逸,觉得我妈有点突然袭击,嘀嘀咕咕就下去了。我妈说的,她来是一路问起来的,我们那个生产队是在个坝子头,一个坝子,下了火车,一路走进来好几公里。走进来了边走边问,问到我们队上,一问我的名字,说起何多苓,老乡就来控诉我,说我懒得要死,一天鬼混等。我妈气惨了,因为我总是给她谎报情况,我妈就把我数落了一顿。当然后来也没有什么,我带她到各个生产队走一下,看一下朋友,住了一两天。我的住处完全像个狗窝,天晓得我妈当时咋个住的。
后来我就把我妈送起走,我还记得到那个场面,我把她送到火车站。当时是去的泸沽那个火车站,当时为什么不在漫水湾上车我记不到了,反正是搭车到了泸沽,离漫水湾大概30多里。等火车,去得还早,我妈就喊我先走,怕我赶不回去,因为我若搭不到车,就要走30里路回去。我妈就喊我快走,不要等她了。后来我就先走了,我妈一个人就坐在那,西昌荒山到处都是枯草,火车站是个小站,来火车的时候才有点人,没有车子一个人都没有,我妈就坐在那唯一的一把候车椅上,一个人坐在那。我妈就来过那么一次。
后来我就……也是开后门,我进了成都师范学校,有个美术班,我就开始画画了,开始正规学习。毕业后我分到……哦,对了。中间还有个插曲,就是我先去考“五七”艺校,就是周春芽他们进的那个“五七”艺校,我也去考了的,我有个同学他帮我去报了名,我就画了张速写,红色娘子军的芭蕾速写。老师看了觉得画得之好,就喊我回去考,我当时从西昌筋斗扑爬地跑回去考。结果,是当时考得最好的。但当时我爸还在“五七”干校,是属于问题没有说清楚的,政审没有过关。我考上了,又喊我回农村去等,却一直没有消息,我也无所谓,反正年轻,什么问题都想得开,待在乡下有兴趣就出一下工,没有兴趣就在屋里搞点其他的。
其实,我觉得那段时间对我来说,对我的各方面都起了很大作用。首先是阅读,我全部的重要阅读都在那个阶段。那时我们很多同时下乡的朋友都是知识分子家庭,带了很多书来。就互相传阅,很多经典名著,我都是在那个时候看完了的。包括雨果、巴尔扎克的书,我都在那个时候看完的。狄更斯、契诃夫、托尔斯泰,全部在那个时代完成的。朱成当时收集了很多画册,应该说是画册上撕下来的。我经常跑到他那儿看,一翻就是几天,那些东西对我影响很大,慢慢就走上了这条路。如果不是“文革”,我也许不会走上这条路的,我完全可能是另一个人的。
唐:为什么?
何:没有“文革”的话,我也许就要考大学嘛,考个好大学,考个孬大学,反正不一定画画。也许我会去考中文系,因为我作文一直不错。我要回避理工科,因为我的数学孬。若考上了大学,过后很可能就不会去画画。恢复高考那年我已经29岁了,就年龄来说,考大学对我已经是最后界限了,有很多人劝我去考,说是最后的机会了。我犹豫了一下,就去报了名,就考起了美院。
我觉得专业学习很重要,如果没有经过美院学习我肯定也不会走上这条路,我可能早就放弃了。很偶然啊,我们家里也没有鼓励我做这个事,我自己也没有认真画过画。你看像郭伟那些年轻艺术家,他们从中学时代就很执著,就开始画画,还找老师学。我几乎没有找老师学过,没有认真地学画画,没有把它当成自己的事业。有段时间,我还很想学音乐,学作曲。自己找些书来看,研究和声学等。所以画画没有进入一个很重要的日程。所以说,这些都是些机缘,包括下乡。后来,师范学院招生的时候,因为我其他科不行,包括各种班,数学班、语文班那些,我想美术班其他科要求最低,我就报了个美术班。那会在那里算画得好的,胡成思也是我同学嘛,我们就是从那开始认到的。这个美术班一考就考上了。当然,这个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我干事情都是嘛,我很快就入迷了。我只学了一年,当时是速成的。为了解决成都市教师缺乏问题,我就分到了幼师。很多人误认为我是幼师毕业,其实幼师只有女的没有男的。我就是幼师的老师,教了四年书,业余时间,我就抓紧时间画画,而且是全部兴趣都在画画上,而且全部画油画,比较正规。所以在考美院前我已经参加了全国美展,当时在成都市小有名气了。所以那会儿考美院和现在学生都不一样,我们那会儿年龄都大了,自己的风格基本上已经形成了。所以,进美院完全只是一个回炉过程,把自己的风格和美术界的东西结合起来。所以说,我真正是很偶然、很偶然的从事了绘画。我妈在里面没有起直接作用,就是我小的时候鼓励过我参加美术竞赛。
唐:就是说在绘画方面没有压制过你?
何:从来不压制我,我们家这点很怪,我妈是学中文的,职业是教书,培养了我对文学的兴趣。我爸是学经济的,对绘画这些事完全一无所知,也是毫不关心的。出来个我这种人,气质上和他们完全不一样,似乎很奇怪,好像没有什么遗传基因。
我妈从性格上来说,我觉得她是女的当中很坚强的那种人,她一直到死都没有叫过苦。父母那种忘我,老了全部心思都在自己儿女身上,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什么,对我们没有任何要求。我爸年轻的时候太要强了,完全是躬起个背,拼命地做,当时下放到江油,弄起去背煤炭,他都把它熬过,可能就是这样把身体搞垮了。我爸本来身体很好,但是说垮就垮,70多岁一下就垮了。我觉得他们这一辈子,在我看来就完全是一个悲剧。我妈,我跟她在精神上不能完全沟通,但有一种血缘和一种感情,还有一些潜意识的东西。所以,我妈去世后,我最痛苦的就是在精神上没有跟她很好地沟通,这是我最痛苦的一件事。生活上我倒是尽可能地照顾,治病啊那些都尽力了,这些都不是很遗憾,她那么大岁数了,肉体的衰亡是必然的,所有器官都接近失效了,有时候想起来比较不能释怀的就是精神上和她缺乏一种交流,她老了以后,耳朵也不好了,交流也比较困难,我也懒得跟她说话,几句话毛毛糙糙就把她打发了。其实我想我妈一直对我是特别关心的,我是老大,和她一起长大的,她很引以为自豪的。我妈始终对我很关注,当然她对我弟弟也同样很疼爱。但对我呢有种特殊关注,这方面我觉得没有满足她,我现在想起就觉得这是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所以我要给你说,你现在要和父母搞好关系,经常接触,多些交流,哪怕经常吵架,有些代沟都不算什么,这样以后就不会有什么遗憾。这就是我对我妈去世后感到最遗憾的事,好像我妈还躺在病床上时我就觉得我们已经有很远的距离了,虽然我们离得很近,但我不晓得她在想些什么,她也不晓得我在想什么,我觉得精神上的鸿沟本身是可以想办法填补一下的,但是我没有做这个努力,这完全是我的责任,虽然说,旁人都觉得我对我妈很好,但我觉得这不是真正的好。
唐:你是想完美无缺?
何:每个人在这个时候都是有遗憾的,这个肯定也是。我觉得这个也许很重要,对于我妈来说。在她年老以后我们交流越来越少了,我每个星期天回去就是在那儿坐起,我妈也不怎么说话,我也就很主观地认为我们只要回家了,待到那儿就行了,但实际上她还是渴望和我们交流,我妈肯定还是很想晓得我们在做什么,想什么。但是,可能作为儿子呢不容易做到这点儿。我们家里的人也是比较内向的,待到一起也没有很多话说,反而在家外头,与那些气质不同的人交往话要多一些。原来我跟我爸吵架的时候,争论政治问题,争论得很凶。
唐:争论政治问题?
何:是呀,争论政治问题,所以我妈觉得我反动得很,担心我早晚是要坐牢的人。我有点逆反,我爸越是站在正统的立场上,我就越是给他扭起说。那时我妈就在中间作调停人。
唐:有点担惊受怕?
何:哦,有点担惊受怕,怕我在别的场合也这样说。当然,后来我年纪大了,我就能体会了,我就尽量回避这些问题。他们身体不好了,我爸火气没有也不那么大了,他不想说,我也不想说。我们就回避这些问题,不谈政治了。他们稍微放心点了,觉得我成熟点了。但,实际上晓得我肚子里面经常想这些事情。他们也比较回避这些。我父母真的是这种比较放任我们的,不像刘家琨他爸那种北方人,家长制。我们家根本就没有,父母完全不管我们。然后呢,还小心翼翼地揣摩我们在想什么,生怕刺激我们。很多事情,像我离婚之类,他们都不问。我妈最担心我的生活,怕我把身体搞垮,我就乱说,说我天天都在炖鸡吃,报喜不报忧。后来我听我表妹说,我和我表妹交流比较多,说我妈在生病前有一次给她说,说我什么都不给她说,包括我车子掉了,都不给她讲,她都不晓得。其实我很成功地瞒了好多事,那次我的腰闪了,我都很成功把它瞒过去了。当然,我的动机也是怕他们担心。我妈是个操心的人,一旦知道了,就耿耿于怀,晚上睡不着觉。我想何必让她晓得呢。当然,现在想来这样也不对,从一开始这种方式就不太好。现在我想来,最近我也经常在想这些事情,不可能一下子就搞忘了。妈嘛,反正只有一个,没有了就没有了。很多东西都是不可挽回的。我也什么都不能做,最多给我妈画个像什么的。我妈现在处于黑暗之中,很遥远的黑暗中。过去缺乏的东西,现在再也无法挽回了。当然,每个人都会有一种遗憾。每个人跟父母都不一样,都有一种最终无法沟通的沟壑。我呢,我希望我可以尽快调整过来,也有一些想法。
二 女性
唐:在你的作品中有很多女性,你画了很多女性,无论是来自哪个阶层的模特,你都把她们画得特别优雅,很美、很高贵。你觉得这是不是和你母亲之间存在一些联系?
何:也许吧。可能我妈对我有些影响。我妈是学中文的,古典诗词方面的书比较多,我也要看一些,也许这对我的个人气质也有些影响。
唐:看到女性在你的作品中的形象,使我觉得你对女性的感受是美好的。不像有的画家,他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会让人觉得他把女性看得很低。我觉得你作品中的女性反映了你对女性的态度。
何:我不可能把她们画得很邪恶。但我一开始学画时是男女都画,后来从90年代开始就基本以画女性为主了,后来几乎就全是画女性了,这成了我的一种习惯。其实我并不是不能画男的,男的我也可以画。但是怎么说呢,就是一种惯性。在画女性题材的过程中,能够更多地满足我。这种满足,就像你刚才说的,我可以把女性画得比她们本身更美一些、更好一些、更崇高一些。我喜欢表现女性的细腻、敏感、多变、微妙。这些东西都是我所追求的,我比较喜欢这些东西。我不喜欢粗枝大叶,在细节方面我是始终关注的,比如很细微的东西——胸口的皮肤上的斑点、色素、血管形成的一些微妙的色彩等等,这些东西恰恰是只有女性才能体现出来的。
有人说我过去是唯美地画女性,好像我现在画的女性要世俗一些、客观一些了。我过去画的女性肖像的确是给她们强加了很多东西,不自觉地会加上一些因素,使她们显得比本来更美。这点是我独到的,这种美不是表现本质,也不是要画得像洋娃娃一样,而是一种气质上的东西,一种高雅、忧郁的气质,这是我给她们加上去的。我觉得我现在画的女性较为接近她本人的气质,但是仍然有我的一些一脉相承的东西是摆脱不了的,可能一直到最后都会有。但我也不愿意摆脱,为什么非要摆脱呢?
我现在比较注意这一点,即我不要像过去那样在某一方面去美化,而是尽可能地客观。不过这种客观不可能完全客观,因为我毕竟不是照相机,而且我特别讨厌照相写实主义。所以说,我虽然客观了,但仍然有一些主观在起作用,所以这还是通过我自己的眼睛看到的客观,通过我的手脚表现出来的客观。
唐:你觉不觉得你画出来的有些女性的气质和你自己的气质有联系?
何:这个我承认。虽然我后来变得一点都不女性化了,而且还粗糙得很,还很玩世不恭,但是内心肯定有一种阴性的东西,我知道那种东西存在很深。对我来说,艺术本质上不是一种阳性的东西,而是阴性的东西。我不像有些画家,比如凡•高,表现出阳刚的一面,对我来说,艺术始终是一种阴性化了的事物。我想说不定很多搞艺术的人都跟阴性有关。你看艾轩,他虽然是一个很不女性化的人,但他还是有很阴性的一面;刘家琨看起来就是一个比较阴性、比较敏感的人;郭伟是一个很理性化的人,但还是比较敏感。看来阴性在这个行道里很重要。艺术,我觉得它的属性就是阴性。
唐:我觉得有些男人特别害怕自身中的女性气质,因此要表现得特别男性化。而你在这一点上却比较坦然,对自身中的女性气质是肯定和接受的。
何:我是一个很阴性的人,当然这些气质只会通过我的绘画表现出来,而不会通过其他途径去表现。所以我在色彩、画面的收敛和微妙等方面都去体现一些阴性的东西,而不是那种扩张性的玩意儿。我喜欢的绘画也有一种女性的或阴性的特质,我关注的画家也是比较敏感的。比如毛焰,他虽然是画男性的,但他的画充满了一些细腻、微妙和相当阴沉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我喜欢他的画。
唐:你近来开始了比较客观地画女性,这是否说明你把你自己和你身上的一些阴性气质稍微拉远了一点距离?
何:我想可能是。我在90年代的绘画中赋予画面的文学因素比较多,比如“忧郁”、“抒情”,还有一些人所看到的“苍茫”、“苍凉”等等,这些词汇都是一些文学词汇。这种因素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就使画面特别具有一种阴性的气质在里面。后来当我改变题材以后,我从观念这个角度有所改变了,想更多地表现得客观一点,尽可能把客观性贯穿到绘画中去,于是就更多地把自己隐藏起来。我认为,把生活、个人和艺术的距离拉得越远越好,现在就是这样想这样做的。
我肯定不会像其他人那样完全设定一种题材去画,我的题材还是跟自己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但观念的转变促使我更客观地去表现女性对象。可能这种努力是有成果的——就是我现在画出来的东西跟原来大不一样了,跟过去那种画,比如设定了某种眼神的那类画大不一样。现在我画的女性的眼神就有很多空洞的东西了,我觉得这种形式符合当代气质一点,当代人的气质中就有那种成分在里面。
唐:那种空洞是不是你对某种事物的一个判断?
何:是一种判断!这种判断从我的画里就能看出来。现在,比方说如果要我画出原来的那种忧郁的眼神,画是画得出来,但我觉得这是很明显的一种强加了。我现在画的女性肖像的眼神就很茫然、很空洞、很冷漠。很多人看我现在的画就觉得很遗憾,觉得丢掉了他们认为最动人的东西。
确实丢掉了,因为我已经不再觉得它们动人了。也可能是我自己改变了,像看我以前写的文章一样,我现在看来就觉得稍微有点滥情。我知道去掉了那种滥情可能会失掉很多观众,但我觉得并不可惜。更冷地看这个世界,或是更冷地表现它,也许更符合我现在的想法。
近两年来,我的变化确实非常大。虽然说是本性难移,但这样的变化,随着年龄、生活习性以及对自己的整个人生评价的改变,都会造成艺术上的改变。我的绘画中就体现出了这样一些东西。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当代性。当代性不是刻意为之的,而是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我作为一个当代艺术家,在对当代的客观世界的判断过程中,尽可能地用直截了当的手法去表现,这是必然的。
我过去的文学性和诗意特征越来越少了。当然很多人还是认为有,比如说,一些模糊性、不确定性、含混、暧昧这些因素仍然存在,而且很多人认为很好,我也认为很好。我现在尽可能把很多细节弱化掉,把很多体积弱化掉,而且尽可能更含混和更暧昧一些,我认为这种含混暧昧包含了很多因素,那就是当代社会生活给我留下的一些印象。我过去对人性的判断是比较具体的,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缺乏灰色和不确定性。现在我想大家都看得出这点,这个社会是由一片灰色所构成的,有非常复杂、含混和暧昧的成分在里面,因此我就表现这个东西,不把绝对主义作为出发点。绝对的概念我已经把它去掉了。所以我现在的画在很多人看来比较困惑,因为它缺乏对观众的一种引导性。不像我原来画的女性,别人一看,要么就是美,要么就是气质上的东西,诸如很忧郁、很抒情、很动人,能打动他,观众一看就放心了,觉得他看懂这幅画了;而现在一看,观众就觉得很茫然。再比如我画的婴儿,别人一看,就觉得很丑。原来要买我画的人,现在他们根本不买了,不能接受。这就说明他们还停留在原来对我的画的印象中,而我已经不能提供这种印象了。原来我赋予女性的,赋予我的形象的一些引导性的因素消失了,这样观众就觉得茫然了,所以他们不能接受我现在的画。但我倒真正觉得我现在的画比我过去画得好,比过去那个时代的技巧性更高了,而且客观性、不确定性我表现得更多些了。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观察者,我比原来更细腻,作为一个表现者,我认为我的表现手段更为丰富了。我对我的现在基本上还是满意的,虽然很多人可能觉得我在走下坡路,但我对自己还是比较满意。
唐: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你认为在你原来的作品中的一些特质,它们实际上是你所赋予作品的一些东西。然而现在,你从那种主观的“赋予”中走出来,换了一个角度,更“客观”地观察这个世界了,对吗?
何:对。原来那个时代是这样的:我当知青的时候,经常一个人躺在山坡上,听松涛,晚上看星星,反正就是遐想那一类的。这是很认真的,做这些事的时候,一点也不带虚假的东西在里面,因为旁边没有观察者,我又不表演给谁看。因此,这导致了我有些绘画中出现了那种“人跟自然的神秘联系”之类的因素,或者如别人所说的看到“苍凉”之类的因素。而且我当时喜欢的诗歌,比如美国的罗宾逊•杰弗斯的诗,就有强烈的自然色彩,有点像杰克•伦敦的小说,那些诗我当时还试图翻译。由于我当时对诗中那种洪荒时代的感觉特别感兴趣,所以画出来的东西确实就带有那些气质。另外还带有这样一些气质,比如说画《青春》、《我们这代人》的时候所追求的英雄主义气质、英雄主义情结,以及对历史悲剧性的回顾、对个人气质中的悲剧性加以夸大等等。
除了个人气质的原因外,时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时整个文学界、美术界都弥漫着这种情调,因此这也还是时代使然。
那么就现在来说,我肯定觉得……你看我现在为什么对我原来写的文章感到很“堵”了?因为我觉得很虚假。现在看来很虚假,当时不觉得,当时是很认真的。而现在我们开始对一些东西加以反讽了,这也是一种进步,说明把人性看得更透了,把自己也看得更透了,对自己有一种很强的冷嘲成分在里面了。那么对自己原来的一些东西就有一种本能的回避和抗拒,觉得那种东西还是有点假、有点滥情。
三 青春
唐:你说你当知青的时候,经常躺在山坡上遐想,都想了些什么呢?
何:宇宙嘛,宇宙!那会儿一到晚上,我就躺在山坡上,看山的轮廓。你知道西昌的那些星星吧?那个星空!我感觉自己就是一台天文望远镜。我的眼睛好,甚至可以分辨“双星”,大熊星座里有一对星叫“双星”。西昌的那个天空,完全是一幅星座图。我就躺在那儿看,躺在那儿想。当时有的想法对我来说已经算恐怖了。我想,所有这些星星,比方说一个恒星,也许它就是一个原子核,行星就是围绕它转的电子,也许我们这个宇宙就是另外一个宏观世界的一个基本元素。然后我又想,那我是什么呢?这一来嗡地一下头就想麻了!那会儿经常想这些……
我当知青的时候是很待得住的。你想,在那么一个枯燥、偏僻、遥远的地方,所有知青都调走了,只我一个人在生产队里还是待得下来。晚上的时候就一盏孤灯,周围黑漆漆地真有点吓人。我就看看书、弄会儿音乐、画点画呀什么的,要么就爬上山躺在坡上,感觉是躺在星河里,根本不在人世间了,因为整个地球都是一片漆黑,只看得见星空。我还记得那会儿半夜起来看彗星。是在1971年还是1972年我忘了,有一颗彗星,名字我也忘了,它不像哈雷彗星那样周期性要回来的,它是一去不复返的。当时广播里预告了它要出现,因此当它出现在天空中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我有多激动。我每天晚上午夜三点钟起来看,在那个时辰它在天上要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我画了一幅画,叫做《七二年彗星和火把节》,因为那时正是在火把节的时候,天上是彗星,下面是山的轮廓,山上有几点火光在移动,那是人间的火光,彝族火把节的火光在移动。天上,是很长很大的彗星,视觉上觉得相当大。我还记得半夜起来看彗星的时候把鸡都踩死了一只。当时那种强烈的感觉现在找不到了,当然,现在也看不到星空了。
唐:如果现在又把你放在当年的情景下,你还会不会有当年的那种激动?
何:肯定不会有了。我现在还要看当年的那些书,经常把那些书拿来看,但当年那种激动和沉浸的感觉,肯定就没有了。现在如果把我扔在西昌的一个什么遥远的旮旯里,处在一个人烟稀少的不为人知的穷乡僻壤里,躺在那片山坡上,我可能不能忍受。现在人不知道是怎么的,整个人完全被城市异化了。当年真的是待得住啊,这完全不是说着玩的,真是待得住。
唐:当时人都走了,你一个人还是呆得住,应该说你那时还有一个比较平静的心态。
何:就是这种东西支持我。我基本上都寄托在这些上面,要么是看书,要么我就想作曲,研究音乐,要么画点画。
唐:你作了什么曲呢?
何:没有作,我只是改编了一些,比如把《红色娘子军》的总谱改编成了钢琴曲,或者改编成手风琴曲什么的。还研究一些曲体学、和声学、作曲法什么的,就研究这些,为此还很找了点这方面的书看。
唐:我知道你喜欢音乐的时间非常长,而且有相当的造诣。你现在的音乐修养肯定和那会儿有很大关系。
何:那是,还残留了一些痕迹。我可能比其他画画的人要懂一点专业的音乐知识。记得当研究到和声学的时候,我终于打住了,没有钢琴,我也不会弹钢琴,在不听音的情况下理解和声还是有点困难,但我至少在手风琴上把和声尽可能地理解了,虽然动脑筋想得头昏脑胀的。我钻研的是音乐学院的课本,我看的和声学课本是该丘斯写的,大师的作品。那时候我的阅读的确很古怪。那时候我还忙都忙不过来,晚上研究音乐,白天出去玩,到别的队上去找别的知青,一玩就是一整天,从来不出工。
唐:你也说过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音乐性”。你能谈谈为什么这么喜爱音乐吗?
何:音乐对我来说可能是除了绘画以外的一个最早的爱好吧,而且我甚至于觉得要早于绘画。因为我认真学画是相当晚的,但是我喜欢音乐的时间非常早。最早可以追溯到念中学的时候。喜欢听一些当时很流行的歌曲,当然都是革命歌曲嘛,也喜欢唱。虽然我那时连简谱都不会识,但是我好像天生乐感很好,听了歌很快就能记住,而且模仿得很像。但是真正喜欢上可以称之为“音乐”的还是在“文革”期间。那时我还住在川大,我们一些半大的孩子经常在一起玩,有一个同学的母亲是音乐学院的,他们家里有大量的唱片,是当时所谓的“密纹”唱片,78转的,还有一个唱机。那时他的父母都到“五七”干校去了,所以我们就经常去他们家里听那些唱片。在那个时代,你知道,听唱片基本上属于非法,因为那属于资产阶级艺术,如果被抓到的话,至少是被没收唱片。我们当时对此竟完全不管,当然也不敢把声音开得太大,就觉得跟在搞地下活动一样,很有趣。那时听的音乐,确实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记得那时就有一些像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贝多芬的几个著名交响曲、林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天方夜谭》,还有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交响曲》等等。
那时候感到非常刺激的是,我们经常一到傍晚,就从各个方向悄悄进入同学的家,关上窗子,把窗帘放下来,然后聚在屋里听。他家是在一楼,有一次,我出门去想做什么,刚走出门来就发现窗下有个人影一下子闪开了,我赶紧折回去通知大家,叫他们把声音关了。然后我再跑出去一看已经没有人了。后来我猜想那人肯定是川大的一个老师或是一个音乐爱好者,他实际上是躲在窗外偷偷地听音乐。在窗外是可以听到一点声音。这是一个小插曲。
后来我听CD的时候,也找到了一些当年我听的那些音乐,比如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作品590号,当年我印象非常深,所以当我一看到那张碟的时候,赶紧把它买了下来,回去后在CD机上一听,音色比当年那张“密纹”唱片好得多了,但是印象却好像已不如当年那么深刻了,就只是一个音乐作品而已。当年为什么会那么喜欢,那么神往?真是很难说,也很难想象了。我觉得在童年和青春期接触的东西,无论是什么,都会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听音乐的确是我的一个习惯,我画画的时候喜欢放音乐,把音乐作为背景。我还收集了很多唱片,但是我并不是一个极端的音乐爱好者,或者说是“发烧友”。欧阳江河在成都的时候,我经常和他一起听音乐。但是我看他也是假的,他经常好像真的跑过来和我听一个曲子,但唱片一放,他就开始说话。你想,他的声音竭力想要盖过音乐的声音,就弄得我必须很大声地应答,结果每次跟他一起听完音乐的后果就是我的嗓子都哑了。后来他离开成都之后,就再没有谁来跟我一起听。所以现在音乐仅仅是我身后的一个背景。像原来那样坐下来认真地放一张唱片,然后仔细品味它,而且还对它做出评价,这个时代好像已经过了。
实际上我在音乐上已经进入这样一个阶段了,就是不光是收集曲目,对作曲家感兴趣,而是对演奏家感兴趣了,也就是对怎么样演绎感兴趣。我酷爱的是钢琴,我的唱片大概有70%-80%都是钢琴的,而且说起钢琴家来我可以说是如数家珍,我收藏得非常多,而且也相当的齐。
你问我为什么这么喜欢音乐,那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确实是用言语无法表达的。我认为对音乐的形容词是最苍白的,音乐是最不可言说的一种境界,只能听,它纯粹是属于听觉的。
我前面跟你说了,我自己还曾经搞过乐器,当知青的时候拉手风琴,但是由于没有童子功,始终上不了台阶,始终是业余水平。直到现在,我对乐器都有一种敬畏之心。比如说钢琴,我就不会去碰它。我的很多朋友在二十多岁、三十多岁时还学钢琴,能够弹一些简单的曲子,我想我也具备这个能力,但我的确不愿意去碰。因为我听的都是一些最高级的音乐,随便拿一张CD出来一放,就是大师的作品。因为听得太多了,觉得自己不能去猥亵它了,所以从来没有起过这种念头。
唐:我觉得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真实”感对你来说很重要。
何:这是肯定的。我觉得我不会……我所有真实的东西都会在画中得到体现,但在其他方面说谎的成分就很大了。而且,我现在认为自己的整个生活跟艺术之间,第一,没什么关系;第二,也不很重要。在生活中我可以说是没有多少顾忌,但在绘画中我仍然是很认真的,而且坚持说真话,我现在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对自己的看法和对过去的看法,都在里面体现出来了。在创作中体现出来的扬弃和否定,虽然别人认为很可惜,认为我这样做很可能会导致一头都不沾,但我就不管这些。
唐:“传统”的和“前卫”的,你是如何理解的?
何:传统就是……中国油画的传统其实根本不存在。在国画里有传统,但中国油画并没有什么传统。最初,在解放前主要是受法国的影响,就是留法的那批人;解放后受前苏联影响,政治对油画影响很大。这些都不是绘画本质的东西。一直到现在,从批判现实主义到最前卫的现代主义,整个过程大概也就花了四十来年功夫,速度非常快,实际上则是一个刻意摹仿的过程,这并不是真正的中国油画艺术的本质。中国油画艺术传统到底在哪儿,谁也不知道,而且以后可能也不知道。艺术这个东西,你刻意地去追求它的民族性,也是一个很恼火的事情。
而我也很讨厌“前卫”这个词 。“前卫”这个词我认为是很不准确的一个词。为什么它叫“前卫”,它不叫“后卫”、“前锋”呢?没有意义嘛。它是大家都把它抓来使用的标准,但如果叫你界定一下什么叫“前卫”,任何人都说不出来。也可以认为“前卫”就是当下对权威和对占统治地位的东西的一种反抗,那么实际上可以这样说,在某些时候某些阶段,我们是最前卫的。比方说,罗中立画《父亲》的时候,我画《春风已经苏醒》的时候,就最前卫,那种反叛不仅是对绘画传统技法的一种反叛,而且是对当时政治生活的一种反叛,这肯定是很前卫的。那么后来像张晓刚他们画政治波普的时候,也是很前卫的,在当时也是一种反叛。现在有什么是反叛的呢?现在一切都官方化了,任何一个东西,不管是啥东西,到出来马上被观众、被评论界争先恐后地认可的时候,哪里还谈得上任何反叛呢?所以说,谈“前卫”这个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也不愿意使用这个词。
唐:那么你现在坚持的这种“两头都不讨好”的状态,可不可以也看成是一种反叛呢?
何:当然可能。对每一面都有可能是一种反叛,是不是?现在保守点的就觉得我追求前卫去了,前卫的又认为我仍然是很保守的。可能他们就是这种看法嘛,但 “我属于哪一类”这种归属感对我来说不重要。当然我也希望人家认识我,需要人家喜欢我的画,但是人家如果不喜欢,我也没有办法。我就做这个事,我就只这样画。对于我到底归于哪一类,我完全不去管它。
我觉得现在给中国绘画贴标签是非常牵强可笑的事情。我前段时间跟一个美国主持人谈论这个问题,他说现在画画都不能叫前卫了,现在前卫就是搞影像之类的,甚至连影像都会很快被翻过这一页。现在只要画画就不能叫前卫,大家争先恐后地去刻意求新。这个时代,你只要还在摸画笔,你就已经很保守了,你不能再以画画来表明自己前卫,画画这个前提在“前卫”中是不存在的。“传统”、“前卫”往往说起来很有道理,但实际上你要是去分析的话,你找不到任何界定的基础,没有标准可以界定。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一点都不重要,我也不关心这个问题。
就我个人的情况来说,也始终是被认为游移于这两者之间。罗中立的《父亲》得金奖的那个展览,我的画是落选了的。我画的是《我们曾经唱过那首歌》,这幅画落选了,落选原因就是它的不确定性。罗中立主题很鲜明,我的主题就有不确定性,他们说你唱的什么歌?不确定,很含混,这个画面也很含混,充满了光斑,有点像点彩派的画,所以那时候这幅画就没能上展览,被枪毙了。后来我又画《春风已经苏醒》,当时好多人看了就说,你画的什么啊?没有故事,没有情节,画上看不出任何东西。但是由于这幅画我采取的画法是怀斯式的那种精细刻画,草画出来后密度很大,细节很丰富,因而被认可了。实际上我的画,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别人距离很大。罗中立他们的主题,是在中国大的政治背景下的一种判断和表现;我是相反,从一开始主题就很含混。我在《春风已经苏醒》里画了个小女孩坐在草地上,表情茫然,一条狗一条牛,都很茫然,草是枯草,没有任何背景,除此之外,是非常简洁的构图,刻画精细构成了很大的密度。这幅画的标题《春风已经苏醒》是从歌德的一首诗来的,第一句就是“春风已经苏醒”。我引用这句,是因为当时我还很喜欢浪漫主义诗歌。这是我赋予它的一个题目,我也可以把它命名为任何一个题目。我记得当时还写了一篇文章,我说实际上“春风已经苏醒”这个标题把人导向一个抒情的境界去了,但实际上呢,我画的就是一个人、一条狗、一头牛。当时还有人批判,说我这个看法是一种纯客观主义,没有任何价值。其实当时我已经在说老实话了,虽然当时我加入了抒情性的情怀,但是这种抒情性也可以马上消失,那只是我赋予它的一种东西。我还记得陈丹青当时画了几个藏女洗澡,是叫《沐浴》还是《洗头》?是在他的西藏组画里的。他说,反正时兴画裸体嘛,我也来凑凑热闹。其实他当时就在说老实话了。我的画没有什么情节,和他们比起来没有什么情节。从一开始,我的画就非常个人化。整个90年代,我的画非常个人化,跟他们没有关系,而且始终没有政治性背景。
我参加全国比赛的第一个作品《追穷寇》,是以解放军过长江解放中国为背景的,那就一下子被认可了。后来我脱离政治背景以后,就既不被中国美术界所认可,也不被西方美术界所认可,尤其是不被西方美术界认可。然而被西方美术界认可,这个对中国美术界是最起作用的。自从官方对艺术的控制之后,西方便成了中国艺术的一个新的仲裁者。原来是官方作为仲裁者,现在是西方作为仲裁者。西方标准是中国艺术现在的唯一标准。从80年代到现在,一直是这个样子。
而西方对中国的标准还是东方主义的一部分。他们认为在第三世界国家,比如中国这种国家,政治在生活中的作用非常大,因此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你需要国际认可,那么这就是你应该做的。那么你如果追求一种纯艺术性,追求一种全人类共有的东西,他们就认为不是你该做的事。为什么中国政治波普到现在一直是中国艺术的主流,就是这个原因。并不在于画得好,西方人不管你画的技术这类东西,他才不管这些,画得好是他的事,不是你的事。他要求你现在首先要讲政治第一,要表现生活,要体现民间疾苦,所以说他们对中国画家的要求仍然是意识形态的,而中国画家似乎就必须依照这种判断标准来工作。所以我的画从整个90年代一直到现在都处于一种非主流地位,我其实很想当这种角色。我并不想在风口浪尖上,我始终想让自己处于这种非主流的地位,边缘角色。虽然我的画在整个90年代影响了一些人,有名气,但是评论非常少。评论家也觉得没啥可写的,评论家也要考虑自己,他们也晓得这点,所以说他们一看到政治波普马上就可以写了,觉得这才是中国。
唐:他们可以找到话题?
何:对,可以找到话题,找到迎合艺术界强权的话题。实际上中国艺术界还是西方的殖民地,我仍然是这样看的。1985年我在美国波士顿艺术学院讲学的时候,我把我的画的幻灯片放出来,学生们看得云里雾里的,后来放到《青春》,他们就觉得和“文革”有点关系了,马上牵入“文革”问题,我就只有回答关于“文革”的问题,根本跟艺术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始终就是这样界定我们的。
郭伟在美国帮我买了一本《观念绘画》的画册,它基本上囊括了现在还在画画的艺术家的重要作品,代表了当前绘画界现状。它的前提是绘画,不是行为,也不是装置。这里面有两个中国画家出现,一个是一位抽象画家,抽象画始终是西方的一个很重要的门类,但在中国画抽象画的很少,所以他们选了。第二位画的还是毛主席、样板戏什么的,还是这种东西,因为西方仍然坚持这个标准。他们认为,即使你画得确实好,但这些东西我也能画。你们中国人就应该画你们的生活。
所以说我一开始,从画《春风已经苏醒》开始,就不会有那种轰动效应。人家看我这些画,最多觉得很有诗意,或者说画得很好,人家不会去想它后面的什么政治背景。而像《父亲》那样就很重要,把中国的农民几千年的苦难一下子就全部加进去了。我始终是一个喜欢画画、而且喜欢画得好的人,我也喜欢画得好的画,而不喜欢那种虽然主题很大,画得却不是很好的画。所以说,在中国,不管在哪个背景之下,无论是官方在鼓励主旋律,还是西方在定义一个主旋律,这两个主旋律都没有我的份。我始终处在中国美术潮流的一个边缘位置,这一点我倒也很喜欢。我愿意去充当这种角色,而且我自己有满足感,我觉得我画得好,我是有实力的那种人。
唐:当年你和罗中立一起去参加那个展览,罗中立画的《父亲》入选了,而你的画《我们曾经唱过那首歌》落选了。当时,当你知道自己落选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呢?有什么感觉?
何:呵呵,当时的感觉就是有点气嘛,骂了一顿嘛……
唐:是骂评委吗?
何:哦,骂评委骂领导。因为当时落选的理由很怪,他们的理由是:《我们曾经唱过那首歌》,唱的什么歌?没有说清楚,万一唱的是资产阶级的歌呢?在当时那个政治背景下,这些问题都是必须要说清楚的。其实那幅画已经体现了我的一贯风格,就是情节模糊。虽然说有一点情节,但是情节非常模糊、含混,可以做多种解释。这就很恼火了,领导可能想到别的方面去,然后觉得“不宜展出”,就给我扣下来了。我想如果展出的话得个三等奖是能得到的。但我也没有很生气,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些事情还更计较一些,那个时候不怎么计较。当然后来我在王川的怂恿下写了一封信,写给中国美协主席,告四川美协的这个领导,写的什么内容我都忘了,王川,好像还有杨谦,我们联名写的信。信寄给中国美协的领导后,他根据当时的一贯风格:“批转给某某同志处理”,你告的谁就转给了谁,于是就转到了四川这个领导手里,你可以想象一下后果。我想我在美协一直有点背运就是这个原因,但我简直无所谓。我现在记得当时他们到北京去拿大奖,拿各种二等奖三等奖的时候,就是 1981 年全国青年美展那次,四川的画家都去了,除了我。我一个人留在美院画了《春风已经苏醒》。
唐:其实你对你自己的技能还是很自信的。
何:很自信,确实很自信。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技能。
唐:不会寄托在评奖上面?
何:那是。我在绘画中基本上还是可以叫做无所不能,随便画什么。虽然我没有画过国画,但我相信画起国画来也很可以。而且到现在为止对评奖那个东西我仍然是一笑置之的,我到现在都认为若要得奖我不愿得一等奖,得个二三等奖就是了。到后来也的确是这样,我得的都是二等奖或者三等奖,因为我的画确实就没有政治背景。有些评委觉得,你什么都好,但你不是主旋律,所以你就只能得二、三等奖。我很满足于这个状态。我觉得二、三等奖从很多方面说来都是一个最好的状态,一个人不要中头彩,中点小彩就行了。中了头彩就像“肥猪”一样,任何问题都来了。
四 技巧的魔力
唐:我曾读到对你的画的评论,说你的绘画具有“文学性”;你自己也有“我过去强加给画面的、强调的、赋予画面的文学性、诗意”这种说法;然后我又看到说某些人的画具有“绘画性”。我不懂这个“文学性”和“绘画性”的含义到底是什么?
何:我理解的绘画性就是……比如说印象派的画,它就很有绘画性,就是说它的题目不重要,主题也不重要,它是通过绘画本身来打动人。比如说我画了一束花,就是用怎么画这束花的技巧和表现出它的美感来打动人,而不是这束花背后所隐藏的某一个故事。另外一些作品它就需要有一个故事,这些故事很重要,画得怎么样反而处于次要地位。前一种画就可以认为是绘画性很强烈,后一种画就可以认为是文学性很强烈,情节性很强烈。一般是这样子来看这个问题。但界定也不是很准确、很清晰,同时也不是很重要。
唐:那你认为在绘画当中更重要的是什么?
何:也可以说是绘画性,就是画本身。
唐:一幅画本身是由许多东西所组成的。
何:是啊。韩东不是说过“诗歌到语言为止”吗,这就把写诗的语言技巧提到一个很高的地位了。对我来说,绘画也是到技巧为止。实际上技巧最重要。当然关于技巧有种种说法,涂鸦是技巧,精雕细刻也是技巧,但高下是一目了然的,我可以看出哪几笔画得好,另外哪几笔就画得不好;或者哪几笔画得很匠气,哪几笔画得很灵气。这些都能看得出来,至少是圈内的人、专业的人看得出来。
唐:技巧本身反映的又是另外的东西了吗?
何:是啊,但它反映到画面的时候,又仍然能提供一些因素。比如说毛焰的画,他用了一种很专业的技巧来画,但他表现出来的东西非专业人士也能看懂,就是他画出来的画面的那种密度啊,那种控制啊,别人看了也很喜欢,觉得画得好,好在哪儿人家又说不出来了。专业性很强的绘画性就是这样的。我觉得我的画就很有绘画性,也许有的人不这样认为,但我自己认为很有绘画性,我是典型的“绘画”。
唐:技巧还是要表现一些技巧之外的东西吧?
何:当然。但我认为表现的东西越不确定越好。就是说让人家在你的画面前无话可说,但看得出技巧高超,这就可以称为一张好画。
唐:你认为绘画到技巧为止,那么你能不能谈谈技巧和技巧之外有什么不同,主要从你的一些代表作,比如《春风已经苏醒》、《小翟》谈起吧,谈谈各个阶段你是怎样探索的、实验的,以及它们之间的某种递进关系。
何:《春风已经苏醒》那幅画在技巧上实际上是很拙劣的。当时我看了怀斯的画,印刷品,印得很差劲。我是看到了他的画上密度,所谓密度,具体说来在他那张画上就是草地,一根一根的草中间没有间隙,它没有虚的东西,都用同一种强度把它表现出来了。那种密度是前所未有的,因为过去传统绘画包含很多虚的部分,它却是一点虚的东西都没有,绝对的物质化,我看了感到很震撼。可能我的潜意识里有物质化的倾向,我想表现它,所以我也刻意去画那一片草地,但我的画法非常不对,有多少根草我就要画多少笔,甚至是一根草上画很多笔。你可以想象一下我的速度!这幅画画了三个月。很笨的一个技法。
当然后来我就不这样画了。画《老墙》的时候,我就开始做肌理,先做预设的肌理,也是密度很大,但那个密度是我人工做出来的:我先用刷子一刷,刷子的纹理正好跟墙的纹理吻合,再将很薄的颜色上上去,然后一擦,把突出的擦掉,沉到纹理中的就留下来,就很像墙了,就产生了一种自然的错觉。而且实际上这个错觉产生的因素和墙本身很接近,只不过对墙来说凹进去的肌理我就把它画得突出来了,它们实际上是一回事。我就是重复这个过程。墙的质感有个物理过程,要过很多年,风吹雨打,风化形成的,而我是人为地在画布上做出来的,于是我画的速度就提高了很多。
当然现在我也没有用这个方法了,我用其他办法,觉得这样更直接:我用笔,用笔本身在光滑的画布上画出来。我觉得这样就绘画来说更本质一些,更接近国画意义上的写意了。松,非常之松,不像原来用某种预设的、做作的办法,现在更为随意了,收的时候又能把它收到一个我限定的框架里面。
我认为我现在的技巧是比原来高得多,现在也有很多人认为我比原来画得好,他们也是那些比较重视画得“松”的人。以前的画法比较“紧”,这个术语在绘画中经常被使用,但我不晓得行外的人理不理解这个意思,就是刻意求工。而“松”就是那种信笔挥来,看似漫不经心,实际上达到效果,类似“笔不到意到”。
唐:比方说你画墙时候的那种技法,是你自己本能就感觉到的方法还是学来的?
何:这是我的一个发明,在中国艺术史中是我的发明。原来也听说过,像早期的画家,如伦勃朗等人,那时也经常在画面上做点肌理,但我们其实没有看过,老师也没教过。我这个技法在中国美术界没有任何人用过,是我自己发明了这个办法。这个东西后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吸引了一批人采用这个办法来画,但有的人把它庸俗化了,把它又变成了一种新的八股文,新的刻意求工。我觉得任何一种画法都是看使用它的人,还要看他的灵气,没有灵气的话,仍然是一个很笨的办法。现在我也不用这个办法,但在当时的中国艺术中确实是原创。后来我参加一个学习班,在中央美院举行的一个法国画家的技巧讲座,我发现他讲的那些我已经用过,就是多层画法嘛,我早就用过了,只不过用的材料不一样而已。
唐:我插一句,你说过你很早甚至在进美院前画得就很成熟了,那些绘画技巧都是你自己琢磨的吗?
何:的确是自己琢磨为主。我觉得阅读始终是我学画的一个很重要的属性,以至于我后来看到原作的时候,反而觉得不震撼了。因为原作很多不如印刷品那么漂亮。当然,原作可以提供一些技法,但我看那些技法也不是很陌生。
我想我对技法的训练,自己琢磨的成分相当多,做底子,多层画法等。这个多层画法我到现在实际上还没看到先例,包括我看原作,也没看到过先例。而且我从小不喜欢临摹,都是在画的时候,把我喜欢的一张画,想模仿的那张画摆在旁边,用这种办法来影响我,但我并不打算临摹它。我从来不临摹。
当然也找老师指教过,但说实话,从老师那里得到的东西并没有从阅读中得到的东西多。一直到现在,阅读都是我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很广泛地看画册,而且,有些画就成了我的标准了。比如,当初看雷诺阿和谢罗夫这两人的画,他们也画的是女性。谢罗夫画的女性肖像很高贵,气质高雅,笔触和色彩都很漂亮;雷诺阿画的形体、光线都更美。这两个人的作品是我看了后马上奉为标准的,觉得就要画成这个样子才叫画家。这种阅读很重要,哪怕我现在不看他们了,但仍然是一种标准,仍然是我认为没达到但很想达到的标准。技法是我从头到尾都在追求的一个目标。
唐:先是说到技法也没有一个恒定的刻板的标准……你说“到技巧为止”,那么后来有很多人都掌握了你说的技巧,但是他们的画和你的画还是不一样。
何:简直不一样。这个跟使用它的人有关系。
唐:就是技巧之外的因素?
何:对。就像给每个人发一支枪,有的人就打得中目标,有的人永远都打不中,有的人还能打中更远的目标。比如我们用同一支笔,都用同样的颜色去画,方法也很接近,但画出来的东西千差万别,有好有坏,这就是因为掌握技巧的人区别太大了。我看到圈中好多人对自己的技巧保密,我从来不保密,我经常是又写又说,完全不在乎。我觉得你可以来照着我做,可以临摹,照着我做什么都可以,我无所谓,反正我晓得你做出来的肯定和我是两码事。
唐:刚才说到了在画《春风》和《老墙》时的技巧方面的摸索。那么你能不能再具体谈谈,各个阶段中你在技巧方面的摸索。你在创作上还是有阶段的嘛。
何:《春风》、《老墙》……包括《小翟》,整个90年代都是做了肌理的,但是不会像《老墙》那样,刻意地像做浮雕一样地做一堵墙出来。
唐:为什么没有人讨论技法呢?
何:现在很多人认为技法也是一个需要保密的东西,很重要,就跟注册一样。现在无论任何一种你自己独到的东西,或者是符号上的东西,或者商品性的东西,你都要注册,然后要保密。因为一旦你教给人家,被人家学会了,你就不是独一无二的了。这在现在的绘画界是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同行之间不会问:你这画是怎么画出来的呢?所以我也遵循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行规,从来不问人家是怎么画出来的。但是人家一旦问我,我就会和盘托出。我无所谓,我觉得我的方法你也可以用,反正效果就不一样。我还把我爱用的调色油到处向别人推荐,结果很多人根本拒绝使用这个东西。
关于风格,有一种说法是:风格是技巧上无法克服的困难的总和。这样说让人很费解,那如何去理解这句话呢?我是这样理解的:当我画画到了继续不下去的时候,那就是思想的极限、风格的极限,在这个时候你的风格就形成了,所以说它是“困难的总和”。就是当你已经无法再前进一步、当你所追求的那一切到了极限的时候,你的个人风格就形成了,而且很强烈。
唐:但实际上你的风格一直在变啊?
何:但我有个一脉相承的东西啊。人家仍然认得出来是我的画,还不光是题材上,我用不同技法画的女性很多,技法变化也很大,但任何人都认得出我的画,就是这个原因,就是始终有这么一个追求到极限的东西。
90年代我也有一些过渡时期的画,没有追求到底,我自己不满意,人家看了也不满意。那些画我一般都不发表的,那是一种过渡性的东西,绘画技巧上没有追求到底,这种没有追求到底的东西一下子就能看出来,能看出这种画在技巧上不成熟。
所谓追求到底,我并不是指都要照我的画这样,用很长时间去精雕细琢。其实一个人即使信手涂鸦,只要他到位了,他的风格也是追求到底了的,他的技巧也是追求到底了的,那也是一种成熟的、无法复制的技巧,而且也到了极限。所以不是说非要花很长时间画,我恰恰不是指这点,如果指这点的话我就傻了。我的意思是,任何东西它都有一定的极限,如果一个人走到了极限,他就是比较幸运的。
五 题材
唐:从你作品的历史来看,好像题材范围非常狭窄。但从绘画的组成形式上看,你好像又相当广泛。比方说你早期的一些作品,还有一些油画速写风格的作品,或者怀斯风格的东西,后来那些带有中国情调的系列,现在主要是一些人体画,等等。中间你甚至还画过连环画。总结起来看,题材的相对狭窄和技巧的变化多端显示出一种矛盾。现在很多的画家,尤其是青年画家,他们一旦确定了个人符号之后,总是可以维持很长时间的稳定,把这种符号不断地重复、巩固和强化。但是好像你并没有这么做,你好像总是不断地改变,除了90年代那一次大的放弃之外,你在这中间不断地放弃一些东西和转向一些新的方向。你觉得这种现象显示了你在方向上的犹豫不决呢,还是你是有所考虑的?,
何:的确我的画有这方面的矛盾:一方面是题材范围极其狭窄,另一方面却是绘画的手法和体裁比较丰富。这说明我在绘画上的适应性还是比较强,也就是无论哪种手法我都可以尝试,而且我很快就可以掌握它,因此那种符号上的转换对我来说就没有什么难度,而且也不重要。我可以自由地采用种种办法,只要我觉得需要,就可以天马行空。但是另一方面你提到的关于重复的问题,的确在这一点上,我有一种犹豫的东西。我可能还没有像你所说的其他人那样,找到一种真正的、我说的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完全独特的符号或者手法。如果我找到的话,也许还是会坚持一段时间。这当中包含一种自我怀疑在里面。
可能我还是一个好动的人,如果要让我长期地从事某一种方法,就像现在看到的其他很多画家,我觉得他们画画已经丧失了乐趣,长期地重复,类似于工厂的定量生产,这在我看来,跟把绘画作为一种乐趣的态度是背道而驰的。当然,其实是我自己缺乏耐心,一种必要的耐心,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巩固和强化自己的符号是很重要的,我没有去好好做。但这是一种策略性的问题,我现在还不是太考虑这些问题,我更愿意自己兴之所至。
你说到我画连环画,的确,这个形式好像跟我的特点是矛盾的。我的画的感觉是没有情节,没有文学性,但是它有一种……有一种诗意在里面。一种隐喻的诗意。所谓诗意是一种不用说出来的很含混的感受,而文学性是有明确情节的。但我的绘画正是缺乏情节。
那为何我选取连环画这个题材呢?我一共画过两部连环画:《雪雁》和《带阁楼的房子》。它们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它们本身都没有强烈的情节,而且它们都表现了一个孤独的男性和另一个孤独的女性之间的关系,它们的结局都是不了了之的。也就是说,我所说的这种关系:两个孤独的人之间并没有真正找到一个切合点的这么一个关系,也许正好是我潜在的兴趣点吧。
《带阁楼的房子》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契诃夫的这部小说是我青年时代特别喜欢的,也许那时我还是一个比较浪漫的人吧,所以那种充满浪漫主义的小说,我非常喜欢。我更喜欢的就是它里面那种朦胧的、惆怅的诗意。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这代人共有的俄罗斯情结,我始终想在绘画上去表现它。这部小说中的主人翁是以列维坦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