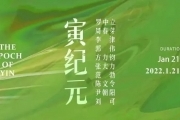2009年第53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徐坦的参展项目“威尼斯关键词学校”
记者:在维他命空间中展出了您在90年代的一些读物,有文学、法律之类的。
徐坦(徐):我读文学的书并不多,那时候(90年代)读了一些哲学、社会科学之类的书。
记者:现在还在读吗?
徐:现在还在读,但是读得不多了,因为我读书很慢。
记者:是不是对法律类的书比较钟爱?
徐:不是的,在现场的这些书是作为1995-1996年《问题》这件作品的创作背景而呈现的。那个时候讲国际化、与世界接轨,这件作品是谈国际法、土地占有问题的,是出于我个人兴趣而做的。这件作品做完之后我觉得很失败,但维他命空间出于连贯性的考虑又把它重新提出来。
记者:作品失败在哪?
徐: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一直讲法制,要向国际规范学习。社会上经常会谈及“民主与法制”的问题,我们以为有了法律就意味着有了公正和秩序,那些民族纠纷、土地等问题就都能得到解决。我那时读了一些像法律史一类的书,也试着以做一些与法律、物权和占有等相关的作品来理解现实中的问题。但后来我发现,从逻辑上讲,关于占有的法律是不合公理的,是不合逻辑的,它并不能像我们期望的那样很好地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我想通过推理并且辅以视觉艺术呈现,以达到对占有权法律的合理性认识,结果失败了,这个作品体现了这种失败,所以后来干脆不去想它了,甚至想把这件作品忘掉。
记者:这件作品的思路和方法与后来的“关键词”项目是一脉相承的。
徐:刚开始有点类似,但后来“关键词”项目也出现了一些转向。“关键词”项目刚开始学习借助了一些社会学调查、统计的方法,有点模拟社会学研究,想通过语言分析研究来了解社会的意识活动。后来在项目推进的过程中慢慢了解到,这样并不能深入个人的或者社会的意识活动,所以在后来的项目中这种方法用得少了。
但是,在回顾的时候意识到,在早期创作中和现在工作中的相似性在于,认知和表达的一致性要求,既:认知活动一直是艺术活动的重要部分。
记者:但很多人会觉得统计学的结果会相对更科学、更理性一些。
徐:这里有一些误解,如果要很理性地讲一句话,统计在很多时候是无效的,它只是提供一些比较定量的东西来做参考,但语言领域有很多不确定的内容,所以统计的方法在这个方面有时候并不好使。
记者:法律、语言是人们制定的一种规则和社会规范,反过来又对人们形成一种制约力,有时这种制约是无意识的。
徐:我没有接着1996年那件作品继续往下做,因为后来我发现法律是低于社会政治系统的。比如中国和美国,政治制度不同,关于土地占有和使用的法律就不同,中国的农民是没有地的,所有的土地都是国家的,政府掌握土地的所有权,人民只有使用和租用的权利,并且有期限。中国古代也是可以私人拥有土地的,但现在就不可以。所以说法律是在其所属政治体制支配之下的,而且这并不是一直不变的,你在认可或执行具体的法律的时候,就相当于你默认与其相连的政治系统是合理的,也就是你接受了这个法律之上的政治系统。另外,具体的法律在判断和实施看起来似乎合理性是最重要的,而与之相连的政治系统则建立在意识形态信念上,这种情况是没法用理性分析的,并且不管合理不合理它都在那里,对你的所谓理性思考是一种制约,也就是说,理性的法律,建立在非理性的政治系统之上。
记者:社会植物学这个项目做多长时间有预期吗?
徐:想的是三年吧,现在已经做了一年了。但这个也不能确定,因为它是开放的,我在以前的讨论中说过:关键词项目就像一条一直流动的河,会有不断的结晶物,就是这些展览和所谓的作品,但最终什么时候结束,会到达哪儿都不能确定。它是一个过程。
记者:为什么是植物,而不是别的“社会××学”?选择珠三角作为考察区域是出于什么考虑?
徐:主要是我个人的原因,2009年某个时候,我觉得继续像主流艺术家,以追求名利的方式生活有虚无感,我想做一点我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当我回到住的地方,在家后面山上散步的时候忽然觉得,在名利生涯之外我们是否应该用另一种眼光看周围的世界,我周围有很多树,我居然一棵都叫不出名字,我很无知,自己被绿色包围,离它们很近,却也很远。另外我有哮喘,对花、草等植物比较敏感,所以一直向往较舒服的自然的环境。但我们周围接触的自然都是人工种植的,是园林规划部门规划、设计的,这是一种社会性的植物,不仅不是原生态的自然,而且是非常年轻的自然,其后果还有什么现在还说不清楚,但至少造就了一种单一化的植被环境。
记者:这或许跟您考察的范围有关,您考察的以城市中的植被居多。在这之外的其他地方的植物会不会是另外一种状态?
徐:我考察的主要是华南珠三角一带,但从全球来讲,原生植物都在减少。我去过多伦多的一个郊区地方,两百年以前那个地方都是树林,那时的地方法律规定,只要你开垦一块地出来并且保证它不会再次荒芜,就可以拥有在那里居住的权利。当我去那里的时候已经不是这样了,以前的人们是需要努力在森林开垦并且维持一小块地,作为人的存在标志,而现在那里只剩下一小块树林,成了受保护的自然公园。在珠三角,这里原本没有多少原生态的植被,现在是次生植被也难以保存。
记者:在OCAT的那个展览是请人在展厅中搭建的小屋里做访谈,而在维他命空间展出的访谈是录像形式的,内容是实地考察和采访的过程,呈现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徐:OCAT展览是关键词学校的一部分,在展厅中搭建一个交流平台,或许可以说勉强像所学校。现在的“社会植物学”是关键词实验室,这个现场已经不仅仅是艺术品展示的地方,它与外界有更多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实在的,有一种向外延伸的状态。
记者:您在实地考察中接触的是实在的、具体的东西,而展厅中呈现的录像虽很详实,却也难免显得单薄或生硬,像是呈现了某个球体的一些断切面,包括录像角度等的选取和裁剪都是刻意为之的,从实地“搬”到展厅的过程中还是有很多关系发生了变化的。
徐:是的,我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研究的形式和呈现的形式不重合。问题是我们研究的是什么?给观众看到的又是什么?这种不重合的情况不断出现。我们在展厅里搭建一个实验室的平台是为了我回去不断工作,那么这种所谓研究性的过程要不要给观众看,这也是个问题。
记者:您需要不断回到展厅中工作是指哪方面的工作?
徐:我们做某个访谈的时候是以单一线索进行的,而我们有时候需要同时观看这些不同线索的东西,就像有的人喜欢同时摊开几本书阅读一样,这种同时性的观看带给人的感受跟平时我们习惯的那种单一的观看是很不一样的。我在展厅中可以同时对着几个屏幕观看,也可以在几个屏幕间切换,这样才是一个实验室的状态,因为在家里不可能有那样的条件让你同时观看几个屏幕。
记者:从实施者的角度讲,这种同时性的呈现与您具体实地考察中线性的工作模式最直观的区别是什么?
徐:我的考察工作还不是单一的线性模式,它是交叉的线索和循环,对每个人一到两个小时的访谈你要反复回看,你不仅要看这个人的,你还要反复看与他相关的别人的访谈,这就是一个铺开的过程。比如我们会反复问这些人种植的感受,他们都会说挺好,但要深入下去了解为什么好的话会牵扯到很多问题,比如古代人们对于种植的态度,还有现在一些西方人对于种植的不同看法,而且有这种“挺好”感受的人不在少数,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所以对这种现象要摊开去研究。
记者:在某些录像的旁边或屏幕上有提取的文字关键词,在这里面有没有一种自我预设存在?假如“政治”、“集体”这些词汇是你比较重视的,那么在采访中你就会有意地关注这类关键词,或者在别人的弦外之音中捕捉这类符合你预设的关键词?如何确保这些关键词真正是采访内容的关键词,而不是您个人的关键词?
徐:我们先回到以前的关键词学校项目,别人总会问我如何把关键词确定出来。而如何确定关键词,对于每个具体项目都是一个问题。我一般都会:先把每一句话看成一个结构,这个结构里有一个到数个要点,我就把这些要点看成关键词,这是普通关键词。在普通关键词基础上我再做四种不同的统计,第一种就是出现次数多的词,比如一个小时的访谈下来会有好多个重复的要点,这个就是高频率关键词。比如中国艺术家说“社会”比较多,西方艺术家以前是不太说的(现在也说得比较多了)。第二类是敏感词,比如六四、民主之类的。第三类是流行词,跟现在的网络用语、流行时尚有关。第四类是不在场的关键词。比如我曾经做过一次活动,采访近三十个中国当代艺术家,我预设“自由”会是个高频词,采访完了以后,发现“自由”只出现了一次,这挺奇怪的。大家都不说这个词,我觉得很有趣,我想不是这个词不重要,而不说会有其他原因,我想这就是不在场的关键词。当然,由于这种自我预设的暗示,主观是不可避免的,有的时候有些关键词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我自己的关键词,而不一定是别人的关键词。在近期的项目中往往会产生我杜撰的词,比如“社会植物”、“社会植物学”,我会把这类词看成项目性的关键词。
我们现在也还会使用提取普通关键词这道“工序”。但在近期的分析中越来越少用那种接近统计式的方法来做,而是尝试其他的办法来深入。
2011年在深圳OCAT当代艺术中心“可能的语词游戏——徐坦语言工作室”对话现场
记者:录像中屏幕上的文字关键词可能会对观者形成一种引导和暗示,有没有想过去掉这些文字的关键词,仅仅将多屏幕的访谈录像呈现在那,让观者自己去把握哪些是关键词或他所理解的关键内容?
徐:与文字的关键词相比,我还是认为视频的关键词更重要,但实际工作中要反复大量回看录像,有时录像在提取和筛选关键词方面比较弱,由于工作量大,文字表达的话就相对简单很多。你讲到的没有经过关键词提取的视频,我称为素材。随着剪辑(分析)增多,关键词就会越来越少,这是一种不断精炼的过程。这个展厅效果的呈现我认为并没做得很好,至少是没有足够的可视性的、言说性的关键词。
我现在经常做的以讲话方式的写作,称之为“可视性言说写作”,我最近一年时间一直在做,当我想写东西的时候就打开摄像机,对着镜头录下来。
记者:对受访者的谈话内容进行关键词提炼的过程,其实也是一种将口头谈话转变为书写文字的过程。但语音和书写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中介,在这种转换过程中什么发生了变化?这种提炼的过程也是将关键词权威化的过程?因为人们更愿意相信概念化和可视性的语言,即“白纸黑字”的语言。
徐:言说性的语言与写下来的文字语言是不一样的,人们更愿意相信书,那是历史原因造成的,而不是书有天然的权威。现在有了电视和录音、录像,实际已经开启了另外一种书写的方式。我们平时讲白纸黑字是要负责任的,但是写下来的东西往往损失掉了很多意识的活动,那为什么不让两者并存呢?就像看电影,如果可视的、言说的语言和书写的文字没有区别的话,那我们就直接看完剧本就可以了。所以,在语言,其语气、表情,以及环境的关系就变得很重要。
我采访一个老农,我们问他是不是种田很辛苦,他笑着说那当然咯。因为他是笑着说,我就继续问他是不是很享受,他说也不是。所以这个笑就很有意思,会带来一些疑问。我们继续追问他是不是“悠然见南山”,他问什么是“悠然见南山”,他说不知道陶渊明是谁。他说自己干了一天活,出了一身汗,到了傍晚斜阳西下,感到凉爽,感觉挺自由的。由于我们很少会把老农和自由联系在一块儿,所以我们觉得老农说的这个自由值得注意,跟老农的对话以及周围的环境会令我注意这一点,而这个自由是否是西方概念上的自由?
再接下来分析,以及联系性阅读(汉娜?阿伦特),并对比西方的政治哲学中关于“自由”概念的历史过程和老农所说的“自由”,于是在我的思索方面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空间,我觉得我应该在老农说的这种自由的前面,加上“动物性”,这就出现了一个我的关键词:“动物性自由”(这里没有任何贬义,这和“人是政治动物”一概念有关)。
这些都是在访谈的过程中才会有的微妙的感受,你需要从这个氛围中去体会,如果只有文字我们估计就不会想这么多。
记者:您在维他命空间的展览“问题,地—土和社会植物学”,其中“地—土”为什么要用这样的形式来表示?它与人们惯常理解的“土地”有什么不同?
徐:这个其实挺简单的,“地-土”是两个事情,“地”是土地,“土”是土壤。如果我们直接说“土地”的话,这两个层面的意思就又变成一个了。其实就是为了与这个相区别,指出所要关注的是两个事情。
记者:说到“植物”就会涉及到“土地”,在维他命空间的展览中有一份土壤成分的分析报告,这种分析是不是更侧重量化的成分?
徐:之前用统计学方法的时候是量化比较多一些,现在逐渐地就少了,适当的量化是必要的,但如果依赖于这种方法就有问题。我们对土壤的分析检测,刚开始检测公司说这些土壤有三项指标有问题,其中一项的问题还很严重,他们没有说明这项严重问题具体是什么,只说需要重新测试。过了两周,他们通知维他命空间,那个问题严重指标的重新检测结果出来了,很正常。但是我们很难相信这个结果,并不是故意去怀疑,就是很难让人信服。所以量化的方法也是有问题的。
记者:后来这个成分分析的报告还是展出了。
徐:对,我让工作人员把那份正常的检测数字展出了。
记者:您让维他命空间租用了两平米的“试验用地”。100年显得有点遥遥无期,因为现在的社会二三十年就已经变化非常大了,这个听起来像“两平米的乌托邦王国”。
徐:以前我和城市规划设计师有往来,今年年初哈佛大学一个城市景观设计专业的教授带着一帮研究生来黄边站做交流。在这过程中,我们感觉到,人们相信,我们人类有能力设计一个越来越好的世界。我对这种自信十分怀疑,这事实上是资本逻辑的体现。
我们的受访者中,有个人打理了一个私人庄园,他每天都去庄园里“享受自然”,我问他,你这里的植物都是经你手种的,这算自然吗?他说那有什么办法啊,这些植物虽然都是我种的,但我把它们种在那里不去管它了。“有娘生无娘教”,那片地过了一段时间变得茂密而“荒芜”。野草野树比他自己种植的树长得还要好,几乎要吞没他种的那些树,在这里他就能感受到一丝丝自然了。我从这个例子中感觉到,自然恰恰是人不可控制的那部分世界能量。像我们城市中的植被,被整齐划一地规划种植和修剪,一旦有野草就会马上消除掉。这样的自然就是社会的自然,它是可控的,这些树犹如我们人类社会,一旦生长越出规范(我称之为植物行为不轨),马上会被修剪。从最低层面上讲,如果我们人类还需要自然的话,最好让它自己去生长,不去干涉它们的自由。就像我借的那块2平方的地那样,我会留下提议,告诉人们要维护这块地不受控制的状况,但是对这块地的破坏也是我们作品预设和测试的一部分。因为这就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在现在更多地是一种“利用”,所以谁也不敢保证几十年、一百年之后这块地是什么样子。
记者:被采访者坐在摄像机前是什么状态?
徐:中国人(海外包括华人)大多是不喜欢接受采访的,有些是很不好意思。有些私人农庄和庄园都不同意接受拍摄和采访,刚开始他们会满腹狐疑,但慢慢谈开了就好一些了。
记者:会不会影响到谈话的真实性?
徐:这种情况肯定是存在的,或者说任何的采访都会面临这个问题,有的人不会说真的感受,这些我们可能会从他们的眼神、表情看出来。所以有些关键词是需要经过分析之后得出的,从很多不同的采访之间去寻找一种关联性的东西。
这个关键词的项目很庞杂,感觉很多方面都没有说透。但有一点是我比较关注的,就是强调在艺术活动中,认知和表达的同一性,而现在的艺术世界所注重的是表达,在我看来是不够的,认识世界和自我表达是要同时进行的。
记者:但一般情况下,艺术家所表达的世界就是他看到的或认识的世界。
徐:对,但有一个问题,比如说现在的艺术世界里,艺术家越来越趋向于“弱智”,似乎艺术家越来越没文化、说什么做什么都可以被社会原谅,艺术家就象征着一群没文化的人。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家需要做的就是去表达他的感觉,这实际上是不可能带来独立的表达的。
记者:这就是您对今天艺术现象的态度?
徐:达芬奇是我很崇敬的一个艺术家,他就是研究与表达合一的艺术家。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绘画创作时的研究性工作的存在。而现在的艺术家所做的仅仅是表达的那部分,分析研究的那部分已经没有能力做了,因为现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这一部分被社会学、人类学、医学、科学等承担了。但是,我觉得,研究的态度在任何时代和任何情况下都是必要的。
艺术家要做自我表达,应该是不同于他人的自我表达,不仅仅从福柯、拉康、朗西埃这些大师写作中来。艺术家认识的世界不应是从别人的书中知道的,我认为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刷牙、吃饭这些活动对于我们认识世界似乎更重要。
记者:这两种方式恰恰是两种对立的模式,现在很多艺术家都在标榜观念,使自己哲学化。但是这种自我表达的结果(也就是艺术作品的呈现)又常常是很直白化,甚至肤浅的东西。
徐:两种方式:不研究只强调表达,和哲学化表达,在一个问题上是一致的,即都忽视对世界独立关注的建立。哲学化的表达是原本要表达自己对世界有看法,但这个看法又不是自己的,是别人研究的成果,是世界的理论成果,或者说是在大师指导下看世界,所以艺术家很容易陷入一种糟糕的自我表达,是没有自我认识为前提的表达。悖论在于:你前面讲到视觉化是艺术家区别于旁人的一个方面,那么为什么不利用这一点去认识自己所看到的世界呢?
记者:所以您深入实地去考察您所看到的世界。
徐:是的,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是现代教育的产物,但是立足点不同,情况就不同,我们需要阅读,但是应该立足于自己的实践。
【编辑:谈玉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