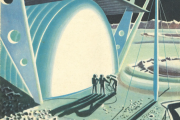卡帕摄影作品《基辅街景》
相比较1936年的莫斯科,显然1947年的苏联首都清洁了许多。194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两年,这个城市里有了很多新建筑以及斯大林纪念碑,但是,进入美国战地新闻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镜头中的人们看上去面呈灰色,一脸阴沉,莫斯科建城八百年纪念典礼上仰望烟花的父子脸上的喜悦仿佛是那抹隐入天空的光芒,脆弱,转瞬即逝。战争胜利后的巨大空虚就是吸入光亮的黑洞。1947年,卡帕的作品中,苏维埃党代表们甚至开会决议,什么样的服装才能出售给本国的女人们。的确,战争结束了两年,前苏联的人民都太累了,被战争、强制性集体化和监视生活弄得精疲力竭。妇女出门都不化妆,那被认为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豪华奢侈品,大部分人的衣服都是廉价的,显得俗气。许多人仍然穿着战争时期的军装,他们也只有这样一些衣服可以穿。
1947年冬天,苏美双方从战时的盟友转变成暗暗较劲的敌对状态。为了了解铁幕后苏联的真实面貌——用当时已凭借《愤怒的葡萄》闻名国际文坛的美国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的话来说,真实展现“伟大的另一面——俄罗斯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苏联人穿什么、吃什么、如何面对死亡”,斯坦贝克和百无聊赖中的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一拍即合,踏上了苏联的大地。两人本着“不刻意表现主管立场,如实记录所见所闻,不加评论,不对自己不了解的事物妄下结论”的中立态度,足迹从莫斯科到斯大林格勒,从乌克兰田园到格鲁吉亚海滨。
但是,在1947年,要看看苏联的“人们怎么过日子”,这本身就意味着一个政治行动。进入这个国家进行实地考察,要么会受到谴责,要么会得到当时斯大林政权的默许,何况扛着照相机的是来自冷战才开始时另一方的新闻摄影记者。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的知识分子,包括罗曼·罗兰和安德烈·纪德、以赛亚·伯林都曾抱着极大的好感去苏联,但苏联发生的事实,终于击碎了西方知识分子的幻想。以赛亚·伯林89岁的生命历程,有两次总计4个月(1945年9月至1946年1月)又4个星期(1956年)在斯大林的苏联。4个月的访问结束,以赛亚的传记作者后来写道:“他(伯林)在离开俄国的时候,心中满怀着对专制的憎恶之情,这种憎恶几乎在他后来写的每一篇文章的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到。”很明显,访问苏联的一路,不是以赛亚·伯林一个人在拜访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还另有一位秘密警察——始终陪伴着他。
1947年,卡帕到访苏联也绝没有享受到他认为应该得到的并崇尚的一切,甚至,那样的阴暗比战场呼啸的子弹更瘆人,它们无声无息,却无处不在。到达目的地的第一天,卡帕和斯坦贝克的行程是由苏联情报机构安排的。他得不到在莫斯科街头公开拍照的许可证,整整一个星期,他请求苏联的新闻官能够允许他拍照。他所去的每一个地方,警察都阻止他拍摄照片,并一再要求他出示证明文件。他无法在莫斯科当一个真正的新闻记者。但他以为总有办法绕开政府的规定,得到有价值的照片。乌克兰和莫斯科的苏维埃档案资料显示,卡帕到苏联后,就处在严密的监视中,卡帕他们不晓得在苏联期间,苏联政府怎样精心策划地跟踪他们。
这样的严密监视,自然无法唤醒卡帕的战地记者天赋与活力,他本会一同迸发的肾上腺激素和同情心无法在画面上体现出来。从他留下的苏联照片看,画面没有新意,而且平淡无味,失去了敏锐的感触力,他似乎不适合拍摄冷战这种极其复杂和有政治敏感性的主题。
持续六周的苏联之行,成为战地记者卡帕摄影生涯中的低谷。他原计划拍摄的是产业工人、政府职员、农民,但他的镜头无一深入到苏联普通人民的家庭,他只好去拍农田里裹着头巾劳作的妇人,街头指挥交通的女警察,丰收的农田,像宣传画一般。他再回莫斯科,恰遇莫斯科建城八百周年的纪念,这个城市四处挂满了旗帜与横幅,像极了奥威尔《1984》的情景。在巨穴似的发电机体育场,卡帕拍摄了数以千计的运动员。在市中心花园,他看到苏联家庭围在纳粹坦克与飞机旁边。八百周年庆的那天晚上,卡帕跟一百多万人一起涌向红场和周围的街道。八百年大庆会的演讲中,斯大林明确地说,无论世界各国如何看待苏联,他都觉得莫斯科是一场伟大运动的象征。当看到一个生活在地下室却依然看上去充满骄傲和魅力的女子时,作家和摄影记者的疑惑终于压抑不住了:“我们无法理解,这是在现代生活中,对于英雄主义的拙劣模仿和歪曲。”
而当时,许多犹太作家都死在古拉格群岛。一些优秀的科学家则在那里制造出那个国家的第一颗原子弹。
1947年10月22日星期三的晚上,《先驱论坛报》召开一次会议,卡帕在会上做了一个陈述,总结了他对苏联的观察:“那些人受到的损害和遭到的破坏,比我在战场上10年的经历还要严重,他们也痛恨战争,比我谈过话的任何一个人都更痛恨战争。”之后,卡帕说,苏联人听说美国有“对自由人士的迫害”之后,表示出很大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