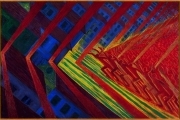艺术之都巴黎与现代艺术有着诸多渊源。/ Unsplash
一百年前,谁为现代艺术开宗立派?谁为一战纪实?谁通向包豪斯?谁为艺术史留下最先锋一页?谁的创造力影响至2017年?
现代艺术的故事,最好从1917年讲起。
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打到了第三年,超过六千万人卷入战争,其中约六分之一失去生命。4月,一直保持中立的美国对德宣战,并将全球军事最强国的地位保持至今;9月,德国在东线发动里加战役,此后德军在东西两线只剩防守之力;11月(俄历10月),列宁领导革命,俄国退出帝国主义大战。
这一年,德加、罗丹相继去世,遗产是未完成的黏土模型和随性的舞蹈室速写。他们留下的破碎形象和重塑空间关系的企图,对后世艺术家来说是重要的遗产。
这一年,毕卡比亚38岁,毕加索36岁,莫迪里阿尼33岁,藤田嗣治31岁,杜尚30岁,曼·雷27岁,米罗24岁,苏丁23岁,布勒东和查拉只有21岁。他们同时身负才华和焦虑,正准备开启现代艺术的新章。
毕加索。
2017年,巴黎决定好好回望一下百年。
大皇宫召集全球顶尖雕塑家,举办罗丹逝世百年大展。蓬皮杜艺术中心也推出两个百年展:一是“1917”,重现了100年前欧洲的艺术盛景;二是“泉之文献”(The Fountain Archives),展出后观念艺术家萨丹纳·阿费夫(Saadane Afif)自2008年起从各种画册、杂志和教材上撕下来的800多张有“小便池”的图片——作为最狂热的致敬者,这个计划获得了2009年马塞尔·杜尚奖。
不那么有家国情怀的杜尚,是巴黎的骄傲。如今他是艺术史上最重要的形象之一,也是唯一一位做与不做都同样引人注目的核心人物。他总是对“游戏”——先是艺术,后来是国际象棋——成竹在胸,总是走在前面,实际上有点太超前了。“他根本不在乎别人!”超现实主义创始人布勒东佩服地说。
杜尚从卫生用品商店买来一只小便池并署名“R.Mutt”的事迹早已写入教科书,然而时隔100年,仍有人认为现成品艺术难以理解。
杜尚。
1917年,纽约独立艺术家协会(Society of Independent Artists) 在最后一分钟拒绝了 《泉》。《卫报》艺评人乔纳森·琼斯说:“这个协会为自己代表一切最新、最前卫的艺术感到自豪,并接受其成员之一杜尚的提议——任何人只要支付6美元就可参加开幕展。杜尚付了费,但开幕前夕的紧急会议还是决定将这件杰作拒之门外。”
杜尚作何反应?他转而把《泉》拿到摄影师阿尔弗雷德·斯蒂格利茨的工作室展出,不出所料,先是轰动、争议,最终是从者如云。在小便池之外,杜尚还选择过自行车轮、雪铲、酒瓶等,但小便池是最荒唐也最有智慧的,换句话说,是最成功的。
一个月后,杜尚参与创办的小众杂志《盲人》(The Blind Man)发声道:“马塞尔先生有没有用双手制作《泉》一点也不重要,他选择了它。”这等于宣布:艺术家拥有点石成金的本领,由他指定的现成品即为艺术,或者说,观点本身就是艺术。小便池原件早就不见了,今天在全世界展出的是上世纪60年代制作的17件复制品——只要是由艺术家选择的,是不是原件并不重要。
百年后再来看,现代艺术的观念革新好像突如其来又翻天覆地,实际上过程是自然而漫长的,“像糖溶于水”。杜尚对“改变”狂热却有耐心,他“眼睛笑眯眯的”,亲和优雅,从来不会为了建构自身而攻击他人。评论家阿兰·儒弗瓦在《黑夜的蝴蝶——巴黎20年代艺术大爆炸》中写道:“与大部分人相反,杜尚总是说艺术家的好,互相诋毁的癖好使他倍感厌恶。”
杜尚作品《泉》,1917年
尽管如此,杜尚特立独行,不与任何流派为伍。即使在最亲密的朋友眼里,他也是一个谜。“马塞尔的房间里没有任何个人物件,没有书,没有家具,没有相片。他不再阅读了,他早已满腹经纶。”儒弗瓦如此描述。
“我把瓶架和小便池扔到他们面前,现在他们开始赞美它们的艺术美了。”1962年,杜尚在一次讲话中不无得意地说。达到这一成就,他用了整整45年。
1917年,热爱纽约的杜尚住在纽约。当时正是美国空前排外的时期,国会刚刚通过法案,要求16岁以上移民在入境之前必须通过测试证明自己有读写能力。爱国主义情绪席卷美国,影院里正在放映《纽约的骄傲》,“I want you for U.S.Army”!由漫画家詹姆斯·蒙哥马利·弗拉格亲自扮演山姆大叔的征兵海报狂印500多万份。美军征兵200万人,其中超过一半是自愿参战。
而此时的欧洲人是另一番感受。由战壕、坦克、毒气弹主导的一战比二战更加残酷,战争是欧洲人的切肤之痛。2月,超现实主义艺术家马克斯·恩斯特在防线上向一公里外的壕沟扫射,怎么也想不到他未来的挚友、诗人保尔·艾吕雅就藏身其中。
这一年,英国在西线配合法国,向德国发起了数次进攻,然而战果不佳。隶属于外交部的战争宣传局(War Propaganda Bureau)此前一直没什么作为,直到这一年,英国好像才终于意识到宣传战的重要性,专为志愿参战的艺术家组织了一个叫做“艺术家的来复枪”(Artists' Rifles)的训练营,或征召他们进入战地救护单位。
画家埃里克·肯宁顿、威廉·奥尔彭、C.R.W.内文森、保罗·纳什和威廉·罗森斯坦因此先后前往西线,在寒冷的壕沟里画速写和水彩,或者照顾垂死的伤员。这段噩梦般的经历给他们带来极大的震撼,战争中的部分画稿至今仍保存在同时成立于1917年的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中。
2017年,荷兰海牙,市政厅用建筑装饰纪念风格派运动100周年。
而在后方,宵禁中的巴黎弥漫着及时行乐的气氛。巴黎城随处可以听到由班卓琴、低音提琴和打击乐器演奏的爵士乐,高亢的萨克斯管很少被使用,可能是因为这座城市饱受战争创伤的脆弱神经受不了。就连浪子罗丹也终于决定给相处53年的罗斯·伯雷一个名分,不过73岁的新娘于两周后先他一步去世了。
贫穷的艺术家们聚居在蒙帕纳斯区(Montparnasse),过着作息混乱的生活,时常饭不够吃,酒又喝太多。他们买不起颜料,却毫不犹豫地把画框劈成木片生火,以免冻着光临寒酸画室的“缪斯”。
没钱买煤的藤田嗣治就是用这一招,也许再加上出示了证明父亲是日本军医的文件,得到了费尔南德·巴雷的芳心,15天后他们就在巴黎十四区结婚了。巴雷是个出色的女推销员,1917年年底,藤田已经在谢戎的画廊连办两次画展,走出了贫穷的地狱。
1917年1月14日这天,蒙帕纳斯的艺术家们在玛丽·瓦西列夫的食堂聚会,欢迎从战争中负伤归来的乔治·布拉克。阿波利奈尔、雅戈布、马蒂斯、雷维蒂、毕加索都来了,可没想到莫迪里阿尼酒后失态,竟对着旧情人的新男友(一位意大利雕塑家)掏出枪来,女主人瓦西列夫立刻招呼人把他扔出了食堂。事后德高望重的马蒂斯亲自讲了一段搞笑脱口秀,才让气氛恢复正常。
莫迪里阿尼画作《一个女孩的肖像》。
到夏天,莫迪里阿尼早就把上一段感情抛到九霄云外了,他迎来了生命中最后的“缪斯”(也许是倒数第二个)——让娜·艾布特纳,这个19岁的姑娘有一张长圆形的脸——今天在佳士得拍卖行常能见到她的倩影,莫迪里阿尼以让娜为模特,画出了一生中最富标志性的肖像作品。
跟莫迪里阿尼共用画室的苏丁就没那么顺利了,这一年他几乎什么都没画出来。这可能要怪莫迪里阿尼老是在他面前晃来晃去,苏丁是那种一有人就静不下心来的艺术家。
这一年,通过长袖善舞的沙龙诗人让·谷克多,左岸的带头大哥毕加索带着阿波利奈尔、莫迪里阿尼、基斯林等人,开始与右岸的贵族精英打起了交道。5月18日,由毕加索担任舞美设计的芭蕾舞剧《游行》在小城堡剧院上演,右岸上流社会对喧宾夺主的巨大戏服持保留意见,然而阿波利奈尔却很兴奋。
“超现实主义。”他一针见血地说。不过对毕加索来说,这一年最大的收获是来自河对岸的奥尔加·科赫洛娃——芭蕾舞演员、俄国将军的女儿、他的第一任妻子。
藤田嗣治画作《年轻的情侣和动物》。
1917年,第一期《达达》杂志面世,苏黎世“达达”走向全盛期。“当枪声在远方发出持续而低沉的隆隆声,我们竭尽全力唱歌、绘画、拼图、写诗。”这是达达主义艺术家让·阿尔普的自白。
苏黎世与杜尚的纽约“达达”一样无法无天,但它们是同一种运动吗?也许不尽相同。“达达”主义只存在了五六年,而当杜尚出现之后,超现实主义、波普主义、新表现主义等,随后的艺术流派几乎没有不受他影响的。
“我发现现成品的方式,是打算用它来消解审美,而新达达们却要在里面发现美,意味着我打算把它彻底带离艺术的企图没有成功。”杜尚说。
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
1917年夏天,另一本开创风格杂志《风格》(De Stijl)在阿姆斯特丹创刊。其背后是一群荷兰先锋派画家——凡·杜斯堡、巴特·范·胡萨尔,还有被战争挡在巴黎之外的蒙德里安。
6年前,蒙德里安慕毕加索和布拉克的大名前往巴黎朝圣,在那里他明白了“线条比色彩重要”,但现在,立体派已经不能满足蒙德里安了,他嫌他们还不够深沉,并开始追求抽象到极致的“纯粹实在”,直到作品只剩相交的线条。
在巴黎,女人是缪斯,是艺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蒙德里安则宣称,风格派不需要女人——他的缪斯是荷兰数学家苏恩·梅克尔,梅克尔通过三原色、水平线和垂线表达精神意义的思想大大启发了蒙德里安。
1917年,列宁从瑞士乘一辆“密封列车”秘密回国,领导十月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先锋艺术家、音乐家、作家对此给出了最热烈的回应,俄罗斯迎来了先锋艺术最辉煌的15年。这一年,回国从事艺术教育的康定斯基画出了具有更强烈几何元素的《即兴第29号》,但现实主义统领一切的环境下,他还是决定离开。
被任命为维捷布斯克地区艺术人民委员的马克·夏加尔也走了。不管身处何处,他总是忘不了家乡,做梦时想,画画时也想,所以当他看到I.L.佩雷茨创作的意第绪语故事集《魔术师》(Der Kuntsenmakher)时,胸膛被乡愁填满,立刻同意为此书绘制黑白插图。
这段短暂的先锋艺术时期为艺术史留下了独特的一页,2017年,伦敦皇家艺术研究院推出“革命:1917-1932年俄罗斯艺术”展,展示百年前的俄罗斯先锋艺术家如何将立体主义、后印象主义、未来主义接入新政权的视觉系统。这是1917年故事的另一头了,此后世界两极的艺术各奔东西。100年后,它们又再次合流,那是另一个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