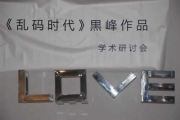对于叶永青来说,艺术不是一种职业,不是一门学问,而是一种日常生活的方式。生命中所有的甘美与痛苦、所有的幻想与沉思、所有的批判与预言,都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酣畅淋漓地流泄出来,欲罢不能。这种艺术与生活的内在一致,决定了叶永青艺术中的自我剖析和表达的精神分析性质。
从一开始,叶永青就是一个行走在云贵川高原上的孤独的行吟诗人,他的作品中具有明显的抒情表现与淡淡的伤感忧郁。他又是当代艺术家中酷爱读书、长于思考的一位智者,还在80年代中期,他撰写的艺术文论和书信,就以其视野的开阔、思想的深入、文笔的优美而引起我的关注。
“优美”二字,也许是品评叶永青艺术的一个切入点。无论是他早期反映云南山民生活的《洗马河》、《牧羊村的姐妹们》,还是80年代末所画的《梵哈的行列》、《季节的降温》等作品,都具有那种精致的装饰性结构、瑰丽的色彩、自由松动的用笔,自然地流露出淡淡的忧伤和无法言说的梦幻之美。即使是具有强烈社会批判意识的《大招贴系列》,我们也能从精心选择的丝绸与丝网印刷及独特的装饰性构思,而看到一种“乐而不淫、哀而不怨”的平和心态。这是一种建立在对生活的冷静观察与反思之上的有距离的美感。这种有距离的美感和冷静的观察,即使在他的装置艺术作品《冰床--时间与温度的具体性》中也有充分的表现。在这件持续了几十个小时的作品中,我们通过明亮的灯光、晶莹的冰块、洁白的米饭、瑰丽的颜料,充分感受到色光形的视觉变化。我们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不知不觉地参与了艺术家为我们的精神所搭设的舞台,在时间与温度的流变中,目睹不断变换的场景,在亦真亦幻的生活变奏中品味生命的底蕴。
这种对于现实生活的有距离地关注和长期的独自思考,使得叶永青将历史与现实、神话与幻想都融于日常生活的平静而轻松的表达之中,在这表面的轻松之后,则是艺术家对于日常生活的自觉反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命运的深沉思考。
个人的幻想与沉思的气质,使得叶永青的艺术在轻松多变的语言形式之下,具有了历史反思的厚度。从早期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到近年来对社会变迁的敏感,都显示出艺术家对于个体生命的自觉的存在意识。在叶永青的作品中,历史的变迁、社会的戏剧、个人的心绪都在缤纷多样的文化符号和图式结构中得到了含蓄的表达。其中虽然有艺术家无力直接改造社会的清醒认识,但却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强烈的历史责任和自觉的生命反思的率真坦露。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叶永青艺术创作的两个方面,以《大招贴》为代表的工作室大型作品,是具有开放性的对中国社会与历史的提问和含蓄批判,展开的是艺术家对民族根性与心理状态的思考。而《苍白的时刻》、《离家》、《春眠》等一批小型的纸上作品和丝绸作品,则以极为随机性的个性化方式,呈现个人的心路历程,使之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理轨迹而折射出时代变迁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冲击。
无疑地,现代化进程正以其不可逆转之势在中国土地上迅速展开,它所带来的物质丰富的环境恶化是清晰可辨的,但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和当代人的精神世界的震撼与改变,仍然是难以估计的。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使得人们和生活脱离了传统的轨道与秩序,使许多事物超出了人们的预料与把握之外。科技信息的膨涨与商业文化的泛滥,使人们面对各种各样的诱惑和选择而无所适从。对于潮流和时髦的追随,使许多人丧失了本来就不那么坚定的信仰和精神自持,迷失于多元价值的混乱和怀疑主义的虚无之中。作为一个艺术家,叶永青以他的艺术来进行灵魂的自我救赎,走上寻找新的精神家园之路。他选择划地为牢的方式,以画室和书桌来折射历史和空想的事物,探索新的思想和观察方法。在他的作品中,中国传统书法、古典青绿山水、大自然中的孔雀芭蕉、蒸气机车与冒烟的厂房、黑色的飞机与拼贴的报纸,还有形形色色的广告形象、外文残句、阿拉伯数字、卡通人物、儿童漫画、书信与麻将等,都在叶永青的手下获得了文化与历史的过滤处理,重新结构为一个庞杂而又多义的视觉图像系统,其中流露出浓郁的东方气息,但又具有开往的文化视野,触及了当代世界的普遍性问题。
叶永青作品中这种空灵轻快的视觉语言与多义而丰富的历史思考达到了一种融合无间的内在统一,可以看出叶永青对当代世界艺术潮流的熟悉和自我把握的能力。这使他的作品区别于中国当代艺术中一些直白外露的波普式图解和丑化宣泄的玩世表现,从而获得了含蓄而富人视觉艺术的可读性的审美品格。在喧嚣的都市文化风景中,他为我们开辟了一块灵魂的憩息之地,一个内心的故乡,在这里,我们将自己的激情、欢乐、苦闷相互倾诉,满怀欣慰遥想曾经有过的青春激情和柔美的人生惆怅,在无言的默想中将自己沐浴在神话与梦幻的光辉之中。
也许,叶永青对于古代帛画、中国丝绸、西藏唐卡、云南东巴族绘画、波斯细密画、日本屏风、明清绣像和木版插图的迷恋,本身就渗透了一种挥之不去的东方文化情结。其中的细腻、繁复,甚至纤弱,都象19世纪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一样,具有某种精致、冷峻和敏感的美,所不同的是,叶永青作品中没有19世纪末象征主义诗歌、绘画中那种颓废的病态美,而更多的具有健康的儿童般的幻想与稚拙。他画中的小鸟与自画像,都具有宽容而谦和的幽默,在随意性的涂鸦与符号之后,是对平凡而又单调的日常生活的超越,叶永青的作品为西方人了解当代中国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德国评论家本杰明·布洛赫(Benjamin H.D.Buchloh)在一篇题为《对再现在欧洲绘画中的回归的注释》中,有一段精彩的文字,我想用来评价和理解叶永青的艺术,是十分贴切的。本杰明这样说:“表现主义艺术家非政治的人道主义立场,他们对精神重构的专注,他们对工业技术的批判,以及他们吸收异质文化和原始经验的浪漫情怀,都与将精神从被异化的日常经验中拯救出来的艺术达到了完美统一。”
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叶永青仍然是一位表现主义艺术家,区别于传统的架上绘画,叶永青以开放的心态,运用不同的材料和风格语汇,表现了一个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人类日常生活的思考。他从中看到了日常生活的历史意义,而他的艺术与思考也就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份,进入了历史之中。(殷双喜 1996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