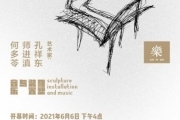曾妮说何老师(何多苓)今年五月六十生日,朋友们想出新招为他祝福。几个男画家要和他一起展览,又几个女画家要做一个“外围展”助兴。近年来我们圈子的展览,都时兴请各类“名家”,而何兄的展览总是朋友和美女环绕。在我们这个圈子,这样人情、潇洒、平易的玩法,唯有何兄。无论平日作为老朋友被何兄叫来喝酒看展,还是作为何兄的“老粉丝”被热爱何兄的美女艺术家叫来“友情出演”, 对于我都是何兄的一份情意。
我这个“老粉丝”可是资深的。1980年代初,我刚上大学,只是个“艺术爱好者”。那时可看的艺术杂志只有《美术》,全年订阅贵,就每月等到过期杂志放到旧书摊时再去挑。有一天有那一刻,旧书摊纷杂的封面群中,一个小女孩迷茫、游离的出神状,让我骤然感受到与生俱来的孤独被另一个灵魂触摸过的温暖——当我还是小女孩时,随父母在农村改造,这样迷茫、游离的出神状贯穿着我整个童年,只是那时我最喜欢发呆的地方不是干草地,而是干裂的锅底塘底。很多年后,当我的人生绕了大圈子最终还是落入“美术界”时,我才恍然那就是著名的《春风已经苏醒》,而当时留在我心底的唯有那种遥远而熟悉的温暖感,一种至今我在任何时间和场合再看到它时都能唤起的感觉,即便是以后我作为业内人对画面草地的特别处理一时惊异,被画面的忧伤再度感动,都没能取代这种原初的感觉。有趣的是当时匆忙一瞥的“何多苓”这个名字我倒记住了,因为和我从小最喜欢吃的“茯苓饼”同“苓”,而现在我更多的时候称何兄为“何多”,偏偏就省略了这个“苓”。 人生如戏,最终不过一个“情”字。
何兄是真性情的人,重哥们情义,怜香惜玉的花名更不亚于他的画名。这次参展的女画家,多是与何兄熟识的,也多是真性情的人,我每次来成都,也借何兄的光蒙她们温馨照顾。总体看来,她们的作品也大多是女性个人感觉的真实流露。符曦的作品持续地、夸张地画一些受伤的女人体,女性柔软的身体被处理成冷冰冰的水泥质感,有点脏乎乎的伤痕仿佛早已经肉体的伤害和内心的焦灼凝固。曾妮的画面是成都朋友聚会饭饱酒酣之时最常见的摆拍模式,画面人物处处透着“底色”呈半透明状,“耍”到这样的程度,以及“我耍故我在”的理直气壮唯有成都。郭燕的画面总是城市舒适生活背景,站行坐卧的人物几乎都是成双成对的,灰黑的基调上只有一种天黑前晚霞最后的玫瑰紫色,透着浪漫、梦幻和优雅,以及淡而无名的忧伤和有控制的距离感。廖海瑛把女人体和花树融为一体,强调一种触摸般的随心所欲的手感,色彩让人有某种欲望联想的刺激的粉红色,犹如充满女性内在激情和欲望的生命树,使花树与女人体之间本来就不清晰的界限更加模糊。罗敏的画面笼罩在中国红的色调里,破碎的石榴在玻璃瓶中呈现出模糊的性感,熔化的玫瑰花被粗暴地划开又缝合, “记忆”着甜蜜的伤害。安琦的“蛾”、“鸟”、“人”都像是快乐、轻松标本,毛进的“狗”不知是死睡呢还是睡死了,而杨青的纯净、空旷的蓝色背景中央,暖暖的小娃娃和梳子,透露出女性的平静的孤独感。艺术如梦,最终也不过一个“情”字。
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人说“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性自命出,命自天降”,也就是说人之所以为人的一切理由,都是因为上天给的生命的本性中有个“情”。怎一个“情”字了得。
廖雯 于宋庄小堡工作室
2007-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