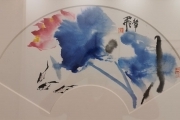乍看之下,大多数人对“跨界”展的参展画家的构成都会觉得不解:杜小同、孙浩和吴雪莲画人物画,形态和媒介上都很不同;谭军和阴澍雨毕业于花鸟专业,风格上南辕北辙;李飒和王剑现在画抽象形式的作品。他们每个人在内容、题材、形式、媒材和整体风格上的差异性都很大。是什么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组成一个联展?尽管每个人在面貌上显得如此不同,但他们之间最大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接受过长期正规的中国画教育。
进入现代以来,中国画的境遇变得尴尬异常。在二十世纪开始的中西美术交汇中,中国画是首当其冲的碰撞对象,康有为认为“中国画学之衰”“归罪于元四家”、陈独秀“要革王画的命”。自从以他们为首展开中国画革新运动以来,“水墨为上”、“写意为上”的传统绘画格局,便面临着内与外的双重挑战:既须应对来自西方艺术体系的形态学与方法论质疑,又要处理被救亡图强的时代主题所强化了的经世致用传统与文人画隐逸自娱传统的价值观对立。这样的双重挑战不仅打破了中国画长期高踞金字塔尖的稳定结构,同时也以前所未有的批判精神,引导着中国画家对艺术取向进行自由地选择。经过徐悲鸿、刘海粟等前辈美术教育家的大胆改良,以及更多水墨画家在创作上的大胆尝试,一个多元共生、各执一法的水墨画新格局,依托着中国社会发展和国际关系变化的磅礴背景,而渐次展现出纷繁多姿的身影。
中国画的变革最初从融合西法开始,当时的主力就是有研习西画经历的年轻人。二十世纪上半叶,尽管革命维新的思潮涤荡着中国画的保守观念,民国政府在美术教育上所持的西化立场也使中国绘画的人才构成发生着历史性的转化,却一时间还无法推出足以与沿袭传统派相抗衡的成果。然而饶有意味的是,这种变革的风气和大量外来的新鲜信息却促成了变革传统者的巨大成就,“浑厚华滋”的黄宾虹、画尽“胸中山水”的齐白石、提倡“强其骨”的潘天寿、“往往醉后”作画的傅抱石,都受惠于此。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曾经留洋学习西画以及回国后从事西式美术教育的人逐渐增多,传统派的影响日见萎缩。与此同时,解放战争的白热化,又使前进的艺术变革发生了新的方向性的变化。一大批艺术家改变了对艺术创作目的的看法,认为创作服务于革命的需要,所以“美术革命”成了“革命美术”,这股力量迅速成为之后一个时期里的主导力量。此后对待中国画的不同取向,由艺术理想、学识修养和形式趣味的分歧,演化成对待艺术与政治关系的不同态度。中国画从上层建筑演变成通俗化、写实化和叙事化的大众美术手段;而坚持艺术独立品格,不为政治而画的艺术家,则进入韬光养晦的保守状态。
在大陆沉迷在“红、光、亮”和“高、大、全”的政治波普形象中时,港台及海外却孕育出了“重新发现东方”的现代水墨画风。刘国松的纸媒肌理、陈福善的幻景、赵无极的抽象,都使大陆的水墨界为之一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的中国画创新浪潮一道,构成了空前个性化、多样化的局面。
自此时起,中国画的资源开始多样,形式变得灵活不拘,绘画的目的也重新回到审美本体上来,不再以外部政治需要为唯一目的,更多的人回到了对内心的审视中来。站在当代文化的立场来看现下的水墨艺术,它的当代境遇和未来的发展在本质上是个传统资源的再生问题。
自二十世纪前期,就开始有人预言水墨的消亡,但事实上,水墨画的影响力并没有降低。哪怕是今天,在浓郁的商业氛围和各种消费文化、各种流行时尚竞相充斥的时候,水墨仍然是全世界认同的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
他在当下的发展和变化,较之以前更有明显的不同之处。首先,就是对于水墨精神的理解。水墨画在当代的进化,关键就在于如何超脱出手段、材料和技术的藩篱,在遭遇和面对不同的文化情境和文化问题的时候,不断进行自身的调整和转化,生成出新的文化意义。目前的水墨画状况,基本可以分为传统水墨、现代水墨两种。显而易见,这两种绘画的方式在当下都有使其根植的丰厚土壤,是当代中国精神现实的反映。这两者之间并不是一种线性的取代关系,它们每一种都可以在当代中国找到它们生存的理由,这种立体、混杂的状态或许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其中现代水墨主动吸取了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某些观念和方式以及制作方法,对传统水墨进行了反叛和改造。对这一类的创作实践,在不同的地方也被冠以“实验水墨”、“抽象水墨”等名称,它最大程度的对传统的基本造型观念进行挑战而将笔墨等基本元素抽离出来。它与传统水墨的区别表现在,现代水墨有着现代主义艺术的资源背景,吸收了现代主义艺术中的表现手段和方式,例如采用激进的方式,以抽象性、运动感、制作效果等因素,破坏了传统水墨画的趣味和题材模式;同时,现代水墨扩大、改写了传统的笔墨标准,在工具和材料上,在作品的幅度和装帧方式上也进行了大胆创造。
尽管极尽反叛之姿态,现代水墨仍然很难和传统水墨真正划清界限。它在创作面貌上虽然和传统水墨有了很大的不同,但它的基本问题仍然是从传统水墨自身中所生发出来的问题,它在精神和文化品格上,仍然与传统水墨一脉相承。这种一脉相承表现在,现代水墨继承和强调了传统水墨中的核心问题,“笔墨”,将具有偶然随机性的性比过程理性化,由此来放大和强化那种挥洒的、诗性的精神因素;同时,它们都属于精英艺术,强调的是个人体验,个性的书写,和心性的释放,所以它们都与当下的社会现实脱节,不针对问题和公众,而着力于个人的风格和形式的营造。
那么水墨的当代性又该如何体现?这也即是说,如何获取水墨的当代性品格,这才是当代水墨发展问题的关键。
我想,这就是这些艺术家最终能够联合在一起展览的原因。这次参展的艺术家都有很长时间的水墨训练经历,但是他们的作品所呈现出来的是各自对当下周遭环境的映射。生活单纯、性情淳朴的,画面就追求传统的淡泊气质;个性严谨、注重理性思考的就在抽象形式中钻研智性的美感;亲和人性的就绘画人物,并在其中投射出自我的影子。不管他们的创作是否真的在后世被认可具有当代性,但是形式上的突破明显已经不再是他们的最终追求。
在都市化程度迅速提升,国际性交流日趋活跃,信息传媒和艺术资讯高度发达的大趋势下,形形色色的现代探索、古典复归、趣味投射、形式翻新、意义解构,将当代水墨画拓展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容器。如果说,世纪初的水墨画更多地面对不同艺术取向之间的分离和对峙,世纪中的水墨画更多地受到政治和社会功利主义的裹挟,那么,新世纪的水墨画又将如何演变?二十世纪是一个充满论争、困惑和畸变的革命时代。希望这些艺术家能够以自己的创作重新拓展水墨的精神深度。
【编辑:叶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