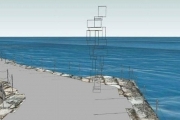尼尔森,芝加哥大学艺术史教授、文化历史委员会主席。出版并发表了多篇关于中世纪地中海世界艺术的著作和文章,最近编有《拼贴艺术专题文集》。主要从事两项课题的研究,即文艺复兴时期对拜占庭艺术的接受和19、20世纪对拜占庭艺术的接受。
有两条道路可以通向得克萨斯州中美城市(a Middle American city in Texas)的一个公墓,我的家人们已经在那里安息了多年。一条是穿梭于老式别墅中的迂回小径,现在已被翻新;另外一条是更加繁忙和便捷的商业大街,两侧林立了众多新兴的店铺和办公楼。公墓是一个普通的地方,有着开阔广袤的草坪,从没有像洛杉矶森林草场那样被赞颂和炫耀,相反,却被急驰而过的现代化交通工具所遗忘,或者被那些悼念埋葬在这里的亲人的人所缅怀。这个坟墓与美国大多数公墓一样,没有陈设相互攀比的奢华纪念物,同时来访者也可以沿欧洲公墓纪念走廊行走。这是一个属于死亡的更加寂静,更具乡村特色的地方。但是,它也是一个商业场所,隶属于一家销售丧葬用品、鲜花、墓碑和公墓平面图的企业。它所占有的空间、它的社会性和商业性同时也昭示了它是一个用来象征性地界定丧葬身份和管理葬礼场所的工具。人类用所能想象出来的各种不同方式对墓碑施以密码,加以掩盖,并由死者的直系亲属和含义的制定者为墓碑设计识别标志。
我父亲的墓碑也不例外。在一棵高大、葱郁的橡树旁有一个简洁的墓碑,地上还竖立着一个体积不大的刻有姓名、生卒年和宗教象征的大理石徽章。前不久,我沿着那条小道去祭拜父亲的坟墓,沉缅于跨越公墓边界和大门时所必需的心理准备。即将通过大门时,突然想起自从上次来访时就已经放在门上方的雕塑,我逐渐变得惊讶,并最终愤怒起来。在我面前耸立着威尼斯圣马可教堂正门上方的四匹慢跑的华丽镀金青铜马的缩小版本(图9.1)。这些马匹和它们多变的历史环境(sitings,建筑工地选择; (道路等)定线)是我探索艺术与个性或认同(identity)之间关系的焦点,无论是个人的、集体的、市民的,还是国家的。
几年前,圣马可教堂的这些雕塑被派遣进行了一次巡回展览,我们还看到了标准的展览目录。最近,这些雕塑还成为一些学术性专题论文的课题(比如,雅科弗,Jacoff 1993年)。在艺术史的准则范围内,这样的青铜雕塑被充分地礼拜。在这篇短文的结尾,我将转而论述它们复杂的历史。目前,有报导说:为了更好地加以保护,这些雕塑已于1983年被从教堂的正面拿走,安放在教堂内部,在那里,它们与以前不同,不再在威尼斯咸水湖那样柔和的阳光的照耀下,而是像其它博物馆或精品店一样,打着强烈而又华丽的聚光灯——如插图所示。它们的替代品是呆板而又平庸的复制品,完全没有历史原作的气息。但是,相比之下,得克萨斯版更加不尽人意,和大狗的尺寸差不多,用某种奇怪的材料制成,外表极其不自然,竖立在距圣马可广场很远的地方。无力改变公墓入口处和内部的一切——包括我父亲的坟墓——的象征性窜改。作为一名学生,一位艺术史学家,一个拜占廷艺术的学生,我只能诉助于今天被看作是笔墨的东西——我的键盘,同时,我的调和存在于“挪用”这一过程中。我将通过当代艺术和艺术史中的一些问题来思考这个术语。
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单词“挪用”几乎不能再简单或再直接了,它来源于拉丁文ad,意思为“向、往……(to)”,具有“参照(rendering to)”的意思;proprius,意为“拥有或个人的(own or personal)”,两者结合在一起便产生了appropriare,意为“视某物为自己所有(to make one’s own)”。“挪用(to appropriate)”,排除政府的意义——拨款或者为某个组织设立基金,在今天意为将某物据为己有;形容词“appropriate”意为追加的或附加的,属于某人的,私人的或适合的、正当的。“Appropriate”还有更左的内涵,暗指不正当占有某物,甚至绑架或偷窃。综合肯定的或贬义的两方面,挪用不是被动的、客观的或漠然的,而是积极的、主观的、充满目的的。
将“挪用”应用于艺术和艺术史是最近的事,且与对艺术作品先前存在的成分的采用有关。但这样的行为一直没能被成功地描述成“借用(borrowings)” 或者“影响”:描述成“借用”,就好像拿走的东西永远要偿还;描述成“影响”——一种令人困惑的方式——就会使某人或某物影响、启发、诱导,甚至左右艺术作品的生产和接受。米歇尔·福柯已经对影响的概念进行了批判,尤其是当它从属于术语组(a constellation of term)时,如果从理论层面上浅显地谈,这些术语证实并维系了历史、传统和话语(discourse)的连续性与完整性。尽管从句法上讲非常复杂,但是从概念的角度看则充满了智慧,福柯将影响描述为这样一个概念,“它为传播和勾通的事实提供了支持——太虚幻了,以致于无法经得起分析的考验;它意指一个显而易见的因果过程(既没有严格的界线,也没有理论上的限定),相似或重复现象;它在远处并穿越时间——就好像通过传播媒介的调解——将个体、艺术家的全部作品(oeuvres)、观念、理论等被明确界定的单位(unities)连接起来”(福柯,1972年,21)。就艺术史自身而言,米歇尔·巴克森德尔还提出:影响割断了行为者和中介(actor and agency)。相比之下,术语“挪用”则既存在于制作者,也存在于接受者。两者间的不同就好像是被动语态和主动语态之间在语法上的差异。
从理论上讲,这一术语与罗兰·巴特的符号学同时,尤其是他对所谓的“神话”的分析,是最近才逐渐形成的。神话,正如他在1957年的著作《神话学》中所写的,是讲演(speech)的一种类型,一个自觉利用单词的希腊语词根,却无意识地揭示了语言学的基础和法国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影响的定义。神话是讲演,因为巴特正在探索的是信息(communication),而不是一个客体或观念。他介绍了传统符号学中所指、能指,和他们的结合体——记号的范畴。接着,通过限定神话为意义的第二秩序(a second order of signification)扩展了记号的概念。在神话中,第一记号,能指和所指的结合,转变成一个新的所指的能指和第二记号的组成部分。曾经是完整的和有意义的东西被第二体系借用,并用来表示(stand for意指?)新的概念。这样的过程可以被无限制的重复。巴特通过对一家法国杂志封面的分析进一步说明了他的理论,与我父亲坟墓处的马一样,只有描述,没有解释。因此,在开始之前,巴特做了一个没有自白的符号转换(shift),也是一个从图像到词语的复杂转译(translation)(见第四章“词语与图像”)。另外一本书《显相器》Camera Lucida——关于许多他妈妈的有争议,但却永远没有解释的照片——中巴特也使用了同样的手法。
我想将巴特所谓的“神话”重新命名为“挪用”,从而通过挪用他的神话来解释和规定这一理论。这样做,我就将巴特的符号结构的含义转向个人,以此来强调个人的中介力量(personal agency),而不仅仅是意义的游戏。由于相似的惯例,我还采用了一个已经在英语国家使用了的单词,这个单词凭借它在习语中更加坚实的基础比“神话”更容易重新定位。挪用,即是在墓门上方安置圣马可之马这一方法(process)。
曾经竖立在城市主教堂和总督府礼拜堂前面的四匹马一直是伟大威尼斯的能指。而马的缩小版本则为他们的新主人服务,更确切地说,作为威尼斯、艺术、古老世界标志的马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所指的能指。由于一些我们只能臆测的原因,一个普通的墓地因此被重新予以界定。目的在于通过对艺术的挪用——甚至是在拙劣复制品的伪装下——来强化入口?还是仅仅增添一些更加常见的高贵雕像的标志?就像在美国一些新成立的文化机构(比如,纽约公共图书馆、芝加哥艺术学院)入口处用来标榜威严的狮子。或者马自身的基本概念是地方文化的主要价值?在得克萨斯,自远古和中世纪以来,马始终是个人声望的一个最重要标志(骑马像、着盔甲的骑士),直到工业革命才被自动机车所取代。后来,马的名字被运用到汽车上(如,野马Mustang),既以此来追忆历史,也用来掩盖工业技术上的革新。
在介绍挪用时,我故意在我的生活琐事中进行讨论,因为这个词“有理由”或者说从词源学上讲涵盖了个人的因素,这既给予这一过程以概念上的力量,同时也表现出在符号学上的不稳定性。就像放射性核素,挪用或神话打破了时间界限,既没有消失,也没有成为一个新的神话。因为,挪用,与玩笑一样,是具有语境和历史性的,依据新的语境和历史,它们可能被隐匿或改变。“福特(Ford)”,一个公司,不是汽车,也不是死去的工业家,耗费上百万的资金来维持挪用的清新与活力,并使其成为集体话语的一部分。
按照巴特的解释,挪用与神话一样,是一种曲解,而不是对前符号学组合(the prior semiotic assemblage)的否定。什么时候成功,它便保持而不是转换前者的涵义来创造新的记号,而且是悄悄地完成这一切,进而使过程看起来普通、自然。公墓中马的效力来源于他们的原件,这一效力被用来重新定位、销售和为墓地作广告,但是,通过在门口附加复制品,所有这一切都进行得如此平静。神话或挪用是现代广告业的基础,也是分离和夺取资本主义自身战略的基础——这一战略正是马克思试图在《资本论》中描述的。对哈尔·弗斯特(Hal Foster,1985年)来说,联系是具体的,而不是隐喻的,挪用在文化领域与在经济领域中资本主义的劳动占有是同等的。然而,今天,这些改革并没有在相对简单的19世纪乡村资本主义(cottage capitalism)经济结构中完成,而是在跨国工业集团中完成的,马克思主义者喜欢称那种经济景观(economic landscape)为“后期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但是,随着近期的发展趋势,或许称其为“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更为适宜。无论叫什么名字,今天,人们对产品的需求受到全球广告代理商——我们这个世界上真正的符号学魔术师——的刺激。就当代的经济秩序而言,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一个研究符号资本(symbolic capita l)的理论家和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一个关于时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早期工作是有所裨益的。
巴特指出,神话可以挪用的那些记号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完整的。因此是可占用的,如果被完全、充分地控制,记号就不能被转换——至少不是悄无声息的,或者没有结果。一个恰如其分的例子即,在艺术和流行文化中,美国国旗的大量使用,甚至是滥用,这样超越社会规范的挪用不断地遭到掩护。一次成功的挪用,其运作是悄悄进行地,像一个外来的有机体突破身体的防御系统,并自然且良性地迂回其内。或许,我坚持呼吁的那些在我父亲墓地入口处的马被大多数路人忽略了。人们已经习惯了主体建筑入口处的动物形象,乘车的旅行者易于接受墓门上方这些借用来的动物,业主们则企图以此来提高他们坟墓的地位和身份。或许,在这些匆匆过客中很少有人了解关于这些马的悠久的象征性挪用历史。
为了破译神话或挪用的运作,人们可以像我所做的那样,关注意义的任何先前阶段,而不是意义的最后产品,因此,我反对符号学进入神话,尽量解释被掩盖起来的原动力。当然,这样的过程导致了更多的挪用行为。但是,这些行为是个人的,而非客观的。从抽象层面上看,挪用这一概念很容易延伸到阐释行为本身,也易于扩展到个人与任何内在的或外在的事物间的针锋相对。这样,挪用可以成为知觉本身,是对所视事物的一种反映,甚或是记忆,是思维对过去的重构。然而,更进一步地说,挪用行为成为一个理论上的Pac-Man,它可能吞并所有其它理论术语和方法,并且,也可能被做解析式的无用诠释(render)。
就我们的意图而言,“挪用”更适于视觉艺术和当代模式领域,这种当代模式将外在的东西引入艺术作品,或简单地制造技术艺术(make art art)。最近,“挪用”和另一术语“讽喻”(allegory)结合在一起,长期以来一直被应用于当代艺术,尤其是当代艺术实践中的某些潮流,这些潮流依旧聚集在纽约——通过这些潮流,现代主义被接收,部分地被剥夺了其符号的丰富性,并且篡改进入后现代结构之中。在早期的拼贴和蒙太奇实践中最早详细论述其发展和起源的是本雅明·巴克洛(Benjamin H.D.Buchloh);随后在20世纪80年代涌现出的该运动的其他批评家有哈尔·弗斯特,道格拉斯·克里普(Douglas Crimp)和克雷格·欧文斯(Craig Owens)。
比较这些批评家,许多现在被称为“挪用艺术”的倡导人都是女性,而且性别上的评论是很常见的。这些艺术家,比如巴巴拉·克鲁格(Barbara Kruger)或谢利·莱文(Sherrie Levine)都不像杜尚或达达艺术家那样用现代工业生活的基本物品工作,而是利用挪用来的形象。谢利·莱文挪用各种各样的现代主义画像——沃克· 埃文斯或者爱德华·韦斯顿的照片——并因此评论和反对现代主义的战略,但是她并没有完全逃避开任何挪用所带来的危险——被挪用者战胜了挪用者。巴巴拉·克鲁格是一家杂志社的版式设计师,用集锦照相术工作,这是现代广告宣传的主导方式。代替将图像和文字说明天衣无缝地、自然地、有力地相互挪用的结合在一起,克鲁格的文字与图片不仅像磁铁的两极似的彼此排斥,而且还排斥观者,对于他们来说,思考文字-图像间的结构就像是倾听两种无法调和的乐器。克鲁格自己曾经使用过其它隐喻,她在接受安德斯·史蒂芬森(Anders Stephanson,1978年)的采访时说,“我想要通过语言笨拙的离题和不确定的窘境来打破形象沉沦的缄默,并且在企图揭露我们所看、所言的基础的愿望中,使外表(看到的文与图间的关系——译注)松散或至少使其接合处分裂。”
克鲁格的代表作品是一件大理石妇女头像的侧面像,在这里她为之添加了标题“你的目光击中了我的脸庞”,就好像这个被再现了的客体能够答复对象化了的观者(另见第16章《注视》)。与杜尚、20世纪70年代的某种艺术、或大多数广告一样,克鲁克的视觉/言辞结构向观者发表演说。为了简化这种对抗,克鲁格用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而不是用抽离出来的有距离感的第三人称为她的作品命名,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在广告中相当常见,第三人称则是标准的信息性图解。克鲁格用摄制的,而不是绘制的形象工作,因为,尽管使用了数十年,摄影仍然被假想为与再现之物有着直接的、无中介的联系。因此而生的重构的和再挪用的蒙太奇向复合范畴:再现(尤其是描述女性、注视的客观化对象)、观者和观看的语境提出了质疑。作品是一种新颖的、具有原创性的,因而也是适应市场销路的中间重构形式(media reconstruction),只是有些方面已经出现过了。具有劝诫性和修辞性的影响使人想起一种早期广告和宣传,例如,军队招募海报上萨姆叔叔指着并命令道:“我要你(I want you)”。相关的符号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古代,包括:同样被刻画了的日常生活器皿、墓碑铭文、圣像画或中世纪手抄本。(尼尔森,Nelson1989年)如果只需片刻一个对位(dialogic position)便可以非常熟练地为他们建构,那么这些言辞/视觉结构将是非常成功的,因为,观者可以使他们自己成为交流结构和挪用中的一份子。
尽管对历史学家来说预测未来通常是不明智的,但是,巴巴拉·克鲁格和谢利·莱文所作的挪用性工作却是一个规模更大的现象的过渡阶段,这一现象将被称作“后摄影”——近来一些展览和著作的主题。这个新世界所带来的是对摄制形象全面控制的可能性。正如威廉·米歇尔(William J.Mitchell)所描述的,传统的摄影产生类似的形象,或者呈现为空间中连续不断的变化,而且形象的色调与照射在胶片和相纸上的光线相一致。相比之下,新的方法则是数字化的、具有更明显的间断性,由一个数字化的网络系统产生,被称为像素,存储在电脑中。由于每一个像素都可以被电子化来控制,从理论上讲,形象可以被明确地操纵,同时,这一技术日益普及,尤其是在新闻业中。传统的集锦照相术是拼贴的一种类型,但是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缝合的痕迹消失了。后现代摄影的挪用策略在艺术上的结果并不明显,但是“电脑拼贴”已经在技术上实现了。现在,符号向摄影滑动的速度逐渐加快,进一步模糊了绘画和摄影,以及文本和形象之间的传统界线。在计算机中,文字和图像都是数字化的,口令在视觉“画像”的监控下直接处理程序。
摄影和集锦照相术已经开始在另一系列当代批评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些批评涉及到博物馆、展览设施,以及在任何形式的收藏中都不可避免的挪用。装置艺术已经成为当代艺术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某些艺术家,比如汉斯·哈克(Hans Haacke),便利用它瓦解了两个序列——艺术-博物馆-观众和商品-企业-消费者——之间的略音(elisions),前提条件是企业对艺术的支持。路易斯·劳勒(Louise Lawler)在许多情况下这样理解艺术:不那么尖厉、容易引起争辩,并且效率更高的是那些温和的、抒情的摄影作品。她的一些形象和引申文字说明被收入道格拉斯·克里普文集中的最近一卷,其中一些与目前所关切的事情有关。在书中,劳勒的照片孤立地摆在一边,但是还是间接地支持了克里普的评论,此外,注意其方法——运用这种方法,艺术在生动的语境中发挥作用,这些语境可能是在办公室,可能是在画廊,也可能是在家中。装了画框的印刷品和复印机,绘画作品和电视机出现在同一个空间中,形成一套作品(gesamtwerk作品全集),不管艺术(kunst)与否。
当代艺术和批评迅速利用最新的法国理论成果,巴特关于神话的概念就经常被援引,其他法国学者也被卷入了这些讨论。比如,社会学家皮埃尔·鲍德里亚(Pierre Bourdieu)在他的著作中使人们了解了现行的收藏实践和自身组织结构,1979年第一次出版,后来被译为(改为translate as)《差异》(Distinction,1984年)。从它的副标题——《趣味判断的社会批评》(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康德是一个主要关注点,但是经验主义的数据(收集了在社会各个阶层家中发挥作用的庸俗艺术品和高雅艺术品)也预示了目前艺术和艺术史中的许多隐患。在趣味中显示了阶层、收入和教育等社会基础,趣味是一个被鲍迪尤扩展到与艺术史密切相关的问题的范畴。购买艺术,或其任何形式的变体:获得复制品、进入博物馆、参加展览、挂在董事会上,都是聚积“象征性资金”的一种方法,并因此在社会群体中获得身份,取得预期效果。控制了“象征性的权力”也可以取得同样的结果。艺术家、艺术史家和批评家们可能缺少购买实际艺术作品的资力,但是他们却有能力将普通的物品转换成艺术,反过来也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中,物品的特性和意义让渡给个人,这便完成了挪用的循环(appropriative loop)。
这种社会科学方法的一个明显结果是形成一个针对惯例的批评,依据这些惯例,“我们的”文化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制约地获得其他社会的艺术品,通常参照当代欧洲或美国(见本卷第13章《原始性》)。萨利·普赖斯(Sally Price)的著作《文明地区的原始艺术》,一个颇具讽刺性的题目,很好地批评并嘲弄了文化的不均衡,这种不均衡牵涉到对部落艺术品的发现、再界定和挪用。像劳勒一样,普赖斯创造了拼贴,其重要性在于语言(verbal),而不是视觉,为的是让人们不关注物品或它们的制造者,而是关注它们的重制者(remaker修改者)或挪用者。目前,对艺术品、话语和殖民主义的类似分析构成了当代人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艺术史而言,话语对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展览《20世纪艺术中的“原始主义”:部落与现代之间的亲缘关系》反应最为强烈。詹姆士·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在他的文选中对该问题,以及文化再现中的其它普遍问题进行了深思(1988年)。文化再现的当代研究在文化多元主义(multiculturalism)和后殖民主义话语浮现的环境中也经常被富有创造性地理论化。从那一观点出发,霍米·巴巴(Homi Bhabha)击中了问题的核心,他指出:我们所需要的是“‘记号’的再形成(rearticulation),在这过程中,文化认同可能被铭记”——换言之,即关于所有类型文化再现的创造性挪用的工作。
严格说来,在广阔的艺术史领域中仍然可以感觉到文化多元主义的雄厚力量,但是再现行为的多样结果,尤其是再现的感觉是挪用,是在许多领域里激起了一股仓猝的研究。比如,再现一个没有穿衣服的人的暗含——习惯上称为裸体——正在被检查,特别是对未穿衣服的女子的图像的使用和滥用。问题是也要转换到男性裸体的意义上(阿德勒Adler和波伊顿Pointon,1993年)。对静物画的分析或对家用物品的描绘潜在地揭示了对待物质财富及其象征(representation)的更宽泛的态度。这里显而易见的对象可能是17世纪的荷兰和被西蒙·沙玛(Simon Schama)在《富有的窘境》中称之为“富有的窘境”的东西,或者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消费文化。纽曼·布列逊和其他一些有远见的学者已经在较早时期进行了论述。比如,在华丽的荷兰绘画中或陈列在博物馆入口处的迷人的花朵的意义是什么?消费者的生活是怎样通过他们的财富重新组织的?这些物品的设计(design)、主题的模式(the subject of design history与混乱相对应的一致或有意图的模式)是怎样促进了挪用?对于精英观者来说,流行艺术(pop art)、大众消费的再现(the representation of mass consumption)是怎样在表面上挑战,而最终重新肯定了消费文化?
然而,或许对再现与挪用之间联系的最积极的研究正在风景画领域中发生。在这项研究中,英国18、19世纪风景画成为最具理论色彩的挑战性工作的焦点,其目的,正如米歇尔(W.J.T.Mitchell)在新近一卷书的引言中所扼要介绍的,“是将‘风景画’从名词转变为动词”。新阐释的一个结果是,如果偶尔使田园生活无聊的再现(renditions)变得与众不同,那么,一般博物馆的参观者可能会心满意足。在1980年约翰·巴雷尔(John Barrell)的著作之后,在汤姆森(E.P.Thompson)的社会史的启发下出现的是所谓的“风景画的阴影”(the dark side of landscape)。巴雷尔解释到:在18世纪风景画中,与光线充足的、被显著描绘的财富相比,在阴影或背景处人们期待着展现出乡村的贫穷。所有的风景画都有一定的明暗范围,这样的图画惯例是说明性的,而不是自然主义的,同时这也是一种想要获得的社会秩序的投射。几年后,安·伯明哈姆(Ann Bermingham)的著作进一步解构了认为风景画是自然的标记这样一种观念。
更近些时候,伊丽莎白·赫尔辛格(Elizabeth Helsinger)思考了19世纪上半叶在英国艺术和文学中乡村景象的挪用,但是将问题转向了集体(the collective)和意识(the sense),即风景画是充满竞争和冲突的挪用场所。风景画,被认为是“本质上是英国的”,是建立英国风格或民族感的一种手段。因此,风景画不仅表现理想中的社会关系——至少是财富,而且要表现假想出来的中下阶层的共同体。然而,通过这样的自然的形象(images of nature),被认为是普通的形象(natural images)来界定国家、民族的概念,就有意无意地排除了没有在场的人物和空间。在欧洲或美国,风景画始终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和象征性挪用国家土地的一种战略,因为这是一个拥有领土的国家的最基本需求——无论这是真实的,还是假想的。这种所有一定要在每一代人中重申,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方式就是视觉记号,无论是风景画、摄影、电影、地图,还是公路指示牌。其目的和往常一样,是为了制造对领土的人为的、瞬息的和政治上的拥有,而表面上看起来却是自然和永恒的。
然而,对土地的象征性挪用(至少在它的英国版本中)既不是以现代民族国家为起点,也不是以新艺术史作为开端的。在1973年,奥利格·格雷巴(Oleg Grabar)在其著作的一个章节《伊斯兰艺术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Islamic Art)中论及了此问题,并向人们展示了这一新兴宗教是怎样通过耸立的群山来证明其对前拜占廷和波斯帝国的领土的象征性的和物质上的所有。在上述引证的事例中(比如在耶路撒冷的the Dome of the Rock),穆斯林赞助人和修建者借用先前的象征性语言,并使之适用于新的寓意,即是一个关于神话或挪用如何操作的清晰示范。有些山,比如the Dome of the Rock直到今天还仍然享有象征性的中心地位;而另一些则像古老的神话和衰亡的隐喻一样退隐并消失了。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象征性客体的持续可接受性。今天,随着许多大量复制技术成为可能,客体被带到其观众面前;而在过去,情况则与之相反。目的是要在人们聚集的地方建立认同和所有权,如十字路口、城市广场、主要建筑物,或旅游场所,尤其是像耶路撒冷的the Dome of the Rock或the 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er(圣物储存室、坟墓)这样的朝圣地。
圣马可之马在若干历史语境中的显著位置使它变得如此重要。反过来说,这四个与原物等尺寸的镀金青铜雕像本身的美、经济上的价值和技术上的完善抬高并增强了支撑它们的建筑和与之相呼应的共同体的地位。人们对他们的早期历史并不清楚,但是一般认为是制作于公元2或3世纪。15世纪时被从开俄斯半岛带到了君士坦丁堡,放置在竞技场或城市主要的公共剧场,它们耸立在出场入口处的正上方,马队与战车就是从那里涌出的。拜占廷的挪用无疑转换了它们的含义。尽管对它们之前的语境完全不知晓,但可以知道,马队经常以四马两轮战车的形式出现(包括两轮马车、御车手和四匹马),以同样的姿势站立在罗马建筑或拱门上方,目的是纪念特殊的历史性重大胜利。不管它们在开俄斯岛的涵义是什么,发生在竞技场的竞争和帝国的仪式都将赋予这些马一种更加普遍的胜利感。
竞技场能够容纳成千上万的观众,并且与宫殿毗邻,是拜占廷皇帝与人民见面的主要场所。因此,正如莎拉·巴西特(Sarah Bassett)所详细论述的,它是与政治权力的象征相匹配的,聚集在这里的马也不仅仅是雕塑。现已不复存在的更好的例证是巨大的赫拉克勒斯青铜雕像,雕像耸立在Tarentum卫城,由公元前4世纪著名的希腊雕塑家利斯普斯(Lysippus)制作而成。公元前209年在罗马人征服了Tarentum之后,雕塑就被放在了罗马城象征性的中心主神殿(即丘比特神殿,the Capitol),当首都迁至新建的君士坦丁堡时,赫拉克勒斯便与之一同前往了。后来加入了这四些匹马,与其他雕塑一同成为新罗马竞技场的合法财产,以古罗马马戏团编钟敲奏法(maximus)为模型。
在积极的威尼斯人的赞助下,雕塑一直在竞技场里存放,直到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此时雕塑被君士坦丁的基督教徒,而不是圣地(巴勒斯坦)(the Holy Land)的穆斯林教徒搬走并摧毁。十字军战士们倾倒在城市的财富面前,他们掠夺教堂、宫殿,将竞技场上的青铜雕像融化成钱货,用拜占廷历史学家的话说,“伟大适于渺小”。四匹马为了一个不同的挪用而被保存下来。通过航运被送到了威尼斯,稍后即被安置在城市主教堂的入口处。在圣马可,这些马曾经是毗邻总督府的公共空间的一部分;现在,它们在另一个入口的上方昂首阔步,与其它一些胜利的标记一同来纪念威尼斯的伟大胜利。这样,威尼斯挪用了君士坦丁的挪用。在每一阶段,之前记号的部分知识残留下来,说明了符号学的失真(distortion),而不是全盘否定,这就是巴特的“神话”和我的“挪用”的特征。
按照米歇尔·雅科弗的说法(1993年),这些马在圣马可获得了另一层意义。它们曾经和西面表现基督和四位先知的浮雕结合在一起,作为基督的四轮马车。截止到14世纪,竞技场上的马已经转变成威尼斯的象征,所以反对派可以通过提议给圣马可教堂的“没有被驾驭的马”上笼头来威胁共和国的独立。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再度挪用这些马,他们将其视为古代艺术的伟大杰作,并在没有充足理由的情况下认定其为上面提到的利斯普斯的作品。曾经一件真实的利斯普斯的青铜作品可以在君士坦丁堡获得;而现在,借助另一挪用,利斯普斯的作品可以通过新的稳定的美学话语的“象征性权力”出现在威尼斯。在现代早期,随着圣马可广场的扩大和总督府piazzetta的创造,马周围的自然和社会空间改变了,表述行为的语境,以及马的宗教涵义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同时,它们在教堂正面的替代品因不符合美学上的尊严而遭到了批评,卡纳莱托(Canaletto)在他的《随感》(Capriccio)中将它们刻画在教堂前面华丽的古代柱础上。(见Corboz,1982年)
然而,马从未与威尼斯本身失去联系,当18世纪末拿破仑彻底征服威尼斯共和国的时候,他取走了威尼斯从君士坦丁堡拿走的东西,也就是君士坦丁堡从开俄斯岛拿走的东西。他将这些马带到了新帝国的首府,并于1789年在巴黎的市民面前炫耀。起初,马被放在杜伊勒利宫(Tuilleries)庭院的入口处,后来又被安置在新建的用来纪念拿破仑胜利的竞技拱门上(Arc du Carrousel),就像罗马凯旋门上的四马双轮战车一样。但是,帝权的胜利和对战利品的掠夺在19世纪可能一样,也可能不一样。当拿破仑倒台后,这些马被送回威尼斯,但不是威尼斯共和国。当时是奥地利的国王弗朗西斯一世统治这座城市,他主持了正式的仪式将马重新放回到圣马可教堂。在巴黎,这些马一直被用来拉拿破仑的胜利战车;现在则处于从码头到教堂的宗教性队列之中,被在另一个世纪中获胜的帝国的军队牵引着。
在威尼斯,这些马返回到了贵族化的主题公园,第一欧洲迪斯尼;也返回到了这座依靠遗产为生的城市——研究、分析、复制、包装它的历史遗迹,并为游人(包括教育旅游和包办旅游)陈列,并因此年复一年地实现了许多新的挪用。在拿破仑失败的地方,专家们却大获全胜,这些马得到了专家的关注、被供奉在博物馆的聚光灯下,并通过我们这个世界上无所不在的挪用——名信片进行销售(见图版9.1)。这些马已经成为艺术世界的公民,在这个世界中,它们曾经作为政治象征的符号的丰富性不再成为可能;在这个世界中,意义以各种表面上看起来专断、任性,而实际上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方式——和所有挪用一样——破裂、改变。这座无墙的博物馆什么都不拥有,却拥有一切。随着每一次技术革新,所有权向大众传递,人们的了解日益加深,数字化的设想和电子网络系统只是以印刷的发明为起点的示威现象中最近的一次。大众复制技术可以使马在任何地方存在,甚至在偏僻的得克萨斯公墓,也使承诺要弄懂过去意义和多次改变的历史学者们头晕眼花。
然而,挪用更加复杂。正如爱德华·萨义德长期以来认为的那样:在每一个文化的挪用中都有行为者和受影响者(those who are act and those who are acted upon),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的记忆和文化认同受美学的、学院的、经济的或政治的挪用的控制,结果可能是焦躁不安和痛苦的,就像是我们开始时所列举的那些人们。研究挪用是为了质疑符号的转换,也是为了承担起艺术史自身创造的这些符号的责任。与传统艺术史中的术语相比——如“影响”——挪用将问题转向了社会中意义的积极的行为者,同时也照亮了历史语境。它剪掉了艺术客体特权似的自律,或者说允许研究那种自律的结构。同时,挪用的观念也允许艺术客体过去和目前的社会效用被公开重申,而不是悄悄地。艺术是重要的,长期以来一直如此。术语“挪用”鼓励我们去问为什么和怎样。
【编辑:张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