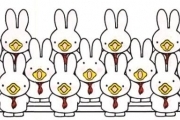新闻背景
在10月下旬于济南举行的“第七届中国体育美术作品展”上,浙江省丽水市油画院副院长李跃亮的参展油画《我小时候》,与陕西省摄影家协会主席胡武功的摄影作品《俯卧撑》惊人雷同。后被网友指出是抄袭,胡武功本人也表示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由此引发艺术创作与摄影之间的版权争论。
胡武功摄影作品《俯卧撑》
李跃亮油画作品《我小时候》
把别人的摄影作品,依葫芦画瓢照搬到油画亚麻布上,再涂上颜色,署上自己的名字参加全国性美展。抄袭事件被拆穿后,昨日,抄袭者李跃亮选择了公开道歉,成为国内类似事件公开道歉的第一人。
10月下旬在济南举行的“第七届中国体育美术作品展”上,浙江省丽水市油画院副院长李跃亮的参展油画《我小时候》,与陕西省摄影家协会主席胡武功的摄影作品《俯卧撑》惊人雷同,只不过把黑白照片“搬”到画布上,变成油画而已。
胡武功的摄影作品《俯卧撑》是他在1996年西安民乐园棚户区拍摄的,画面上是棚户区一条狭窄的小胡同,胡同这边坐着一个大妈端碗吃饭,胡同里横趴着一个孩子,边做俯卧撑边读书。
“油画《我小时候》上签署的作画时间是2003年,而摄影作品是1996年拍摄的,明显是抄袭。”在上海从事创作的油画家王雨超接受采访时称,应该狠刹绘画剽窃摄影风。
王雨超表示,从挂在家里自我欣赏的角度讲,可以把自己拍摄的照片照搬着改成油画,但是如果要把自己拍摄的照片改成油画参加展览,就需要根据照片增加自己的艺术语言和风格,做一些画面元素的改变,这才叫创作;如果把别人的照片依葫芦画瓢改成油画,就成了抄袭。
昨日,记者联系上李跃亮,李跃亮在电话里告诉记者:“我已经跟胡武功老师打了三次道歉电话,也向目前关注此事的《中国摄影家》杂志发了电子邮件,想在上面向摄影界公开道歉,现在先通过你们向公众道歉。”
胡武功是谁?
胡武功
胡武功,1949年7月生于西安,1969年始在部队从事新闻摄影,1975年转入传媒至今。现任陕西省摄影家协会主席。1983年7月31日,采访安康百年不遇特大洪水,所拍摄照片《洪水袭来之际》获首届中国最佳新闻摄影奖及中国新闻特别奖。1984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并出席中国记协在北京召开的表彰大会。先后出版文集《摄影家的眼睛》、《中国影像革命》,摄影画册《胡武功摄影作品集》、《四方城》以及《西安记忆》、《藏着的关中》等专著,主编《中国摄影四十年》、《中国人本》等;(与人合编)大型画册和《摄影美学初探》:多次在中国美术馆、日本东京写真美术馆、香港艺术中心等地举办个人摄影展:应邀参加平遥国际摄影节并展出摄影专题“关中百姓”:近年来先后参加了“台湾一日”、“北京一日”、“贵州一日”、“成都一日”、“澳门一日”等海峡两岸四地的大型摄影活动;兼事摄影评论,从80年代开始就倡导纪实摄影,发表文论60余万字,多次参与国内外的摄影理论交流活动;1987年发起举办“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并于次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同名展览;1989年应邀在日本东京举办“中国现代化进程”摄影展;2003年作为策展人之一于广东美术馆举办“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大型摄影展。曾接受中央电视台、陕西电视台、日本NHK电视台专题采访,为中国摄影界有影响有实力的摄影家。2006年9月在法国巴黎举办“人文中国”个人摄影作品展。2008年与石宝琇联合策展的《中国民间体育摄影大展》在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巡展。
李跃亮是谁?
李跃亮
李跃亮,1966年1月生,浙江松阳人。先后毕业于杭州教育学院美术系、浙江师范大学美术系。1991-1993年中国美院油画系插班进修(期间参加了法国艺术家司徒立“具象表现主义”课程班),2007年9月赴法国、德国、希腊等国艺术考察。现为中国油画学会会员,浙江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浙江省油画家协会会员,丽水市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丽水职业技术学院美术系副教授。以油画风景写生作为主要的创作方式,部分作品被香港、台湾、新加坡、美国等海内外人士、机构收藏。作品参展:1993《雨后》入选第二届中国西湖美术节。1994《盛装》入选浙江省第二届青年美术作品展。1996《午后的阳光》入选建党75周年《浙江——可爱的家乡》美术作品展。1998《秋色》入选巴比松油画赴北京艺术博物馆展。1999《美好的早晨》入选第九届全国美展浙江省展。1999《田垄》入选浙江省教育系统第二届艺术节教师组铜奖。2001《奕山》入选走进新世纪——2001浙江油画大展。2001《春光》入选建党80周年浙江省美术作品展。2001《山树》入选2001浙江省东方杯群星美术书法大展。2005《阳光下的南山》入选月映浙潮——2005浙江油画大展。2005《春到山村》入选浙江省第二届乡镇美术作品展优秀奖。2005《花卉系列》参加温洲首届艺博会。2007《浙南秋声.》入选中韩油画邀请展。
质疑声音
姜纬:胡武功被抄袭了吗?
巧得很,我除了摄影,其实我还做绘画的事情,比如策展,比如写评论,比如编辑出版画册,只是摄影界的人不晓得而已,这再一次证明了雍和对我说的话:“这个圈子太小了!”岂止是小,我想说:还太浅了。
胡武功摄影作品被画家抄袭了吗?舆论基本上是一边倒的肯定。但我看未必。
严培明这个人听说过没有?没有的话可以上网去查查。他是我朋友,也是上海人,1979年就去了法国。严培明1999年在巴黎先贤祠的个展,从大厅里一直延伸到大门外,先贤祠的大门在他展览期间是关不了的,先贤祠在法国是什么样的地方、是何等地位,请再去查看一下吧。2009年,卢浮宫为严培明举办个展,他因此成为继毕加索之后,第二个在卢浮宫办个展的当代艺术家。严培明有一张大画,颜色黑白灰,就是用绘画复制了埃迪•亚当斯获1969年普利策奖的摄影名作《枪杀越共》,这张画在欧洲各地展出,没有人质疑它是抄袭。严培明许多绘画,其实都来自于照片,比如他画过的毛泽东、李小龙、希拉克、奥巴马、教皇等人物的肖像,还有其他反映社会问题的绘画。
1969年普利策奖的摄影名作《枪杀越共》
2004年德国曼海姆美术馆的严培明个展现场图片
为什么在法律严苛的西方没有人说他是抄袭?这是因为人家懂事明理,知道经过绘画以后,那叫艺术“再创作”。画家为什么挑选了那张照片?是什么打动了他?他通过挑选、复制这个过程,到底想发出什么声音?——艺术家用自己的大脑思考以后,根据他自己的理解,进行了“再创作”,而且,这样的“再创作”作品,它往往也不是一个单独的作品,它往往是被放置在一个组织过、策划过的展览场地,和周围其他作品一起,构成了一个语境、一个重新解释世界的场域。
就比如严培明复制埃迪•亚当斯《枪杀越共》的这张画,2004年时我看到过在著名的德国曼海姆美术馆,在这张画的旁边,就是严培明复制西班牙绘画大师哥雅的名作《1808年5月3日夜枪杀起义者》,这些作品和其他有关枪杀的东西放在一个展场内,共同建构起了艺术家想要达到的效果。
《艺术世界》杂志2006年第11期里有一篇刘铮的访谈“图片的选择是我内心的独白”,正巧也是涉及到了影像“复制”与“再创作”的话题,限于本文篇幅,现选摘如下——
ArtWorld:从你的新系列作品《太阳底下》(2005-2006)当中,我了解到你所“拍摄”的照片全部都下载于互联网。互联网上充斥着相片素材,有些具有新闻价值和历史意义,有些具有科学性、娱乐性,有些带有强烈的情色、偷窥暗示,有些具有社会性或心理探究意义,还有些是以上所有的综合。你怎样从中做出选择,来限定你这本新作的范围?
刘铮:这些图片并不是完全下载于互联网上的,还有一部分是DVD影碟的截图文件。可以说这些图片的来源包含了所有我们经常涉及的影像范围。同我以往的作品相同,关于历史、情色、战争的成分占有的比例比较大……
ArtWorld:你随意更改、个人化你在互联网上获取到的真实的照片。你难道不担心有人会控告你侵权么?不但心被指责模仿ThomasRuff、RichardPrince、SherrieLevine或其他任何一位在他们的作品中运用过类似手法的艺术家?
刘铮:我不认为这其中存在侵权的问题。正如你所提到的上述艺术家,他们也曾做过类似的事情,正是因为他们这些伟大的尝试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和尊重。对于人类文化现成品的再次创作问题在艺术史上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被淹没于一个影像的海洋之中。在互联网上,电影屏幕上,电视上,杂志上,展览上,数不清的图像充斥着我们的眼睛。我们怎么办?我们多年以来就像一只被掐住脖子的鸭子,不管你是否愿意接受,这已是一个事实。影像的重要和丰富已无可避免,而且已经侵犯了我们原有的生活。对于这种状况我们不可能没有一种态度。这些图像正在逐渐地成为物质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像一棵树,一块石头一样,搭建着一个新的意义下的世界。面对这样的局面我不可能再无动于衷。就如同按动相机的快门一样,我开始选择我面前的图像。这个过程是艰辛和困难的,难度和拍摄一张优秀作品的难度没有区别。在我选择它为我目标的时候,它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环境中简单的图像,而我后来更多的工作又进一步赋予它们新的意义。
ArtWorld:为什么说挪用已有的大众散发的照片是你目前一项很有意思的工作?这项工作在中国当代艺术界的背景下有什么重要性?
刘铮:挪用这个词并不准确。只能说是这个作品创作的一个源泉……它使一个毫无品质的东西变得可以观赏,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改变。这里有艺术的本质存在。这项工作是一项纯观念性作品,它体现了一种态度,是一种对世界上所有影像遗产所展现的一种态度。在这些影像面前,我们不是手足无措的,它们会激发我们,我们也做出自己的反应。它们可以成为艺术家作品的重要组成要素和创作动因。
我想在今天中国的现代艺术领域中,这组作品更加强调了观念的重要性。一切技术和生产规模在艺术创作过程中都是次要的。
ArtWorld:你把自己看成一个运用摄影技术的艺术家还是一个摄影师?
刘铮:我是一个由传统摄影师转化成的一个运用摄影的艺术家。我不同意占为己用这样一种说法。人类的认识来自于对物质世界直接的认识,及对他人经验的间接认识。其中所有人类的影像资源都有被他人再认识的义务。当它出现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它就必须接受人们的评判和再利用。这种再利用并非是占有,而是给了它又一次崭新的生命。同时,我也不否认在借用影像资源创作中所存在的巨大创造空间。试想从众多的影像之中选择一幅需要的影像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它是在你所有以往对影像的价值观及影像创作经验的结合下以及对社会、历史充分细致的观察下获得的结果。因此,这样一项艰巨的工作恐怕不能简单地称作“占为己有”。我将它看作一个原创作品在进行,而且付出了很大的艰辛。
摄影师PatrickCariou曾经起诉过这个访谈中谈到的RichardPrince,说Prince未经同意就复制了作品,而Prince在回应中是这样说的:“Cariou的相片并不具有‘绝对鲜明的特征’……这些图片也没有决定我作品的最终价值,事实上,我运用这些图片提高而不是降低了这些图片的价值。”
SherrieLevine则“翻拍”了爱德华•韦斯顿的经典影像,并标示为他自己的,被评论家认为恰恰是遵守了鲍德里亚的规则。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1940年以来的艺术:艺术生存的策略》ArtSince1940:StrategiesofBeing中,乔纳森•费恩伯格(JonathanFineberg)曾断言:“1940年以来,天才式的艺术和艺术家已经不复存在了,策略是当代艺术基本的生存方式。”而事实上,上述这些艺术家及其作品的背后,的确是有着譬如让•鲍德里亚(JeanBaudrillard)、盖伊•德博尔(GuyDebord)等等思想家的身影。他们这些人关心和探讨的,绝不仅限于翻拍或复制几张图像作品那么简单。如果要展开叙述的话,那将不是本文所能容纳的。
其实,这样的事例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也很多,只是许多摄影界的人,根本不了解这样的语境、这样的情况。
比如在2000年10月开幕的上海双年展期间,有一个名为《不合作方式》的名噪一时的外围展,其中艾未未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作品,就是复制了卡蒂埃•布勒松1949年拍摄于上海的名作《黄金挤兑风潮》,这幅巨大的复制品悬挂在墙上,地上是一叠稍小点的复制印刷品,艾未未在旁边写有一个小小的牌子:“请自取一张”。
卡蒂埃•布勒松名作《黄金挤兑风潮》
2000年上海《不合作方式》当代艺术展中的艾未未作品
比如原上海美术馆执行馆长李向阳、画家陈丹青,他们都有绘画系列复制了南宋画家马远《水图》和明代画家董其昌的册页。
再比如十年前轰动一时的蔡国强《收租院》事件,这组获得威尼斯双年展大奖的作品,也是被许多国人视为抄袭,还打官司,结果根本不成立,一是这些人低估了精得要命的蔡国强的智力;二是低估了威尼斯双年展对于艺术规则的了解,以及对于中国以及国际有关法律的了解程度,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的艺术主持人哈洛德•塞曼(HaraldSzeemann)认为,蔡国强的作品没有侵犯著作权,在他看来,蔡国强的作品不是《收租院》的复制品,而是对雕塑性价值的一个重新解释。他还认为,著作权在当代艺术中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就像对影片和录像片断的使用。如果蔡国强的作品是侵权,那么安迪•沃霍尔和许多其他艺术家也都侵犯了著作权;三也是我们许多人根本不清楚何为当代艺术“挪用”或“复制”现成品的创作理念和手法,结果可想而知。
在我看来,李跃亮没有必要道歉,可他偏偏道歉了。但是,李跃亮的道歉并不能因此而说明他的“做法”有多大的错,只是证明他在舆论的压力下产生了可以理解的恐慌,只能说明他个人有“错”,错就错在他根本就不是艺术家的料,因为他不清楚他其实是经过了再创作,现在看来,他就是一复印机、扫描仪。而舆论也是错的,你们这次很幸运,遇到了李跃亮。
我们现在一方面对于自己应有的公民权利屡屡遭遇侵犯装聋作哑、麻木不仁,另一方面则表现出欺软怕硬、斤斤计较的小家子气,过分的过敏,不问青红皂白,好像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伤害。许多摄影从业者,只看见自己眼皮底下那一亩三分地,既孤陋寡闻又狂妄自大,缺乏足够的视野,身处信息时代却又没有选择、处理、消化和运用信息的基本能力;而那些不懂装懂或者惟恐天下不乱的舆论媒体,自以为在打抱不平,掌握了公正和真理,胡乱起哄,起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作用。
最后,我想说:如果您处处搬出法律条文来说事,如果您振振有辞说什么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任何人的行为都得在法律的范围内操作,那么恭喜您了,您说得非常正确,您是个规矩人,但是您为什么要做艺术工作呢?您直接去做法律工作者的话,我相信一定是非常成功的。说到底,您再怎么说破天,我也坚信法律和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能够、也不应当重叠的。为什么会说“著作权在当代艺术中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这是很明白一个道理,人的精神生活,需要艺术家这样的“野孩子”左冲右突,它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有趣、异样、生动、丰富多彩。世界在需要比尔•盖茨、政治家和法官律师的同时,也需要一些“养尊处优”的艺术家。从小到大,父母、老师、领导都苦口婆心教导我们: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这个是正确的,那个是不对的,是啊是啊,我们太清楚什么是正确的了。可是,正确的东西却往往是无趣的。人一辈子所有去做的事情如果都是正确的,那么,这样活得有意思吗?
两年多前的纽约,罗伯特•弗兰克的妻子JuneLeaf,其本身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艺术家,老太太她问别人道:“你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么喜欢付羽的照片吗?因为他每一张照片里都有不对的东西。”我们有无数的照相机,可我们的眼睛早已瞎了。
【编辑:张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