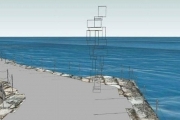他或许是中国摄影圈中最充满争议的一个,也是获国外摄影奖最多的摄影师之一。有人说他是“英雄”,也有人认为他是“靠揭家丑”获得国外摄影大奖。在圈子内,大家因其“拍摄动机不纯”,给照片“做手脚”对他避而远之,却少有同行在面对《西部淘金》《矿工》《非典》《中缅交界处的吸毒者》《青藏铁路》《沙漠化问题》《艾滋病村》《中国的污染》这一系列专题图片时,因自己的无为而汗颜。
卢广在摄影圈中的口碑不算太好。
严格来说,他甚至不属于这个圈子。只念过7年书的卢广32岁才来到京城正式学习摄影,却在35岁就拿到了中国摄影艺术的最高奖——金像奖。接着他一路获奖无数,一直闯出国门。10月14日,卢广凭借组照《关注中国污染》成为大陆首个获得尤金·史密斯年度大奖的摄影师。此前,他的作品《艾滋病村》曾获荷赛金奖,中国摄影金像奖、尼康杯全国摄影大赛金奖等国内奖项也曾尽数被他收入囊中。
这个当过最底层的挑沙工人的拍摄者,总是喜欢去捕捉那些耗时长、危险、敏感且边缘的拍摄主题,比如西部大淘金、吸毒者,比如偷猎者、艾滋病人,通过这些题材揭开中国最丑陋的一角。为了拍到好照片,他可以持续几个小时死守,也可以坚持好几年不间断回访。对于摄影,他有令人讶异的毅力和信念。
而另一方面,对这样一个“半路出家”的摄影者所收获的成绩,新闻摄影圈内的人私下的第一反应大多是“急功近利”,甚至是“人品有点问题”。人们对他的争议和质疑集中在照片Photoshop处理的痕迹太重,摆拍、图片说明模糊、日期出错及其拍摄目的不单纯、拍摄手段不“道德”等等。
多年来,他就这么一直处在中国新闻摄影界争议话题的中心,摆拍、向被拍者塞钱、作假等质疑不断出现。几乎每一个前来采访他的记者在肯定他成就的同时,都会问到他那些传说中的“小动作”和“小伎俩”。
面对这些质疑和争议,卢广有一套解释和逻辑。十几年来,他数次陷入圈子里的口水战中,仍坚持着自己的价值观一路独行。
卢广属牛,一副标准的摄影记者体征,体格结实,衣着简单而朴素。
这次获奖以后,媒体、网络上再次充满了关于他的各式评论。有人说他是“英雄”,抑或“靠家丑获得外国利益的汉奸”,也有人说,卢广这是在“坏人办好事”……
只为“结果”的摄影
11月11日晚,卢广坐在电脑前,熟练地用Photoshop处理一张刚从河南洪河回访拍回的照片。
照片上的女人表情痛苦地侧躺在床上,她只有40多岁,但看起来远比这个年龄苍老。被子掀在一旁,露出她因患乳腺癌而被割掉的乳房,以及大腿后一个触目惊心的大疮。昏暗破败的房间里爬着苍蝇。
洪河流域是典型的癌症高发区,卢广说他之前在这里拍到的癌症患者很多都已去世,而这个女人也在垂死边缘。
照片中,床的部分太亮,卢广在电脑上把亮度压暗了一些。这样一来,整个场景显得更加狰狞而凄厉。
“这个效果不可怕,现场比这个可怕得多,因为她一直在哭喊、呻吟。你到了现场会哭的。”他边调照片一边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这是卢广对2005年起就一直拍摄的污染题材的一次回访。那年,卢广发现内蒙古109国道旁烟囱林立黄烟滚滚,国道边竟然耸立着一块牌子:“欢迎光临中国最大的高耗能工业园”。
他当即决定开始关注中国的污染问题。“我没什么其他长处,就是有毅力。”之后5年,他的足迹从西部黄河中上游沿岸逐渐向中部、东部扩展,沿着淮河、黄河、长江三条河流,记录下不少污染造成的悲惨故事。他用广角镜头拍一个老人难以忍受臭气而捂住鼻子的、干裂的手,用长焦拍一老一少为新逝的儿媳上坟时的一步三回头……
“去年一年间,在江苏的盐城、连云港,我被当地领导抓过四次,直到验证过我的确是浙江永康的一家影楼老板,不是媒体记者才让走。最长的一次关了3小时。”卢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这是在污染严重的敏感地区拍照,必然会遭遇到的“危险”。去年3月,一个农民带卢广去连云港化工园区的灌河口,正好看到很多工人在偷偷挖延伸到深海的排水口,以便排放废水。他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画面,立即掏出相机。这时一个管委会的负责人过来,很凶地责问他是谁,为什么拍照,工人们也奔上前来压住他,要抢相机。卢广死死抱紧相机,大喊,“我是浙江人,来旅游的!”众人僵持了好一会,还是把卢广拉到了管委会,专门找了一个人看着他。
今年6月,他曾趟着泥走了半个多小时,找到江苏常熟市氟化学工业园污水处理厂从江底延伸了1500米之远的排污口。看到远处哗哗往上喷的黄色水柱,他激动得顾不上风雨天气,向附近捕鱼的渔民租船划到附近。等了1个多小时,却由于雨天涨水淹没了出水口而没拍到。
回去后,卢广又等了3天,到天气慢慢转好,他再次租船来到那里,一圈圈地绕着排污口拍了很久。
“神通广大”的卢广
卢广真正的纪实摄影生涯始于1994年。那时他刚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美院)摄影研究生进修班毕业。当时的老师对他说,你应该做属于自己的一些事。
卢广想跟别人不一样。考虑再三,他决心像拍摄希望工程“大眼睛”的著名摄影师解海龙一样,选择专题式的纪实摄影作为自己的发展方向。
1995年拍完《西部淘金者》以后,他突然想去云南拍吸毒者。跟几个老师一聊,他们都说,那些地方的毒贩子不像淘金的农民工,都是有枪的,太危险,还是别去了。卢广不觉得怕。到了云南,他听说瑞丽有很多吸毒的人,当即坐了20多个小时汽车前往瑞丽。可即便到了瑞丽,要找到吸毒者也如大海捞针。
最后,他来到国境线上一个小村子,发现有很多人在一间屋里赌博,他掏出200块钱,也上桌赌,一边跟旁边的人闲聊,“毒品一般在哪里吸?”那人笑笑说,“你想吸毒啊?”卢广也跟着笑。
他很快就输光了,便收拾摄影包准备走。这时,旁边那人突然说声“等等”,他找来另一个人带卢广去吸毒的地方。两人一起走出村子,穿过一片田野,走进一处已在缅甸境内的茅草房。卢广激动起来,他看到了很多人在里面吸毒。
为了能混进去,他先问了问价格,并掏出20块钱,那人真的给了他一些海洛因,还教他怎么吸。卢广吸了起来——他小心翼翼边吸边吐。出发前,他曾请教过很多人如何避免吸入毒品。
吸了几口,卢广掏出一个小傻瓜机,对旁边的吸毒者说:你能帮我拍张照么?我想做个纪念。那人同意了。接着他又说,“我也帮你拍一张吧!”
这是第一次他拍到吸毒者。
接下来,卢广通过汽车站小旅馆拉客的人,找到了另一个吸毒聚散地。头几天,他耐住性子,只观察里面的吸毒者和妓女,跟他们聊天,最后,经常在那里吸毒的女孩终于带卢广到她和另一个卖淫女的住处,给他香烟,教他如何把白粉放进去,烟丝抽出来,用唾沫把烟弄湿,以便其慢慢燃烧。
那时候,卢广头发长长的,他告诉她们自己是画家,要用傻瓜机拍点照片拿去画画用。“她们也无所谓,反正都熟悉了。接下来一星期里,扎针、吸毒、拜神、贩毒,什么都拍了,拍了十几个胶卷。最后一天他还拿了大相机去。
照片获奖后,卢广的拍摄方法在新闻摄影圈里引起了极大争议,有人诟病他在当地与人称兄道弟,回来却发表照片、出卖朋友。十几年后,同样的争议又发生在他的组照《喜马拉雅的枪声》上。除此而外,“枪声”那组照片还因其图片说明“有意模糊、隐瞒新闻事实”,而被取消中国新闻摄影“金镜头”奖的获奖资格。
而对质疑卢广的人们而言,他的“罪状”远远不止这些。
2003年“非典”期间,卢广通过自己一直供稿的报社提供的介绍信,最早混进了急救中心和病房拍照。一天,他看到几名医护人员提着急救箱朝自己的方向走来,准备出车去抢救病人,他马上蹲了下来,大声冲他们说:“你们能不能快点过来?”
“当时他们看到我在拍照,就有意配合我拍这个照片。我咔咔咔连拍三张。”卢广对记者说。
这张照片后来被《三联生活周刊》等多家媒体以显著篇幅转载后,遭到众多圈内人的责疑——跑在最前面的医务人员将手里的车钥匙高高举起,很多人认为这有明显的摆拍嫌疑。对此,卢广的回应是,“这是真人真事。当时的隔离服是没有口袋的,车钥匙必须拿在手上,这是合情合理的啊。”
5年后的2008年初,新闻摄影界元老、中国青年报摄影部主任贺延光在取消了《喜马拉雅的枪声》的奖项之后,公开发表《卢广,为什么出错的总是你》一文,文中回忆说,自己在SARS期间曾与卢广在地坛医院里一起拍了18天照。当时“卢广风风火火,挺规矩的”。而在他先离开医院后,很快接到仍在医院采访的一位同行电话,说有个病人死了,卢广非让医护人员面对遗体双手合十,做祈祷状,场面弄得很尴尬。
贺说当时就给卢广打了电话,“他对我非常感谢,说‘只有你贺老师会直截了当地说我,别人都不会’,而且当时他就哼哼唧唧地承认了这件事。”
事后,卢广则在博客中对此事予以否认。让贺延光更不能接受的是,“后来他出了一本图文并茂的书,还是把他拍的那个假照片作为好照片收进去了。”贺说道。
《卢广,为什么出错的总是你》也使新闻摄影业界围绕卢广的争议达到最高峰。文章中的发问也代表了新闻摄影界同行难以接受卢广的一个重要原因:“我曾经很敬重卢广,我知道他很热爱摄影并为此付出不少艰辛,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热爱摄影?难道除了得奖,做摄影就没有别的意义了吗?”
在争议中找到价值观
卢广没有通过文字回答贺老师的这个哲学式的追问。
不过回溯他的30年摄影之路,或许答案就在其中了。
30年前,摄影对卢广的意义只是赚钱。
卢广只上过7年学,中学念到第二年就去干活了,他做过木匠、泥水匠,卖过红枣、苹果,还去挑沙子,每担八九十斤重,可以赚几分钱,一天能挣到7毛钱。那时他15岁。
1980年,19岁的卢广试着拍了一张风景照,卖了4分钱。于是他没事就借相机去拍风景,再以每张5分的价格卖给当地的小和尚和小摊贩,一年下来居然赚了60多元。春节单位放假时,他骑自行车去一个山区,给别人拍全家福,7天下来净赚260多元——那时候卢广的月工资仅有17块。
1985年,浙江省举行了一个主题为“春”的摄影比赛。卢广送去很多关于改革开放的照片,获得了特等奖,得到一台价值六七百块的电冰箱。这大大激发了他学摄影的热情。
接着,卢广开起了照相馆和广告公司,到了1993年,这个精明的浙江人手头已经有了10万块。这时,他做出了一个连父母都不理解的决定——去北京学摄影。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大目标:2年时间加入中国摄影协会。结果只用了一年,他就如愿以偿。
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习期间,摄影对卢广来说已经变成了一种爱好,一个前进的方向。完成《淘金者》《吸毒者》等几个小专题的纪实拍摄后,因为钱用完了,1996年他只好离开了北京。回到老家后他专心经营广告公司,商业才能再一次得以展现——2001年,当卢广杀回北京时,已经有能力购置一套大房子,并且可以支撑自己未来一段时间的拍摄费用。
回北京后,他在报纸上看到一个豆腐块大小的新闻,说一个8岁女孩,2岁就患上艾滋病,来北京求医。卢广不解,为什么这么小的孩子会得艾滋?他通过报社找到女孩的父母,了解到河南有很多艾滋病人都是通过卖血感染上的。他立即决定去拍他们。
1994年,卢广拍摄西部淘金对藏民生活的破坏性影响后,引发强烈反响,2006年,西藏关闭了全部金矿,狂热的淘金时代结束。1995年,他的《小煤窑》组照促使相关文件出台,很多西部小煤窑也随之被关闭。
卢广开始觉得,自己拍摄真的可以改变一些事情。
对艾滋村的拍摄使卢广的心态开始发生巨大的转变。看到那些痛苦的艾滋病人,他觉得自己应该、而且有责任去帮助他们改变生活。这一想法在他后来的拍摄(尤其在关于污染的拍摄)中一直延续了下来。
每到一个污染重灾区,一些走投无路的村民看到卢广手里的相机,都抢着向他喊冤诉苦,欢迎他去自己家里拍照。受污染所困的人们心中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北京来的摄影家”身上。
卢广将有的照片被寄到环保部门反映情况,有的作为写抗议材料的档案送给了村民,有的则在媒体上发表。但直到获得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后,“污染”组照才真正引发了大震动:媒体蜂拥而至,甚至连“环保”“污染”也随即成为热搜字眼。
接下来能得到什么样的改变?卢广不知道。但他认为,“至少要先记录下来。”
“我的价值观就是一种社会责任。”卢广对《中国新闻周刊》这么总结他的拍摄。
现在的卢广,一方面,面对仍然存在着巨大污染的城市乡村,他决定继续完成松花江、珠江等几条河流流域的污染调查拍摄。另一方面,面对与照片、获奖同时存在争议和不屑,卢广坚定地反复定位自己不是“新闻摄影者”,而是“纪实摄影者”或“自由摄影师”——新闻摄影的规则不属于他。而他也再不会像前些年在《中国青年报》“十佳记者”评选颁奖时那样,公开提起自己为了让吸毒者扎针,如何向他们塞一两百钱的“拍摄经验”了。
【编辑:张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