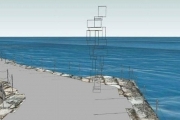沉默、犹疑、迟钝的身体、迷惘的表情、混浊的眼神、裸露的身体和同样裸露的灵魂,展现的是看不见的痛苦、战栗和听不见的哭泣、呼喊,刺痛的是观众的神经。
向京、瞿广慈被称为艺术圈的“模范夫妻”,是公认的当今中国市场最成功的雕塑家之一。据报道,夫妇俩一年在国内拍卖的总成交数额比其他雕塑家的总和还多。
对自己的创作,她的自我阐释是:“我和你面对面坐着,其实‘我’的模样,咱们彼此之间永远也不可能真正知道。你跟一个人朝夕相处,你的丈夫、你的孩子也完全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经常会产生一种隔膜感、陌生感。我能控制的、能把握的,只有我自身以及目光所及,所以我特别想在作品里面呈现这种感受!”
向京简介
1968年生于北京,1995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作品为中央美术学院、北京当代美术馆、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等多家美术机构和私人收藏,为当代雕塑家代表人物。曾举办过《白日梦》、《镜子里的女人》、《保持沉默》、《你的身体》、《全裸》等个展。
夫妻俩成立“X+Q雕塑工作室”:
我这人要不是艺术家
肯定是神经病
“我这人要不是艺术家,肯定是神经病。”向京做雕塑,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解决自己的思想问题”。她说从小有两个问题想不明白:一是“为什么要有我?”二是对自己“为什么是女的?”始终不能接受。
向京成长在北京,父亲是电影厂厂长,母亲是《人民文学》杂志编辑,家庭对她的早期成长影响很大。自13岁考入中央美院附中,她已开始接触专业的学院教育。当初选择雕塑系却是盲目的,“就想学完全没接触过的,而且我喜欢‘干活’,我选的两个专业都挺累人,另一个是学铜版,铜版机巨大,我摇都摇不动。大概是因为我属于‘行动派’。”
身在学院却乐与“学院”为敌
在学院教育中,向京记得老是被老师打击,“学院”成为她要面对的第一个敌人,她希望一件作品有自己的语言,而并非只是讲求技术,也不是简单的合乎比例。毕业前,她和寝室里几个女孩子一起在北京当代美术馆举办了“三月四人展”,当时做展览的人很少,老师也很反对她们的年少轻狂,但这个展览吸引了大批观众,即使现在大牌艺术家的展览也未必能招来这么多人。可以想象,在统一教学的环境中,做出有个人风格的东西很容易出挑,在这个展览上展出的作品也给她带来很多机会,毕业作品《护身符》等获得中央美院毕业生作品展一等奖及日本松冈家族基金会一等奖,作品被中央美院收藏,一出道就小有斩获。
中央美院毕业后,向京在《大众电影》杂志做了3年美编,一周只上3天班,她原本打好如意算盘,剩下的空闲时间可以做雕塑。“但同时做两个摊子并不容易,我这个人又没有那么分裂。”这段郁闷的人生经历让她看到,什么事情是她不愿意做的,慢慢这些事情消化掉,才有如今的纯粹。纯粹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2007年她与先生瞿广慈结束了上海师范学院的教职,成立“X+Q雕塑工作室”,成为自由艺术家。她很珍惜这种梦想中的生活,天天按时到工作室“上班”。
不提供合乎想象的女人形象
自“三月四人展”以青春少女题材在艺术界崭露头角,向京围绕这个题材,用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做了多年创作,这些女性形象也许不可爱、不讨好,她们带着青春期迷惘的表情,真实、却又不是真实的简单再现,像青春一样耐人寻味。
之后,她摆脱浓烈的个人经验,创作语言有了很大的改变,一些女人形象与青春背道而驰,完全袒露自己疲沓的身体,堆砌肉感却毫无美感。对于没有美感的说法,向京并不认同。“我不太苟同那种时尚、传统艺术给予的所谓美感,即简单审美的东西。”她说,“艺术要揭示人性更深处的东西,我觉得那才有意思。审美在我看来意味着去看一个人真正心灵的东西,这才是最重要的。”她并不打算提供一个合乎大家想象的女人形象,因为那根本没多大意义,而且那样做得已经太多了。
有人认为向京所采用的传统手法已经不当代了,装置才是先进的,雕塑是落后的。“这样的话,岂不是艺术太有答案,太有标准了。当代性指的是一种当代精神,并不是一个手法。”“当然,我认为任何一个当代都是杂乱不堪、泥沙俱下的,身处其中肯定很迷惘,只能自己不停去梳理,想办法在很小的可能性里去摸索,找到你可能找到的答案。”
因为拥有尊严
她们获得美感
在北京驼房营东风艺术园宽敞明亮的工作室里,女雕塑家向京一身工装,五官雕塑感很强,一头卷发披散,她如一名拥有魔力的吉普赛女郎,纤瘦而敏感的手指塑造过很多女人形象,被认为带有鲜明的女性主义艺术特征。“我们不是把她当成一个审美对象,合乎所谓标准,而是正视一个真实存在的女人,从中发现,由于她拥有尊严而获得的美感。”
每次转型都要搬家
今年3月,“老北京”向京与同为雕塑家的先生瞿广慈把整个工作室自上海搬回了北京。此次搬家动静很大,随同一起搬家的除了多年的雕塑作品和家当,多达近10名的助手团队,还有三条从小养大的狗。“其中两条老狗不断生病,搞得我整个像当妈似的。”她乐呵呵地笑了。
回忆10年前刚到上海师范大学创建雕塑系的时候,向京说,那时她的创作需要转型,搬到上海正好给了她转型喘息的机会。上海艺术家比较少,跟艺术有关的氛围,包括物质资源也特别欠缺。后来他们把一个老仓库租下来,自己做了不少工作才凑合能用,但周围全是干货铺、修理厂,根本谈不上艺术区,刚搬过去的头一个月遭了4回贼。不过,在上海的生活是清静的,那段时期她攒了大批作品,到目前为止,创作最集中的还是在上海。
“人生就像冥冥中已经安排好了,在上海做了10年以后,当我又想转型的时候,刚好又回到北京,这的确是一种机缘巧合。”
结束在上海10年的创作生涯迁居北京,她发觉自己的创作速度慢了下来,因为“北京太好玩了,很多朋友吆喝一起出去玩”。在上海的最后时间,她已经开始觉得“营养不良”,几乎快“断气”了。到了北京,很明显有了“充电”的感觉,人都活络起来。
对话向京
雕塑女性“身体”如同“治病”
记者:您的作品中为何总凸显鲜明的女性主义特征?
向京:实际上,中国所谓的女性主义都是搬自西方的,与本身的自觉没有关系。我只能说,因为我是一个女人,而且我也看到身为女人去做事情、存活的难处,我做作品时自动从这个角度去切入,好像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选择。因此我绝不会去做愉悦别人的作品,否则本身也就丧失了作为女人的立场。
记者:您认为女性雕塑家与男性雕塑家相比有没有优势?
向京:应该是个体的问题。男女思维方式的不同,当然也会表现在作品上。女性的局限很明显,国外就有一本著名的书叫《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很多女性艺术家后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做不下去,包括家庭、世俗的包围等等。这取决于个人的选择和付出。
记者:是否已经对今后的创作有了明确的方向?
向京:有一段时间我老做女人、身体,就像一个人有病老得治,但有一天病好了,就不需要再吃药了。释放到一定程度,自己也觉得差不多了,不用再絮叨这些事了。去年我做《全裸》展览,专门做了一批女性主义作品,关于“女性身体”,这个展览算是我对性别题材的告别。既然被贴上“女性主义”标签这么久,总得有个了结。自此,我将不再做跟性别有关的题材,因为我的困惑已经解开了,没必要再去面对它。我肯定会有一个彻底的转轨。
【编辑:张明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