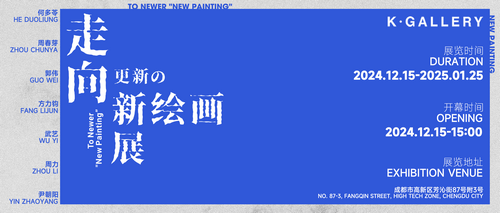从意识到传统笔墨表达方式面对现实生活的荒诞和失落,到自觉地以自己的方式探索中国水墨语言的表现力,脱落掉越来越多的情节和梦幻,愈发给人物对象本身以格外的关注,雷子人看似失去了许多现实的真实,其实却得到了更深一层的真实,一种绘画本身能否在当代生活中安身立命的真实。
记者:您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的专业是中国画,对中国水墨人物画也有过系统的研究与梳理,作品中运用传统书画语言,但却蕴含着对当代人内在情感的解读与剖析。
雷子人:当代与传统并不矛盾,当代不一定反传统。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源头,绝非无中生有,当代是传统的衍生。同时,创作纯粹传统水墨画要有时代背景,上世纪80年代末期,我开始接触西方艺术构成,进行过一些实验性创作。那时,中央美术学院的学习氛围很开放,相容并包,提倡试验性,但对教授传统绘画也不放鬆。学生时代,我的作品在笔墨上较多沿用了传统技法,但更多是在表现青春气息。1998年前后,我的作品似乎有了些当代意味,画中有情调、情境、趣味,但张力不够,结构感不强。
记者:在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您曾经到出版社工作,此后又回到中央美术学院学习、任教。
雷子人:是的,在出版社工作,基本处于纯艺术圈的边缘,但是我并没有放弃画画,那时的工作氛围与艺术有一定距离,之后我通过考研究生的方式回到了中央美术学院。
记者:边缘氛围对您以后的创作有影响吗?
雷子人:边缘状态让我有回望艺术圈的意念,反观自己对艺术的认识,通过“圈外人”的眼光确定从事艺术创作的意义,并能够客观理性地看待作为艺术家的身份与角色,一方面会思考大众审美等趣味问题;另一方面仍会考虑如何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而不是一味地附和大众。
记者:您的画面清新、率性,但隐喻着一些对文化的反省。
雷子人:在画里我不喜欢表现暴虐、残酷或阴暗等情绪和状态,更倾向于呈现“明亮”,更愿意赋予明亮多重解读空间,不是一目了然,也不给价值判断。譬如画中的男女,他们是构筑整个社会的两个因素,是此岸与彼岸的关係,观想状态下可以有关于人之外的想像与阐释,诸如人性、社会性,美丑善恶与审美有关係,也藉以照见自己。
记者:您的画里总有对女性的关注。
雷子人:是的,画面中多次出现小男人、大女人,以男人的某种视角看待彼此,既游戏也设计,荒诞、滑稽与真实并存。
记者:好多画里频频出现女性与马的形象,有何特殊用意?
雷子人:所谓的“马”,并不是具象意义上的马,近期创作的作品中也有所涉及。我并没有真正描绘马的造型,只是借用动物的面具,在我熟悉的动物里截取了部分元素,最终组合成与人若即若离的关係存在。它的形象往往是自我、陶醉,被解读的空间更宽一些。可以将其角色进行移位,更多的是一种符号,可以是观者,也可以是我自己,有若干种可能。同时,这种场景化的描述,来源于生活中的“一剎那”,这种“一剎那”随时都可能遭遇。它无时不在,不可能真正抓住,但我时刻都想让其停留,有关美的、想像的、失落的;既表像,又抽象。
记者:生活由很多“一剎那”组成,您在创作中如何把握?
雷子人:我更多的是把握梦境,梦与生活经歷有关,在现实中失掉的、没抓住的,企图用画的形式復塬,或者是对以往生活的留恋,对未知世界的想像。
记者:您以江西渼陂村为题材创作出一系列作品,通过水墨、油画、影像等形式全面表现出来,当初出于怎样的考虑创作该系列作品?
雷子人:用艺术的眼光来看这座有800年历史的古村落,画画只是关注这个村落族群的一种形式,我运用了一些跨界的艺术手段,包括一些社会学的方式,如田野调查、影像以及文字等。
记者:您的“渼陂”系列作品在您所有创作里是个特殊的系列,您希望这系列的组画最好的归宿是什么?
雷子人:有完整独立学术研究系统的美术馆收藏,保留其完整性。
【编辑:小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