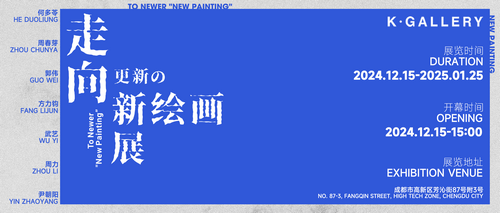历史在人的作用影响下不再明晰通透,显得迷雾重重,欲说还休。而沈嘉蔚又独独对历史画钟情有加。自1970年离开江南的故乡,他的人生仿佛注定拥有了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在北大荒建设兵团成为战士的岁月让他的绘画创作更贴近生活,而有别于同时期突出的“红光亮”。1974年,他以“珍宝岛战斗”为背景创作的油画《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站岗》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得到江青的表扬而红遍全国,作品在文革后退还时却已经伤痕累累。作者不忍目睹收藏于故宅床下。多年后精心修复得以复出,展出于古根海姆美术馆。作品的遭遇与历史境遇的重合,使这幅绘画超越了作为单纯绘画作品的意义。作为文革美术的代表作之一,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嘉德2009年5月29日春季拍卖会首日拍卖场上,《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站岗》以795.2万元高价成交。作品《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布面油画。尺寸:189×159cm。背面签名:黑龙江建设兵团四师四十二团沈嘉蔚1974.5.15上画布;7.1完稿。
1989年的美术创作处于中国向世界开放背景下,也是向西方100年的现代美术史的开放。中国美术创作语言的多样化如井喷般呈现。在以后1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艺术家对西方形式语言的模仿以及对观念、哲学的学习融合,逐渐形成独特的中国当代艺术景观。沈嘉蔚在1989年离开祖国飞往澳洲大陆时仿佛穿越了艺术的时光隧道,刹那间踏上了后现代主义的国土上。在异国的土地上艰辛的生存与获奖或荣耀都不是艺术家停下艺术探索脚步的障碍。已经在国内开始的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论的探索,大量的阅读关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献书籍让沈嘉蔚重新审视自己创作的方向和思想、观念的表达。恰逢沈嘉蔚在798红三房画廊关于自己的创作历程的讲座,借此机会一窥艺术家创作历程和思想渊源的豹之一斑。
关于历史画的解读
记者:所处年代、文化背景不同的人解读作品的时候可能会有另外一种误读,不同的人理解上会有差异性,您对观众理解您的作品有什么样的看法?不同的国家或者是不同时代的人。
沈嘉蔚:这个话题很好。对我早期的作品来讲,因为我的作品跨度比较大,我已经有差不多四十年画画的历史了,早期的作品,我觉得不妨作为一个历史来读。因为中国社会结构和各方面是处在一个巨变的时期,整个历史环境都在巨大变动的过程中间,按照唐德刚的说法就是三峡,正在过三峡,它是一个大历史,就是变动的一个过程,估计要两百年左右,我们这段又是变动最剧烈的时候,所以一转眼都变成历史了,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六十年,就是前三十年,后三十年,咱们要说的通俗一点儿,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他的社会上面的,从领导层提出来的方针政策,一直到社会大众的思想意识,心理的状态,人际关系,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很大的不同,所以对于前三十年,有生活经历的那些人来讲,他的那一段历史,可能现在来看,都已经成为一个过去时了,所以对于70后出生的人来讲,在那个时代,我们这些作品都是依附于那个时代产生出来的。它对现在的人来讲,可能没有很现实的一些什么意义之类的东西,但是它可以帮助现代的人知道,就像你读那个时候人写的书或者是看那个时候人拍的电影都是类似的,它是一个载体,承载了那个时代的文化,那个时代人的精神面貌各个方面,都在这个作品里面,包含在里面,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文革的作品,从广泛地看,它带有很强的政治功利性质,是一种党的口号的形象化、图解化,这个功能非常强,也是这么要求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有很清晰的一个文学创作的规矩,这个规矩由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所规定的,规定得非常严格,就是你的文艺是什么,作为一个艺术家,作为一个画家,你有什么任务,你的任务是什么,你的任务怎么去完成,怎么样完成是好的,全部都清清楚楚,没有任何个人可以变动这些东西,这个是规矩,必须按照规矩里面这样工作,有限的自由。
文革后从创作方法到语言形式的转变
记者:有一个过程,您在国内的那一段创作历程,尤其是文革那一段创作历程与延安文艺座谈会,对文艺的指导是有关系的,但是八十年代以及出国之后的那段作品又不一样了。
沈嘉蔚:后三十年,差不多整个八十年代开始是一个转变,因为没有八十年代也没有后面。从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突然整个思路打开了,见到的东西也很多,想的东西也很多,所以那个时候普遍有一种离经叛道的愿望和倾向,大学都是这样的。我虽然不是大学生,但是周围也都是这个环境,所以八十年代思想解放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从那以后开始,就是说虽然我给自己定了一个框架,因为这个时候人再也不属于由上级领导给你决定要画什么,要怎么弄,可以自由创作了。因为那个时候可以画抽象、可以画人体、可以画花卉、可以画别的东西,也可以变形。
记者:从绘画对象到语言上都变了。
沈嘉蔚:都变了,然后85年就出现了85新潮,新的一代人出来了,完全没有包袱,甚至王广义就直接拿文革的东西来开玩笑,反讽了,已经到这一步了。我就面临作为一个自由艺术家是决定要走哪条路的,有一个个人选择,我的个人选择几乎没有犹豫的,就是我现在画历史画,这个初听起来好像是一个非常老套的,非常保守的一种选择。其实我那个时候是积聚了很多年对于文革历史画的一种不满,很想在这个领域里面给弄出一个东西来,让人知道还有另外一种路子。
历史与历史画创作的关系
记者:和您原来的个人经验有关系,之前画的那些历史画,您是不满意的。
沈嘉蔚:对。当然你可以广义地说,“站岗”也都属于历史画,现在看来实际上不是历史画了,我指的历史画是指在我出生以前就发生过的事情,只能通过读书了解。对于这种现代主义所要抛弃的文学性、叙事性、写实等,这些我都不能抛弃。因为我觉得抛弃以后就失去了我的兴趣了,所以一开始,我就把自己的艺术追求非常明确地规定为艺术只是我的一种语言和一种方式。我把自己定在一个边缘,历史画就是两种专业的边缘,既是艺术的边缘,也是历史的边缘,历史研究的边缘。我是从这个地方来发展我自己的,已经定得很明确了。唯一有一个不同,就是国内画的和国外画的调整。这个调整典型的一看画就知道,你看我的画《红星照耀中国》。《红星照耀中国》的对象只有中国人能看得懂,外国人看也能看点儿热闹,但是他看不懂。因为这张画有两重含义:一重含义,它尽可能真实地记录下三十年代的中共人物。那些人物的精神面貌、气质,他们的服装,那个时候的样子,就是斯诺所见到的,我把它用油画再现出来,记录下来。但是它还有一层意思,实际上是对文革中间,对共产党历史篡改,按照当时的术语来讲叫拨乱反正,回到一个更加真实的历史面貌上来,因为文革中夸张得一塌糊涂,完全是不一样的,而且画家也不研究那个东西。说那个时候戴红领章帽徽,八角帽,灰颜色,衣服都是标准化的,不可能,那个时候根本不是这样的,我整个都在那里反驳,我在所有的领域都给它创造出一种跟文革绘画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如果从根源上去找,实际上文革中间我已经在这么做了。所以08年在纽约展览的时候,《华尔街日报》的一个编辑,是一个能讲中国话的美国人,一位女士,她采访我,我就跟她很明确地讲:“那个时候实际上是有两种不同的文革艺术。”我那种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弱的声音。但是一个逆流,不是一个主流,主流是什么呢?就是今天王广义拿来演绎的那些工农兵木刻,这个东西是文革的主流,因为当时能画画的人都让他们下牛棚去了,不能画画的人,工农兵号召大家都来画,所以画的人都是非常粗糙的,都是没有经过任何严格训练的,他们构成了文革美术的一个基本面貌,主题是不用说了,完全是政治,我们也只能做这样的事情,起码在艺术方面,毫无艺术性可言,现在这个毫无艺术性可言,又可以把它重新分析了,因为它已经构成了那一段的面貌,你也可以说这也是一种艺术性,是不会画画的人画的画,它是另外一种审美趣味,但是在我当时看来,或者以一种比较专业的眼光来看,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种状态的。
我当时好在因为是业余的,我没有受过任何限制,而且我读过的几本书都是教你怎么向苏联学习,都是苏联的书,那个东西使得我既不能够在学校里边学画石膏像,也不能够画静物。我就一直在画素描写生,所以我的东西都是生活中来的,哪个东西跟生活不像,我一眼就能看出来,看出来以后就不去这么做,就是尽可能往生活化里面靠,这个结果就使得我的画既能够今天看,放在文革的画里面还站得住,因为很多文革的画没法看,我的画能看。
第二,也使得它被当时所不容,这是为什么改画组的人要把我的两三张画都改掉,觉得不够红光亮。
记者:当时的作品是具有文学性和诗意的?
沈嘉蔚:文学性和诗意的东西,在文革中间就提倡,从来没有反对过。我们根本没有这个意识,认为画画是没有文学性的,根本想都不用去想。这个问题提出来,是八十年代以后,是现代主义冲击。因为现代主义,尤其是格林伯格这一路的,是不主张文学性的,最后变成抽象主义。在那个时候,我要重新面对这个东西,因为很多人放弃了这个东西,而且变成了艺术方面的一个时髦的东西,也是更符合艺术规律的。我就开始想到我的艺术不是纯艺术,实际上是带有它的思想载体,我的思想的载体,从前是党的思想的载体,现在是我自己的。
澳洲的创作历程
记者:转变是这样的情况。
沈嘉蔚:这是八十年代转变的,同样也存在一个观众的问题,因为你的画,如果让观众互相交流,互相沟通,观众必须和你在某些方面有类似的文化准备。比如我说到毛泽东,如果中国人都知道毛泽东意味着什么,如果跟一个非洲人说毛泽东,他不知道毛泽东是谁,就没法说。那个时期我在八十年代中国画的时候,还没有出国。按照中国人作为我的观众来画,它的里面的含义,也只有中国人才能辨别出来。我到澳洲重新开始创作的时候,就很清楚地意识到,我的观众已经变了。观众改变后分两大类,有两大类:一类观众是普通观众,这个在中国也好,在澳洲也好,在西方也好,永远有普通观众,同时画家不得不面对批评家,就是圈里的观众。圈里面的观众,每个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爱好,不同的一代人,不同的侧重点,不同的解读绘画作品的方式都在变。我当时在澳洲是什么时候接触到这个东西的呢?我第一张作品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还是双重性的问题,要解决我的命运,因为我当时还在画头像,首先参加比赛,那个很容易,因为靠肖像还好一点,接下来我就画那张历史画,就是《澳洲的修女》那张作品。那张画,因为修女是十九世纪的一个人物,我觉得用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来画更自然,更贴近这个人的环境,就是说我是故意地模仿了维多利亚的风格来画一张澳洲的历史画,这张画歪打正着又被评画小组的组长,博物馆的馆长看上了,他非常喜欢。他是一个画家,所以这个馆长就说这张画应该得头等奖。其实它存在很多可能性。因为后来我无数次地发现,往往90%以上的评委会把奖给一个完全后现代主义风格的画。甚至只要看到你稍微写实一点儿的,他就会很讨厌。所以这是一个偶然。
不管怎么说,我得了这个奖,各个方面都变成新闻媒体的一个热门话题,不是圈内人的话题,而是媒体的一个话题。媒体必须报道,教皇是全世界的明星,他在澳洲三十八个钟头,每一分钟都要报道,所以接见我也都有照片登出来。同时,报纸的艺术版面的专栏作家批评的时候,都认为我这张画不怎么样,太维多利亚时代。后来我读了它们以后,产生一个很大的冲动,我得弄清楚,为什么评论家都是这样的态度。这个当然从直感可以感到。因为我看了很多展览,也知道在这个时候这种风格早就已经被认为是过时的。所以我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时代,我从中国登上飞机以后,这个飞机是穿过了一段时光隧道,从一个前现代主义的文化环境到了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环境,中间都没有过渡。那时候我们还在画《红星照耀中国》,到这儿来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
对西方现代艺术理论的研究
记者:几个小时的时间就变了。
沈嘉蔚:我就想一定要清楚他们的文化环境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有一年多的时间我读了大量的书籍,主要是弄清楚什么叫后现代主义,我先要返回去清楚什么叫现代主义,因为没有现代主义,哪儿来后现代主义?后来我弄清楚是什么呢?是格林伯格的那个窄义的“现代主义”,就是从康定斯基的热抽象和蒙德里安的冷抽象一路走过来,走到波洛克的抽象,一直走到美国整个五十年代的抽象,抽象到最后没有了,就剩白的画布,这是他们的现代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反过来的,就是后现代主义,就是波普艺术是现代,我不跟你玩这个东西,我玩实物。实际上现代主义起源是不止一股,最主要还有一个是超现实主义,还有一股是达达主义,实际上后现代主义就是达达主义。从杜尚的小便池开始就是后现代主义的源头。我注意到在西方的,我说的两种观众群里面,内行的观众群,因为从他们年轻的时候,绘画已经不被重视了,所以在他们上大学的时候已经谈论的都是观念,都是装置或者是新艺术,所以他们不懂绘画,他们有懂绘画的,但是不多,他们看不出绘画里面的好和坏。这个就好像你吃一种美味,无法用别的办法来形容,只能吃你才可能知道,或者听音乐,这个音乐真美,那你试试看用文字记下来,是不可能的,不能够用文字转述,你可以用相似的办法来描述大概是这样,但是永远不可能,那么绘画的这种妙处是无法传递的,所以批评家怎么办?批评家是用哲学的语言来讨论绘画,从现代主义开始,到后现代主义、到当代,艺术家的东西越来越自我,失去了跟观众直接沟通的一个渠道,那么观众怎么办呢?观众也想要弄清楚,为什么这个人那么厉害,还得奖了,名气那么大,他们就不得不依靠第三者,就是依靠解读的人,这个人他们认为是专家,这个人是谁?就是评论家。弄到最后,就变成了所谓的策展人、评论家这些人成了最权威的人,他们有解释权,因为艺术家做的东西,谁也看不懂,他们看懂了,告诉观众是如此这般,然后观众也相信了,就知道这个人,原来是这样。所以现在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了策展人或者评论家的天下,他们是主宰一切,艺术家对他们来讲是一堆沙子,艺术家如此之多,太多了。比如说这个人要做一个双年展,双年展的委员会决定由这个策展人来做,他就全世界旅行,就想一个主题,就在一万个艺术家里面,可能会递上来一百份申请报告,说我要做一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如何、如何,我的履历是什么?他看了以后说这个行,那个不行,最后比如说挑了五十个人,给他们一笔经费做作品。所以这样就是说,作品和观众之间就有一堵墙,这堵墙由艺术家和解读它的批评家来消除。我现在要想的一个策略是什么? 95年以后。我就很自觉的有一种策略,我表达观念但是保留绘画技巧,画里面有很多故事,这个故事本来是现代主义已经扔掉了,但是后现代主义又捡起来了,后现代主义都是观念,都是故事,背后都有共性,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是全部通过绘画来画出来的,然后我面对的观众,就一下越过了中间,不需要任何诠释,这样我一下子面对了两类的观众,他们同时可以在我的画前面站下来。他们就出现一个问题,不管是哪一类的观众,首先看到怎么画了很多人,画了九十几个第三世界的领袖人物。这个是阿拉法特,那个是切•格瓦拉,不知道的人会问你,这是谁啊?我说这个是甘地,甘地怎么、怎么样。他们都会看到,看到以后就开始有兴趣了,在里面找,然后就开始再往里看,再往里看的时候,就产生出不同层面的认识。
2001年的时候,是我对这一时期作品的一个检阅。展览规模很小,是一个地方政府资助不盈利的画廊。他们亚裔第二代的年轻人,画廊是从来不做写实绘画展览的,但是就给我做了一个展览。展了十件作品,其中还有几张是文革的画,非常成功。所有的英文报纸全部有正式的评论,评论的程度不一样。最厉害的那个评论家是澳洲最有名的,他的文化准备很大,所以他就能够首先引用说历史画十八世纪被认为是最高的艺术形式,现在没人画了,但是说我的历史画如何、如何有意思,第三世界是谁提出来了,一个法国作家写的,毛泽东怎么解释,这张画他是要说明什么东西,他就主动地写了好多。所以这里面介绍的完全是作品本身,所以从那儿以后,另外我也注意到,就是首先第一批观众是澳洲人,不是中国人,中国人对我哪个画特别有反应呢?就是《北京吉普》。悉尼所有的华人都来看,很多大陆来出差的那些干部都来看,都说好,只要是经过文革的人,全说好,还有一个女士是从来不认识,结果发现是我的中学校友,上一代,专门带着女儿来看,她的丈夫是文革中被杀的,被迫害的,长春科学院的科学家,她就非常激动,给看她们的全家福,当年的照片,都非常感动,我突然发现,这个景象是我很熟悉的,是什么时候发生过呢?就是在1980年前后,大概就是在1979年,1980年,就这么两三年,就是中共中央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批判文革,然后有一段时间老百姓突然知道文革的灾难结束了,每家都有苦水,因为牵扯得太广了,所以当时艺术作品只要是能够写到文革的,能够说真话的,那个时候还敢讲真话,也敢做。我的朋友画了一个《枫》,在《连环画报》登出来以后,观众读者的反馈一麻袋、一麻袋的信,激动到这种程度,就因为讲了一点儿真话,就是红卫兵怎么样,然后对这样的人怎么斗,然后就跳楼自杀了,非常激动。当时89舞台上演文革的话剧,下面哭笑都有,因为有共鸣,后来就没有了,我以为是因为时间过了。但是那张次展览展出以后反应同样热烈,我就知道老百姓还是喜欢看讲真话的作品。
记者:这个情节仍然没有结束。
沈嘉蔚:还是有,因为我们艺术远离群众以后,他们也都不关心了。我有一些画故意用了一些基督教的符号,戈尔巴乔夫后边用的是《最后审判》,人家一看就知道。《基督降生》是达•芬奇的原画,基督生下来,有三个智者知道有一个王降生了,在文艺复兴的时候,这个智者就变成了波斯的富商,有钱的商人,明显地曲解了《圣经》的原文,《圣经》的原文在英文版里是说当耶稣生下来的时候,智慧的人从东方来,所以这个正好可以用来做文章,我用达•芬奇那张,从前翻译成“三王来拜”或者“三博士来拜”,我就另外找了一张明朝的明画,同时代的,那张叫《三教图轴》,是三个人坐在树下面论道,一个是佛陀,一个老子,一个孔子,我就说把这三个人插到里面去,插到达•芬奇的画里面去,这三个人一看是东方来的,基督生下来的时候,这三个人都是五百岁,应该有资格评判,已经存在了,这张画所有的西方人都能看得懂,知道我讨论的是关于东、西文化的问题。
从个体生命的体验转向普世价值的探索
记者:您的作品从个人对历史和生活经验的表述,转向了对人类文化现象的普世探讨?
沈嘉蔚:我有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在八十年代开始就逐渐都建立起来了,就是所谓今天我们说的普世价值观,对于人类共同命运的一种关切,对于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包容、宽容、理解等等,这个东西基本上逐步地建立起来了。
记者:您仍然坚守写实主义的原因是什么?
沈嘉蔚:写实主义是一种武器,是一种工具,不要说得那么火爆,就是工具,工具就是用一种语言,任何人要说话,我们画家通过我们的画来说话。这个画说出来的东西,如果有人愿意听,就起一点作用,但是不可能起大作用,因为一个人的作用是很小的,但是我也不愿意参加某一个组织,我不希望任何人来代表我,我就是我自己,我自己读书、思考,想到什么东西,心得在我的作品里面反映出来,这是最重要的。
记者:下一张《巴别塔》是这种思想的一个集中的体现?
沈嘉蔚:可以这样说,就是说认为这是一种很聪明的办法,就是一个人活了一辈子,我现在活到六十二岁,我这六十二岁里面起码大半生不是我自己可以决定我自己的命运,基本上在毛泽东时代是没有任何选择自由的,当知青什么都是,而且迫使我们不能上大学,后来又当兵,一直到出国的时候也是碰巧。最后我发现每一段历史,每一个经历,都是很宝贵的一个人生经历,因为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他不顺的时候,都有不得不跟着这个时代走的,不可能反抗一个时代。那么你的这段经历,如果说对普通人来讲,我觉得可能是一个不幸,如果说一个普通人糊里糊涂到农村,被迫当了几年知青,回城了,青春时代已经过去了,大学也没有上成,最后当了一个什么工厂的工人,糊里糊涂当了几年以后下岗了,工厂就倒闭了,原来还以为铁饭碗,现在铁饭碗也没有了,一辈子就是这么走来的,这些人是很悲惨的,我非常幸运的是我是一个画家,如果我是一个作家也是,因为我们是以我们的生活体验来作为我们的素材,所以所有的经验,只要能找到一种方式,是画也好,是写也好,就变成了一个很宝贵的素材库,就再也不是一种浪费,同其他人不一样,就是你利用得越好,就活得越有价值,这个也是推动我为什么要走现在这一步的原因,我觉得我现在要画这张画是我人生的一个总结,所有想法的总结,全部都在总结,我也很清晰地自我意识到,这是任何人都做不了,只有我能做,这是一个艺术家最自信的地方,当他找到一个东西,包括找表达手法、内容全部是个人的,甚至我小时候在课堂上听课,在桌子上乱画,画红军、士兵的帽子,钢盔等等,从小的那种东西,兴趣点都可以在里面,一切都在,因为兴趣所以有积累,有积累以后,现在全部都暴露出来,都在创作里面,你说这个是使命也好,就是感觉到那个对了,找到了那种东西,我就做了。
肖像与历史画创作的关系
记者:在创作语言上,您已经找到了自己最合适的方法来表达思想?
沈嘉蔚:对,具体我是通过肖像的结合,因为肖像本身是我的一个长处,我能够抓住所有不同人的样子,在画头像的时候练了很多,我的肖像本身是一个真实人物,所以人物的肖像结合到一起的时候,当他用超时空的办法去处理的时候,他们互相之间只要放到一起就会起作用,因为如果按正规的,日常见到的关系放到一起的时候,人家不会想什么。比如我的画里面我把列宁后面画上陈独秀,这两个人根本没有见过面,这个时候情况就变了,人家就会想很多东西,为什么放在一起,他们有什么关系。更加大的反差,比如说我把耶稣放在桌子上,旁边是一圈官员,这个时候就迫使人去想为什么,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语言,形成了语言,这个语言本身是思想。
记者:跟您在澳洲大量的作品都是跟肖像有关?
沈嘉蔚:我的历史画一直跟肖像有关,我在中国也是这样的《红星照耀中国》也是肖像。
记者:在澳洲画的那些作品和在国内画的作品,在技巧上和语言上还是有变化的?
沈嘉蔚:有变化,我的肖像技巧在国外才发展起来,国内的时候我画得比较粗糙,在国外就画得越来越深入,因为我画写生很多,后来总结出很多经验的东西,而且在另一方面,我也成了澳洲很有名的一个肖像画家。
记者:这也是为您现在这些作品做了很多铺垫。
沈嘉蔚:对,它是一种关系,比如我画的人物都是澳洲嫁给丹麦王子的那个王妃,就是给国家肖像馆画的,比如说澳洲卸任总理,我给他画,放在他们的国会大厦里面的历任总理,前面也画过国会议长,国家肖像馆有三张,一共五张画都在潘培拉,这些画本身画的是当代人,当然它们将要构成澳洲历史回顾,因为这个感想以前没有。但是我到伦敦和丹麦看了他们的国立肖像艺术馆。他们的历史长,从中世纪看到现在,你才意识到我画的肖像也是历史的一个链条,过一百年,人家也是看这个肖像。所以这个也是历史画,另外一种历史画。
新的创作方向的线索
记者:您的作品有几条线,一个是国内的,还有国内也分文革期间和文革之后的,有到澳洲画的,澳洲分肖像和历史画,再进入到之后,您现在正在创作的这个阶段?
沈嘉蔚:我在澳洲历史画很快完全把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融汇在一起。
记者:应该是一个最大的变化?
沈嘉蔚:很大的变化,就是我更加意识到自己作为世界公民的身份。我们这一代从小受的是国际主义教育,工人无祖国的,当然从文化大革命以后,毛泽东民族主义强调得越来越厉害,但是共产党的这种国际主义在我心里是很强烈的,这很容易到外面以后就从共产党的模式里面跳出来以后,也很自然地能够接受世界、全球的观念,我总说这不是一个民族主义的范畴。
记者:这就是出国之后,对这种思想就更明确了?
沈嘉蔚:对,更明确了。因为澳洲恰好是一个很包容、很宽容的一个国家,这个问题从来不需要讨论,我自己回过头来总结一下,我觉得是一直面向整个世界的。
记者:您在创作上有没有想过用其它的语言或者是形式?比如媒体、其它的媒介去创作?
沈嘉蔚:没有,不是我的长处,我只是在九十年代有一段时间写过很多随笔,但是我还没有找到路子在画上表达,而且那个时候更多地为解决生存问题,所以很多时间要画肖像,那个时候我有什么想法都会写随笔,也是一种发泄的方式,随笔写到后来,到2000年,我写了十篇关于国际共运的随笔,突然发现真的可以通过什么东西表达出来,过了一年就有了《巴别塔》的构思,等我有了这个构思就不写了。
记者:《巴别塔》还是通过文字整理之后才开始逐渐完整的?
沈嘉蔚:开始是考虑,但完全跟巴别塔没有关系,是关于国际工运的一些思考,我读了一些书,都是国门出版的书,但是大量翻译的书,有很多的书非常好。
记者:您之后是在国内创作还是在澳洲创作?下面的展览情况呢?
沈嘉蔚:一直在澳州,国内偶尔会回来。我不会有个展,因为个展对我来讲规模太大,我没有那么多画,这件《巴别塔》之后会有展览,然后再编一个书,另外我现在也在画一个《红星照耀中国》的变体,如果能画完,可能明年有一个展览拿过来展。
【编辑:张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