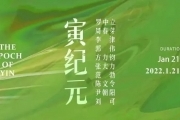为什么左小祖咒老戴着顶礼帽?因为他的头皮被打掉了一块儿。
那是1993年夏天,左小祖咒跟人喝了几瓶二锅头,他的朋友想在小摊上想顺包烟,可左小祖咒被烟摊摊主给了一闷棍。这段往事是认识他快20年的老朋友艾丹讲的。难道就因为这个戴礼帽啊?“当然,头皮都掉了,他恨不能戴钢盔!”那时候他贫穷、绝望、也挺不管不顾,一到艾丹家就站在他们家煤堆上撒尿,把艾丹的妈妈气得够戗。
很多年都没有提过这一段了。左小祖咒把帽子摘了,低下头,用手摸索寻找那个位置,现在那头黑发非常茂密,还蛮柔顺,已经没有任何异常。这件事给了他两个教训:打头没出血比打出血要厉害得多;再也不喝二锅头了,一见到那红标小玻璃瓶都害怕。
这顶礼帽,区分了文艺青年左小祖咒与“忧伤的老板”左小祖咒。
他被冠以摇滚师、诗人、当代艺术家称号,总的来说,他将自己概括为“忧伤的老板”。他的音乐仍在表达无助、麻木与痛楚,却用名牌服装和缤纷包装勾兑出售,都上流行音乐排行榜了,也不介意与周杰伦或曾轶可相提并论;他写下忧伤敏锐的词句,但是绝对恨死文雅高贵,因为那意味着退却;他因为“当代艺术家”的身份获得利益,与资本眉来眼去,可连他自己他都骂,骂当代艺术是场骗局,当代艺术家为包工头;他敏感而内省,又世故且周到……
想当然地将他归为“中产阶级”,他还不同意:“中产阶级是墙头草,太没有原则!”。身为偶像,他扮演了暴烈、有着强烈倾向的无产者;他又向往并开始体会有产阶层的生活,做老板,像“皮尔·卡丹”那样把“左小·祖咒”搞上市。
他身上充溢着双重性,是领会这个时代复杂感受的皎皎者,他就是个弄潮儿啊。
“与其说非常贫穷和非常美丽是艺术成就,不如说它们是道德缺陷”,雷蒙德·钱德勒对消费时代艺术家的判断在左小祖咒身上实现了。他可以接纳假神,又让他们顺从他的意愿;他可以遵循定律,却迫使它们造出少有人想到的东西。他出身卑微,也曾游走街头,他要混出个摸样,因为他不愿死在墙角旮旯里。他与更多久经世故的家伙有所区别——他的才华,他的诚实,他的生命力,他始终在追逐的尊严。目前来看,成功并没有挫败他。
尊敬
左小祖咒浑身酒气,沉浸在前一天的宿醉中。那是从江阴到无锡机场的一辆小车后座,左小祖咒坐在我左边,黑大春坐在我右边。黑大春已经相当老了。这位50岁的“圆明园派”诗人有一股落寞的神气,他感慨自己有如时间的移民,“祖国的陌生人”,不过他气色不错,谈兴上佳,无一句不有出处,引用了荷尔德林、兰波、老子……。他忽然背诵起美国女诗人格吕克的一句诗:“一整天我尝试把欲望/和需要分开……”“把欲望和需要分开!”他又重复了一次,之后望向窗外,给出留白以供回味。就在那段留白即将结束的当口,左小祖咒开口了:“对,从女人身上爬下来之后,才会想起找杯水喝。”
他们刚参加完“江阴三月三诗歌节”。那是场被强行拼贴在一起的杂烩。如果单看雄壮的“江阴大剧院”,前排就座的市领导,备好了瓜子准备观看一场联欢晚会的市民,还有那位语调铿锵的女主持人(她最喜欢串词是:感谢这位诗人,让我们领悟了很多人生哲理!),会感到这将是场胜利的大会、和谐的大会。可台上嘉宾除了上述两位,还包括诗人杨小滨、周云蓬、吴吞、小河和李铁桥等,他们并不擅长撒娇或歌颂,他们更愿意挑衅或激怒。他们站在炽烈灯光下吟诵“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简直太不和谐了。
古典范儿的文人感慨我们总是做着“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信念,要么功利。要么灵,要么肉。要么科学的春天,要么权钱的炎夏。要么纯真而无知,要么成熟而世故。”天可怜见,它们被强行牵扯在一起时更加荒诞。
左小祖咒隐而不发。他站在后排发短信,调音师是跟随他多年的乐手,他提醒,声儿太小了。可前排领导嫌摇滚乐声音太大,命其调小。有那么一段时间,音量起伏不定。后来,他发出一声大吼,把个一家三口吓了一跳,中间的胖小子都快哭了。以为他要搞一把,胡闹一把,把场子给砸了,可他又不动声色起来。他代替诗人食指,从市委宣传部的领导手里领取了年度诗人的证书。他又用歪歪扭扭的语调朗诵了歌词《尊敬》:
掌权者不哭泣怎么赢得人民
掌权者不哭泣怎么赢得人民
当嘲笑你的人开始为你念诗
“一个人要抬多少次头才看到蓝天?”
你即刻学会说套用的蹩脚诗:
一个人要哭多少次才能感到不委屈……
“要有角色扮演精神”,在他还是穷小子时就这样说,周围的弟兄嘲笑他,饭都吃不饱呢,还角色扮演。他不仅一直在扮演,还相当努力——这一次,他扮演的是语言锋利而行为柔软的诗人。当然他也扮演过“当代艺术家”,在艺术展开幕酒会上,用力与艺术推手、拍卖行经纪人、艺术记者干杯,给他们结实的拥抱,握着他们的手送到门口,还鞠了躬。他最经常扮演“摇滚师”,在舞台上,背景霞光万道,他伫立中央,后身甩出一行大字“世界银行行长”,你要华丽就给你华丽,你要癫狂就给你癫狂,音乐勾兑出售。当他办了家宴扮演“男主人”时,会惆怅地对来客说:“我还是混得不够好啊!我要能当上总统,就用大奔一个一个接送你们。”
角色扮演的左小祖咒极为认真,特别诚挚,为了区区小事就竭尽全力的劲头非常感人;他又是紧绷而警惕的,不能容许任何一个角落被忽略而有失了周到。“我非常明白别人的需要,我具有服务意识,我要让你们满意。”
“你知道吗?我从20多岁起,就特别需要人的尊敬。”在角色扮演的另一端,他要的是尊敬。那种尊敬是与兄弟们喝多了酒撒酒疯把饭馆砸了能有钱赔上,而不是衣衫不整胸前沾满了灰被抓到警局里去。角色扮演与追求尊敬,就像弹簧的两端,左小祖咒在中间游刃有余,既不过分谦卑,也不妄自尊大。
“聪明的人像左小祖咒这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跟贵族也能打交道,跟农民也能玩到一起,只要他愿意都可以。这种人是聪明的,有些人不智慧,不聪明,他只是在一个状态中才能游刃有余。往往这种人不丰满,像块木头板子一样。”艾丹评价说。
夜晚的江阴春风沉醉,诗人和摇滚乐手统统喝大。左小祖咒又尽职尽责扮演起“衣锦还乡者”的角色。本地诗人频频敬酒,他与他们表演着他乡遇故知的戏码,肯定是不喝二锅头了,就把葡萄酒像二锅头那样一饮而尽。忽然有一位诗人开始哼唱《乌兰巴托的夜》,附和的人越来越多,演变为集体大合唱。
2005年,左小祖咒在北京君王府大办婚宴,参加的人都叹:太俗气了!新娘子穿红戴绿,他也穿起了长袍马褂。为了让老丈人老丈母娘高兴,那一天,他唱了《乌兰巴托的夜》。他所追求的尊敬,也以另外的方式实现——喝大以前,他将一沓钱交给一个小兄弟,叮嘱说,如果有人撒酒疯把场子砸了,就拿这些钱赔上。
这一次,《乌兰巴托的夜》是如此婉转和深情,诗人们好象要借此拨开挡在他们面前的重重迷雾,激奋地、高昂地唱这首歌,既宣泄着压抑之情,又对左小祖咒施以赞美。他满足吗?可在那身甜腻的荧光蓝绒面西服映衬下,他羞怯得脸色通红,也不失侠气,有那么一阵子,好像还有一丝儿狗尾巴草随风飘荡的神色。他迅速把自己喝大,忘记了角色扮演这回事,连减肥都忘了,手抓着鱼和肉往嘴里塞,再用油手揽住妻子小莉的肩膀,亲她,哼唱着:“小莉啊谢谢你借给我钱花……”
忽悠,忽悠
2001年-2003年,左小祖咒从北京消失了。
30出头的左小祖咒住在青岛,每天大致过着这样的生活:从家里出来,在附近的花市溜溜达达,海风轻拂,远处也看得到教堂,人们脸上洋溢着安详与宁静,竟然从来没有人打架。他感到满意,远离了北京的焦躁与市侩——那里传言已经出过两张唱片他的发财了,都开大奔了,每天嚷着喝大酒、吹牛逼、他要不请客还不高兴。那正是所谓“中国地下摇滚泡沫破灭”的转折期,到处充斥着“不正之风”,不讲技术,谈感觉,这让左小祖咒很生气——要说感觉,兄弟,我也有感觉啊。某个青岛最平常的一天,忽然有一个声音对他说:“创作从来没有让你难受,可是钱,总是让你难受啊!”这让他又惊慌又兴奋,假期结束了。
2005年发行的专辑《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大部分在青岛创作,定价150元一张,把制作人方无行吓着了。左小祖咒算一笔帐,如果要收支平衡,必须定这个价。搞地下摇滚的都知道,坚持是一回事,每发一张片不亏钱又是更要命的另一回事。这里也有他的“深思熟虑”:“我的歌迷都是仍保有浪漫情怀的成年人,他们有更复杂的理解力、感受力和消费力。”这些唱片要直达他们手中,“瞬间抵达指定位置”。2005年正逢全世界将中国奉为“金砖国”,觊觎着这片暴富国土的奢侈品市场,全球唱片业也受网络冲击陷入僵局,150元的唱片正巧成了首屈一指的奢侈品。媒体被刺激得纷纷尖叫,大力跟进,左小祖咒以“媒体红人”的面目重回摇滚界。
“2000年以前,我跟媒体是不配合的。他们不喜欢我,乱写。我也不喜欢媒体,差一点打过记者。”现在接受采访也是顶重要的工作,他不厌烦地解释着某一句歌词里透露出的蛛丝马迹,重温着过去困顿的时光,有时候,或者根本就是随口说一个答案,逗你玩。
“听艾未未说有一天你上了山,碰上个老道,掐指一算你这个人不寻常,跟了你一颗仙丹?”
“我跟艾未未是一伙的,我们准备卖药。”
这种灵光一闪的胡说八道特别讨媒体喜欢,感到他有如安迪·沃霍尔附体,果然有个艺术家的样子,立刻心满意足。
他不再摆死硬的架势,对歌迷温柔可亲,在再版《庙会之旅》前言写了一封公开信,神情款款地说:“再见,小伙子们。”他还开始利用网络,把自己搞成一个“小型媒体”,在豆瓣小组会换上马甲与网友恶搞,也开了微博,更新得挺频繁呢。
之后发行了唱片《美国》定价150元,唱片《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定价500元,唱片《大事》定价150元。他有一套生意经:“我不是卖西红柿的,1块嫌贵8毛,绝对不降价,我明年会变成2块,你可以买别人的西红柿。我会给你机会对我好,我也会给你机会讨厌我,但是你要抓住机会。”
2010年3月的个人演唱会“万事如意”的幕后制作包括:艾未未、宁浩、孟京辉、贾樟柯、朱文、李延亮、方无行……台上嘉宾有陈珊妮与曾轶可,台下坐着韩寒。这简直是让人消化不良的人脉大爆发,每一个名字的熠熠星光都给“万事如意”演唱会增添了一层迷雾——到底是怎么搞大的?“我就是做了个局,大家来一起玩吧。”本来已经放弃获得什么答案,左小祖咒的实诚劲儿又冒出来:“你们来,都能干什么呢?朱文担任‘形体训练和指导’,他指导我什么?督促我减肥,叮嘱我前一天早睡觉,睡足了精神好。演唱会前一天再吃顿饭,给我打一针鸡血。这就是幕后制作。忽悠呗。”
“万事如意”共发售门票1713张,给剧院留下75张票,给朋友留300张,其余的由妻子小莉负责网上售卖,老家来的外甥负责处理剩余的实体票。在开场前夕,粗壮的外甥还遭遇了黄牛围攻,票被抢了个精光。左小祖咒熟悉演唱会的每一个琐细的环节,他把数字背得烂熟。他事事亲躬,是果真喜爱这些杂务这门“生意”吗?“就像庄稼人一样,我是种田的,不是卖种子的,在播种收获的时候不应该想太多。可是如果这种子在很多人不大喜欢的情况下,我也要考虑一条龙服务,把它生产出来,送到客户手里让他吃。”
现在左小祖咒的经济状况有多好?至少他住上了大房子。位于北京郊区的工作室占地96亩,院子中间有湖,湖边养着4只孔雀,1匹马,1头驴,屋内保持原房主的装修——俗丽壁纸、能把脚给崴了的厚地毯与黑皮大沙发,把如同桑拿房的屋顶红色小暗灯打开,屋内仿佛立刻回荡起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秘史。它曾经属于一个老干部,后转手给一个艺术基金会,免费供包括左小祖咒在内的三位艺术家在此地创作。
如果作浪漫化想象,这风景大概就像《竹林》所唱——“天空放晴了,恩!真不坏。很多好听的鸟,人极少,园子巨大……”。可是对不起,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哪会那么容易让你从他的作品中发现真实生活的痕迹。“别人坐在这里,可能就是暴发户,我坐在这里,又成了艺术区。这个房子就像我的作品一样,有一种复杂性。”
复杂性,还真是当代艺术的要义,那里填充着辩解和包袱,以达到“怎么说都通”的境界。以他的代表作摄影《为无名山增高一米》为例,10人裸体摞在一起,而画面中只见5个人,老有人问,左小,你是哪一个?他就乐:“大师在后面。就像我的唱片《走失的主人》的英文翻译:The missing master。”可是这复杂性背后还有一层浅白的逻辑——钱。左小祖咒太无情了,他戳破了这一点:“另一幅照片《我也爱当代艺术》,10头猪摞在一起,再聪明的人也只能看见5头。等我把照片卖光,没钱了,我再卖另外5头猪,我卖雕塑。他们不知道,我的雕塑早就做好了。我再创立内衣品牌‘左小·猪猪’,打开一看,印着10头猪,我把这个品牌搞大,搞臭……。我也爱当代艺术,其实它是一句讽刺啊。”
一楼墙上悬着一副从未展出的摄影作品《小驴面壁》:一头瘦驴面朝琉瓦红墙,雪地上孤零零一串脚印。你若凝神静气,打算细细体味其中奥义,左小祖咒就开始讲那创作过程:“我先跟一个有驴的农民讲好,下雪天把驴借给我,租一天500块,如果还不回来赔5000块。我找一搬家公司把驴运到天安门长安街,然后假装游客,哎,一头驴一头驴,拍下‘小驴面壁’。如果有警察来,坚决不承认,坚决不要驴,反正已经讲好了,赔5000块……。”他就是这样忽悠了当代艺术。
有一天,他在另一艺术家串门,保姆说来个人要看看你的作品,他把钥匙一扔看去吧。回身想起去瞧瞧来客,发现是另一位退休老干部微服私访。他曾经叱咤政坛,又黯然落马,如今耄耋之年,腰板笔直,耳朵特大。搞不清楚他为了什么来到此地,他看了看左小祖咒的作品,评价说:“你是个浪漫主义艺术家。”
“评价得多准确啊!他们老说我先锋,其实我古典;我除了浪漫,我还有什么?”坐在大玻璃床前,望着一棵刚刚吐了芽的挂满了口罩的桃树,左小祖咒猛然忧伤起来。一边的小莉正在面试保姆,吩咐说,这是左先生,又把一袋胡萝卜撂在地上,最近那头驴瘦了,还掉毛,都不能参加艺术展了。这对摇滚夫妇走过困顿,也经历过波折,她如此美丽,曾经也是一代“果儿”,如今她坚韧、干练,是位称职的家庭主妇。大概只有她见识过左小祖咒的脆弱,那脆弱藏得很深,转瞬即逝,她说不出,但感觉的到。
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
艺术家聚集区“北京东村”,如今已经变成了地沟油提炼基地。
紧邻东四环朝阳公园桥,远处不足200米的楼盘单价超过了5万元/平米,小村鳞次栉比的平房好象未来的墓地,活人们在惨淡的太阳下无所事事地走来走去,灯心草脏乎乎的呈褐色,臭水沟上漂浮着刺鼻的地沟油渣。左小祖咒在村中央的小贩那儿买了包茶豆腐,后来他还买了根甘蔗,站在臭水沟边嚼。他可真爱吃甘蔗啊。
“北京东村”由左小祖咒、张洹、马六明等艺术家缔造,取名“东村”,与纽约的艺术家聚集区“东村”相对应。1993年-1995年,左小祖咒在这一片换了3个住处,最终落户“四路居73号”。不足10平米的小屋,是间隔出来的独立偏房,附带3平米的天井,小归小,独立且舒适,相当于北京最早的小户型。“就是在最苦的时候,我也能让自己在小范围内稍微好一点。”左小祖咒在“四路居73号”紧闭的小木门门口张望,远远走过来以前的房东老丁,他喝多了酒,脸膛通红,摇摇晃晃,打着招呼:“小左!找朋友了吗?”好像这是曾居于此地的左小祖咒最大的难题以至于让他惦记了10多年。左小祖咒回答:“娃儿都3岁了。”
“他的确像蜥蜴类的动物,恐龙都灭绝了,它还能钻到洞里生存下来,”艾丹时常到东村来:“那个臭水沟,一两只死猪四仰着,苍蝇在上面飞。当时这么一个条件,他找了一个女朋友好难看,跟他好多年,当然人非常好,可是后来把他抛弃了,他也那样子也跟人家过日子。现在找了个大美女,也跟人家发脾气,也挺本真的。”
1993年一份《北京自由艺术家生活实录》,记录了当时23岁的左小祖咒:“披肩发,脸上架着墨镜,手指上戴着骷髅大戒指,黑皮夹克,黑牛仔裤,黑大头靴。画家们说他整天都戴墨镜,谁也不知道他的眼睛长什么样。”他老爱提“暴躁”这个词,强调自己搞的是“非主流文化”:“我在演唱时故意出现不和谐的刺激的声音,就是要让人不舒服,不然就不是摇滚乐!我决不把我的音乐降低到他们能听得懂的地步,他们能不能接受我无所谓。”
左小祖咒的自我总结是:“那时候,我不仅物质上没有得到满足,连肉体都没有得到满足。”
1970年,左小祖咒出生于江苏建湖县,本名吴红巾,父亲是船工,母亲是农民,两个弟弟至今还在做小买卖。他15岁离家到南京当兵,20岁到了上海,之后辗转来到北京。他把这段时光快速带过,因为“20岁之前,我如同一张白纸。”他把自己叫做“假海龟”,初中也没有念完,鲁迅都没有读过,现在提起隐隐带着庆幸,没有被教育给毁了:“要说这点,我可能跟艾未未有点像,他起点比我高,可以滚到纽约;我一个县城的,我只有滚到北京。”
1993年,钱大成已经有“中国打口带教父”的美誉,他从汕头或厦门的港口上花4000块钱买一吨美国来的塑料垃圾,雇几个大学生分拣出来,放到北京五道口的“先锋音像”售卖。唐朝在那里拿了好些货,窦唯也常在那里流连,朴树没有钱,就整天坐在店里听。“先锋音像”日流水3000多元,钱大成在1992年已经身价数十万元。多年以后,时代浪潮滚滚向前,把他冲刷得有点晕,他信了佛,什么都不爱听了,就喜欢听个左小祖咒。当他慕名前往要请摇滚师吃饭时,左小祖咒惊到了:“你就是传说中的老钱啊!”
在上海短居的左小祖咒靠卖打口带维生,他的最大上线就是钱大成。犹如贩卖毒品,他在街头流窜,被抓过,被罚过,所谓“喋血街头”也时时发生。钱大成心里狐疑,左小祖咒是怎样的人物,可以写出那么锐利的歌词与高水准的音乐?也许有听打口带耳朵听得比较尖的因素,可他没上过什么学,说起话来也前言不搭后语,这位佛教徒喃喃自语:“左小祖咒,一定是前世积攒下来的天分。”
他的天分也许还可以从长篇小说《狂犬吠墓》中窥见。“爷爷是吃人民币自杀的。”他这样开头,有如马尔克斯遗忘在北京的徒孙。这部小说写于1997年,2000年左小祖咒自费出版,河北找了个馒头坊,炭火是黑的,馒头是白的,一不小心给印成了菱形的小说也是白的,一开始馒头坊还不想给装订,左小祖咒说:“不行啊,不订不是书,是传单。”总计印刷1420本,成本8000块。现在此书已经遍寻不见,据说已经炒到了千余元一本。
小说写到后来,他还掉了掉书袋:“我相信弗洛伊德的诡说,自杀有遗传基因。那么自杀的方法有没有基因遗传呢?后者他没论,他的学生荣格有没有论我不晓得,他的书我没读,太深。海明威爱用牙齿咬枪,那么柯特·科本一定是他后裔了,这能不能算是后弗氏精神病学的一种假设呢?这么说,反正是挨枪子的,不管是胸前、胸后、腿前、腿后都是海明威家的亲戚,也不管挨着后是死是活都是柯特·科本的舅舅。”这诡异的灵感从哪里来?文艺气从哪里来?
一提灵感,一提文艺,左小祖咒就急。“灵感是托词,文艺是小孩的玩意儿。我没有灵感,我是职业写手。我坐在这里,音乐自然就出来了,我可以看到旋律和色彩;把10万块钱拍到桌子上,我立刻可以写一首歌。”新专辑《大事》9首歌,有6首一天写成。
“我的所得,都是由我的行政造成的。行政,就是行为的方式。我囤积粮草,我招兵买马,我更换武器。我的行政在变,可是我的内容从来没有变。”他20年前就长成这样儿;他从《苦鬼》就开始写有关钱的困惑一直写到《钱歌》;他一年一张专辑,可是,它们都是以往的创作,还有更多的存货;他说自己创作力正盛,好象装载了太多想法而停不下来的火车……“人不可能变成神。但如果把人做好了,自然就成了神。因为后人需要神,后人会把你塑造成神。”
经不起成功考验的艺术家,几乎跟经不起失败考验的艺术家一样多。左小祖咒有他的神——他理解的兰波,忽然不再写诗跑去卖军火,那是因为,若不能成为诗歌的国王那就做财富的暴君;他喜欢达利,他一生最爱做的事情是数钱。
老板左小祖咒谈起艺术来那么的忧伤,摇滚师左小祖咒唱起歌来又老在谈钱。他像泄露一个秘密似的说:“‘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既无关爱情也无关友谊,这句歌词的意思是,我不能让人感觉照顾不周,我不好意思冷场,我要搞搞气氛。我既不要做一个练舍利子的,也不像父辈那样生儿育女过一生,我要做个魔术师,当我变不出花样了我就自己出丑,因为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
【编辑:sin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