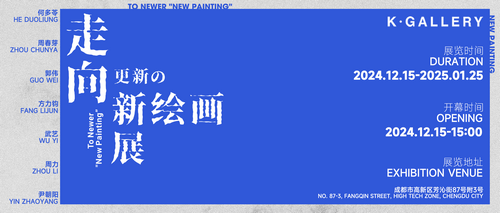匆匆瞥见那不可言说的神秘超验之物……
——关于“信仰”及2006年新加坡双年展
菲律宾裔新加坡年轻艺术家Brian Gothong Tan作品《我们生活在一个危险的世界》
文/郭建文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及社会学系主任、2006年新加坡双年展指导委员会联合主席
译/戴伟平
“信仰”,这个朴素却具有挑衅意味的词即是首届新加坡双年展的主题。艺术总监南条史生(Fumio Nanjo)及其策展团队邀请艺术家以这个词为跳板,奉献一届极其难忘的双年展,用南条先生的话来说,它应该是“一次伟大的,或许尚且稚嫩的实验……通过艺术去探究人们生存方式的基石”。南条先生在双年展概要指南中这样阐述展览主题语境:
当代社会表现为价值观的既复杂而且相互冲突,同时匮乏统一的判断标准,不同的价值观时常导致战争和恐怖主义的威胁,它们各自所暗示的世界图景也包含根本上的差别……我们应该信仰什么?我们应该在什么价值标准下生存?生,即意味着时时刻刻在许多选项中作出决定。在此情形下,人们可以依据什么基本原则来选择和塑造生存方式?
无可否认,文化差异本身并不导致暴力。一般情况下,暴力总是牵扯到一连串相关因素,其中包括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与弱势群体的疏离和异化。然而,南条先生所提出的问题强调了“价值多元论”,此即二十世纪的世界主要特征,在这个世纪里全球发生了形式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暴力。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醒他的学生们留意托尔斯泰的观点——对于“我们应该做什么以及如何生存”这个重要问题,科学并不提供答案;韦伯进一步将这个设问如是戏剧化:“我们应该信奉战场上的哪位神?”在古代谚语中,现代社会的价值多元论被以一种矛盾的方式描绘成多神论——上古诸神“试图获得驾驭人类生活的权力,以重新开始他们之间的永恒争斗”。
二十一世纪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如果说一战翻开了上个世纪的扉页,9·11——2001年9月11日——则象征着一个新的暴力世纪的开端。强势的民族国家继续使用高科技军事硬件发动战争,势单力薄的个人则通过策划和实施暴力行动炸毁他们自己及他人的身体,借助全球媒体向全世界散播影响。关于9·11事件的前因后果,在此不作分析,但可以肯定的是,该事件的重要意义和内涵拒绝任何将之简化成“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之间摩尼教义式的“文明冲突”——因为这类整一范畴所指涉的是永恒地相互冲突对立的同质性集体人群。这种充满怨恨的“我们VS他们”的话语将文化与身份二者假定为完全重合——完成这种假定的途径经常是通过强调文化的官方表现形式——从而忽视了爱德华·萨义德所说的“每种文化内部的不安定感”。而且,通过模式化和妖魔化他者,这类话语不仅在那些持不同信仰的人们中间激化了对彼此的不宽容,而且还继续强化了给予暴力行为合法性的信仰。
在我看来,9·11作为二十一世纪开端的一个象征性事件,引领我们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新时代中对信仰这个问题进行追问。简言之,鉴于科学理性主义和世俗现代性在二十世纪已取得全面胜利,因此也许这个问题已不必从“无信仰”这个角度去考虑。与尼采“上帝已死”这句话恰恰相反的事实是,我们远非生活在一个无神的宇宙,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句——“上帝若不存在,任何事都是合法的”——的理解语境则需要超越韦伯的多神论:不仅古老众神争斗依旧,在宗教运动、宗派群体以及更松散的由个体组成的信徒网络蓬勃兴起的现象背后,新的神也随之激增。诸多新的神——包括世俗权威——规定和指定什么可为或不可为,其中包含使用暴力手段实现宗教或道德目标。善妒的众神为俘获信徒的虔诚而互相激烈争斗,信徒则须证明他们对神的信仰纯洁,如此一来不同宗教群体怎么可能共存相安?且不说达到相互理解这一更高目标,避免冲突的最低基准是什么?
南非艺术家Jane Alexander作品《真相、信念与公正》
当代情境远远超出了韦伯关于泰坦诸神交战的隐喻。一度,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似乎标志着二十世纪浩大的意识形态之争已结束,它最后以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自由主义民主对极权主义的胜利而告终。然而,9·11事件所揭示的却不是一个两极世界走向由超级大国霸权支撑的全球新秩序,特别是美国,它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巨大,同时拥有塑造全球消费文化的意识形态以及文化方面的“软”实力。尽管全球化催生了想象的文化均质化,9·11事件则例证了信仰体系普遍呈碎片化的趋势,变成在我们看来似乎永无止境的信仰过量现象,这些信仰彼此不可通约,互相无法妥协。顾名思义,信仰的体系应是连贯一致的,并带有一种权威性的灵韵。一切都破碎了,所有的连贯一致性都消失了,信徒又该向谁或哪里求助呢?矛盾的是,在这个不确定的新时代,一种庸常的反应却是继续在信徒与无信仰者之间,在真实信念与其它一切之间,再次强调一种互不妥协的两极对立。
因此,信仰这一展览主题提出了很多议题,并对艺术打开了诸多介入的可能。从这方面来看,在此强调一下人类学教授杰弗里·本杰明(Geoffrey Benjamin)于2006年10月26日在南洋理工大学艺术、设计和媒体学院组织的主题为“信仰”的公共研讨会上所作出的一个基本区分,会对理解本文观点有所帮助。参照过去几十年关于社会理论及宗教的研究和文论,本杰明教授做了如下区分:一种是信仰(或多种信仰),它是表述清晰的一系列主张;另一种是信仰行为,“我们不知不觉参与其中的行动”。必须注意此处的“辩证法”,即“我们同时既是行为者也是我们行为的承受者”,他说:“我们可表述的“信仰”是我们后来生产的主张,这么做的企图是为了在他人面前将此时身处这些行为中的我们所经历的体验合法化或合理化。”因而宗教与其说是一套信仰,不如说是把信徒与非实证的存在或者非实证的领域以一种“象征性的凝聚模式”互相连接的“交往行动”。因此,在本杰明教授所举证的基督教圣餐仪式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宗教旨趣的两种模式的比较:一方面,天主教徒把面包和酒“变质化体”为耶稣的肉和血,当作“真身临在”来体验;另一方面,新教徒将这一仪式理性地转化为一种象征性的纪念举动。
换句话说,就宗教信仰或政治信仰中的“意识形态”或“宣言”来说,对体验的清晰表达或概念化促进某种“教旨”或“教条”的发展。我发现本杰明教授所提出的这一区分,对理解新加坡双年展参展艺术家提供给观众来体验的艺术参与行为而言,十分有价值。它使我明确需要进行一种转变,从过去把信仰当做一种“主义”或一套“主义”来研究,转而把信仰看做一种位处时间和空间中的人所经历的行为或动态过程。其实,这一区分还暗示出艺术与艺术创作之间存在一种与之平行的区分。本杰明教授在演讲中也提到这点,他说艺术(我认为这里他指的既是“艺术创造”也是“艺术欣赏”)“必须包括主动情愿地将自我注入艺术客体或行为中”。我们称之为“艺术”的东西可以从“主义”这个角度表述——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二十世纪艺术史提供了一份长长的艺术运动清单,其中包括,例如,立体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结构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表现主义、社会现实主义、观念主义、极简主义,还有感官主义。但是,既然我们有必要在理解当代艺术运动的基础上拓宽和深化艺术话语,我们就必须对艺术创造的参与体验予以特别关注。
正是这种参与感——还有,我想补充一点,愉悦和充实感——建构了首届新加坡双年展虽然无形但意义深远的成就,展览主题为来自全世界的人们,尤其是本地观众,创造了诸多机缘和渠道去体验如此惊人的丰富多样的艺术。
在构筑本届双年展的策展框架时,南条先生和他的同僚们非常注重强调信仰这一主题不仅关联宗教信仰,还包括哲学及政治信仰在内的其它众多信仰。确实,双年展许多作品接受了这一挑战,从政治信仰角度切入问题,而这也再次强调了当代艺术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艺术与生活不可分割,在某种程度上政治和经济彻头彻尾地塑造了当代生活形态,至于社会和全球力量怎样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艺术完全可以对此作出回答。正如新加坡美术馆的展览“现在出局(Out Now):七十年代东南亚艺术实践”所证明的那样,东南亚的当代艺术必须置入去殖民化和塑造民族国家这一政治语境当中。另一方面,艺术与政治的关系也触发许多问题。政府当局、赞助方以及民众有时候会认为某件艺术作品“有争议”或“政治不正确”或“政治上让人无法接受”;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就出现了关于审查制度方面的争议,原来的艺术作品本身不再受到人们关注。在此过程中间,他们提出的疑问不仅涉及该作品本身的美学价值,有的是关于花费公共资金制作这样的艺术是否恰当,甚至从根本上质疑作品的“艺术”地位。
为了简洁起见,也许我们可以通过重温乔治·奥威尔的洞见来梳理艺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所有的艺术都是宣传……(但是)并非所有的宣传都是艺术”。对于奥威尔而言,每位作家(乃至,每位艺术家)“都在作品中传达了某种“主题思想”,无论他(或她)承认与否,而且他(或她)的作品中最微小的细节都处于它的影响之下”。在我看来,奥威尔,以及许多艺术家和关心艺术的人们,的确不希望将艺术降格为宣传,或者政治意识形态。宣传家到别的工作领域,比如政府机构或广告业寻找职位更合适。当代艺术通常不仅传递单一的“思想主题”,更是针对思想、阐释、感受以及形式的探索;它是一种“领悟”,一种开放的过程,随着观者的参与而延续。这是个尽可能与宣传保持距离的过程。
实际上,新加坡双年展的宗旨超出任何对艺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简单构想,显而易见的是,许多作品的“政治性”可以从其创造者具有探索某个重要思想的需要这个角度去理解。然而双年展的参展艺术家们绝非意识形态的盲从者,同时也很难将他们的作品视作宣传说教。本文不打算对这些艺术家及其作品卷入观众的不同方式详加分析,然而,这里将提及三件可能具有启发意义的作品,虽然它们外在的“思想主题”具有欺骗性地貌似政治口号,然而却吸引观者深思:安修克·苏库马兰(Ashok Sukumaran)的电动装置《一切都可争议》;侯赛因·戈尔巴(Hossein Golba)印在金砖上的作品《差异即价值》;以及芭芭拉·克鲁格(Barbara Kruger)印在商品上的字句,“信仰 + 怀疑 = 智慧”。这几个作品及其它参展作品使我对艺术家们表现“信仰”这个主题的方式有了大致印象:他们试图解构那个固定、牢靠、纯粹而不搀杂质的“信仰”概念,从而去发现一个流动并开放的信仰的过程,这个过程接纳——借用前文引用的“口号”的关键词——争议、差异和怀疑。因为,假如信仰不是与信仰行为在本质上紧密相连,那信仰又该是什么?尽管它充满着不曾言说的,也许是不可言说的,模糊而复杂的不安瞬间,同时潜藏着焦虑与矛盾。
当我从市政厅中Jason Wee创作的多媒体装置《1987》旁边走过,年轻的志愿导览者热情地将作品指给我看,我便问她怎么理解艺术家曾祖母的去世与所谓的“光谱行动”(Operation Spectrum)之间的关联。她回答,“我认为两者都与缺失有关……”这缺失指的是心爱之人的离去,还是某种信仰的沦丧?是理想的丢失,还是理想主义的远离?对于新加坡整整几代人而言,它意味着什么?或是给他们留下了什么?(同样值得一提的是王良吟(Amanda Heng)的综合材料装置《值得一游(新)有限公司》质询新加坡是否是一个“没有激情的文化贫瘠城市”,同期还举办了主题为‘缺失(的)文化’的公共论坛)。信仰的缺失是否标志着无信仰和无神论的开始?又或者,当个人对争议、差异和怀疑的面孔展开质疑和搜寻之际,未被言说的信仰过程就已在悄然进行呢?那些已找到无可争辩的,独一无二的且不可置疑的真理的狂热分子不是最虔诚的信徒吗?维特根斯坦写道:“凡不能言语处,皆付之默然”,也许艺术所为即是让沉默开口言说。
由此我认为,双年展对许多人而言,是对不可言说的超验神秘之物作惊鸿一瞥。“瞥视”这个词暗示的是一种短暂且不完整的观看,以及意味着一种新的理解或领悟。无疑,每个观者与这么多作品中的任何一件的遭遇注定是短暂而不完整的。同时,花费些许耐心去体验一件作品可以使我们瞥见被视作“主义”的信仰所遮蔽和疏离的不可言说之物,瞥见那熟稔又陌生,然而界于现实与非现实之间的神秘之物,瞥见通常无法触及的更高界域里的超验之物。此次双年展能达到各种层面上的深度实非偶然,尤其是主题的设计,以及邀请艺术家在宗教朝拜场所创作特定场所艺术。假如有什么可以称作“新加坡特色”——这是旅游业的官方口号——那便是不同信仰的共存,这点具体表现在城中鳞次栉比的教堂、清真寺、寺庙和犹太庙。因此各种迷人的艺术也出现在克里斯南-兴都庙,隔壁的观音堂佛祖庙,街道靠北的马海阿贝犹太庙,附近的两个天主教堂(圣彼得与保罗大教堂以及圣约瑟夫教堂),还有稍远一点的苏丹清真寺。同样本文无法充分讨论这些作品,也许重点举出以下的例子就已足够,在观音寺庙展出的杉本博司(Hiroshi Sugimoto)的视频《加速的菩萨》中,多个菩萨图像不停地加速,以获得一种超验的虚无感,而在圣彼得与保罗大教堂展出的阿尔瓦尔·巴拉苏巴马廉(Alwar Balasubramaniam)创作的具有汽化功能的组合装置《天使浮现》中,天使缓缓现身,使徒安详的脸庞仅在双年展最后几周才现形。的确,神启能突然降临,而“化体变质”的神迹也可以慢慢发生。而与此同时,N.S.哈夏(N. S. Harsha)的《宇宙孤儿》——一件由人像绘画组成的装置作品——正静静躺在克里斯南兴都庙的屋顶上。
解读新加坡双年展及其作品的方式有多种,我提议应该更多地关注艺术创作以及观者与艺术作品的邂逅。有句话曾说“眼睛看见的是心灵的理解”。是故我们从这些艺术中能看到什么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创造性愉悦力和批判力,而这些反之又取决于我们所接受的艺术教育程度,以及在更大的开放的知识话语环境中的浸染。首届新加坡双年展是众人的集体作品——策展人、管理者、学者、赞助人、志愿者,以及为我们所有观众敞开神圣空间的宗教场所租借人和朝拜者。然而,没有艺术家就不存在艺术创造,他们向我们期望的不是宽容而是理解他们作品的耐心。较之作为社会和谐的起码条件的宽容而言,这种耐心是在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中建构真正的跨文化对话所更需要的。
【编辑:唐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