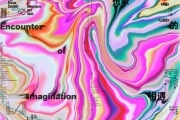邱黯雄: 动物园的基本规则是囚禁(文章原标题)
邱黯雄
“动物园的基本规则是囚禁。”从成名作《新山海经I》开始,艺术家邱黯雄就偏好以动物作为切入点,来表达对现实社会的分析与批判。近日,邱黯雄最新个展《动物园》作为2011“青年OCAT计划”在深圳华侨城当代艺术中心展出,展期将至8月23日。
在展览自述文字中,邱黯雄说,在那些些许衰败的动物园场景里,曾经自由的动物被囚禁在一个似乎“人道”的人造自然之中。展览现场,作品《怀疑者》表现一只死在洗手间的猩猩,场景仿若《马拉之死》的引用和重构;《革命》则描绘一只被吊死的猪,俨然乔治?奥维尔《动物庄园》的另一结局;刚完成的新作《剩余价值》则设置了一款马厩,但中间只有马具却没有马,以传达动物剩余价值被榨干的事实;而《莫名的幸福》则通过兔子一家三口日常生活的一景,表现物质消费对于人的囚禁。沿着这般思路深究,邱黯雄还试图审视广泛存在于人类文明、教育与生活中的“牢笼”,揭露所谓的集体文明如何囚禁乃至抹灭个体的过程。在布展期间,本报记者对邱黯雄进行了专访。
进化论只是一种有创造性的猜想
记者:在描述《动物园》的文字中,你开篇即存疑,说进化论只是一种有创造性的猜想,其实与“圣经”的创造说并无本质区别,“科学已经从最初谦虚的探索精神演变为傲慢自大不断更改和宣布我们命运的现代宗教祭司”,这种想法是如何形成的?
邱黯雄:我们所受的教育给了我们固式的观点,并以此标准看世界。最初我也认为进化论是很坚固的真理,但慢慢接受别的观点和知识,比较后才发现它不是唯一的标准。进化论本身很有意思,它揭示了部分真理,但核心部分还是没有说清楚,仍然有很多事情解释不了。过去我们都把科学当宗教,好像不能去反驳,但其实真正的科学本身就是不断试错的过程,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不一定是正确的。
记者:所以你在创作《新山海经》时才说:“想以未开化的眼光看待这个时代,建立起一个观察世界的系统――不是一个西方式的科学的系统,而是一个感知的系统。”
邱黯雄:现代社会系统总想让我们的思维单一化,只接受一种观点,只用一种角度看世界,这样是有助于管理的,但是是不人性的。
记者:如果这种“囚禁”是你所不愿看到的,你觉得什么才是自由?
邱黯雄:生命本身就不可能完全自由,而是一直都在一定范围内有所限制,但人又始终不满足于现状。不少哲学家认为,动物和人类的存在方式截然不同,它们就像是无生命的东西,存在的意识是混沌的。但是我不认同。我认为“自由”,首先得基于对“存在”的追求。动物也有追求,只是说它的欲求没有人类那么多。当你把它囚时它也会想逃出去。
比较早的是《异端的权利》,白色公鸡被困在以数学勾股定理建造的铁塔顶端,这来自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的典故,他把数学和宗教结合起来,但因为一项数学结论违背宗教教义的完美被徒弟发现,而将徒弟以违反教规为由杀掉,可恰恰数学又代表着文明理性的认知,这其实就是一种悖论。包括《怀疑者》、《革命》等作品,都与革命有关――野蛮和文明始终在人类发展历程中纠缠,它追求的是自由理性等正面价值,但始终伴随负面结果而告终。《莫名的幸福》则进入一种现代式的安稳状态,仿佛社会为我们设定了程序一样,大家都认为安稳平庸、有车有房就是所谓的幸福。其实每个时代都有它的程序和标准,而大多数人是没有逃脱的勇气的。
展览现场
用未开化的眼光看世界是一个奇迹
记者:你在作品中常常试图以“魔幻的现实”表现古今、中西、天地、真伪、虚实的关系,在处理这些对立项时,如何做到不那么分裂?
邱黯雄:我还是比较关注宏大主题的,凡涉及此,都必须把背景点出来。比如《山海经》本身就是非常古老的文本,我在描绘这个世界时,一定会给出历史线索,比如选取从古到今的几个时间点,如此对比着看蒙昧时代与现代文明,就会发觉世界其实已经变异;而如果用我说的“未开化的眼光”看待这种变异,它就完全成了另一个生物世界,这时候就提供了另外一种角度。我们今天用科学的眼光看《山海经》,也许会觉得那都是传说与神话,但我觉得它很可能是基于真实的产物,只是描述方式不同――不是基于知识系统的,而是基于感知方式的。因而用当时的方式看世界,会觉得世界是一个奇迹;但是现在看世界,我们已经意识不到这一点了。
记者:说到感知,日本东京现代美术馆总馆长长谷川佑子曾评价说,你并没有试图解释和批评这个世界,甚至都没有描述它,而只是描绘自己想像中的世外桃源。其实你在做《新山海经》等作品时,是一种置身事外的纯感性表达,还是有理性的寓意在其中?
邱黯雄:当然有态度咯!只是说艺术家的态度不是以一种宣传性的、强迫式的方式来呈现,我更多的是把事实摆在这里。比如《山海经》看起来是神话,但指向的都是现实;看起来离你很远,但在现代社会,其实远近都一样。
记者:其实声音也是非常能渲染态度的。在你的影像作品中,画面是中国水墨式的,音乐却是现代的。比如在作品《雁南飞》中,你把希特勒的演讲声音断续失真地插入到影片中去,但其实观众不一定听得出来。
邱黯雄:我当时只觉得不应该用传统乐器与传统曲调,因为那都是古人的状态。用希特勒的声音是因为和片子的主题有关,那一段配的是秦始皇烧书的画面,他们俩都试图不让别的思想出现,其实是同一种状态。我不需要观众能够察觉到它,它给出了信息的那种腔调、那种状态就够了。
任何画派的都有深厚的文化传承
记者:你如何将自己的艺术创作分门别类?
邱黯雄: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喜欢“乱搞”,搞装置甚至行为艺术,在学生里算比较早的。毕业后兴趣比较广泛。在德国的时候画了一批比较山水画的东西,但那个状态不真实,都是虚构出来的。回国后找到了比较平衡的点,新媒体的尝试比较符合自己的天性。慢慢才找到了比较适合自己的风格。
记者:当初去德国深造,异国环境反而促使你开始大量阅读中国哲学,这对你的创作有没有影响?你怎么看待中国传统艺术的价值和当今对于西方艺术的学习?
邱黯雄:当然有很深的影响。我最早是对西方前卫当代艺术感兴趣,觉得那东西很来劲儿;而对传统的东西不了解,加上从小被灌输意识,认为以前的东西都没有价值。后来慢慢接触中国经典书籍,才发现和自己认为的根本是两码事。不过,当时还没有把它和当代艺术关联起来。当时的我很分裂,一边做当代艺术,好像要和过去斩断,创立全新系统;一边又对传统东西深深着迷。后来才发现,创新和传统不仅不是绝对对立的,反而是一致的。西方的创新永远是在传统脉络里的,更像是一种更新;我们则是一种毁灭,把以前的铲除掉,建立全新的系统,但是根基被毁掉,是无法有建树的。所以无论是单纯仿照中国古人画山水,还是盲目崇拜西方搞艺术,我都觉得浅薄。因为任何画派的背后都有深厚的文化传承,而不是一种简单的审美情趣。
记者:你说德国的经历让你对中国传统另眼相看,回来后找准“中国”的涵义了么?
邱黯雄:没有,这怎么可能找得准啊。中国变化太大了,你瞄这儿的时候,它已经在那儿了。
记者:接下来有什么大的创作计划?
邱黯雄:接下来马上要参加欧宁策划的“碧山共同体”乡村计划;《新山海经》明年要做第三部;《动物园》的计划也会继续推进。另外,我和几个年轻艺术家近两年一直在搞一个“未知博物馆”,只需要一个网站,其实就是一个促进思想交流的平台。
邱黯雄简介
1972年生于四川,1994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2003年毕业于德国卡塞尔大学艺术学院。现任教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院。曾受邀参加巴塞尔艺术博览会、上海双年展、亚太三年展等国际艺展,并在东京现代美术馆举办个展。其录像作品《新山海经II》及版画作品于最近被纽约当代美术馆收藏。来源深圳特区报)
【编辑:丝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