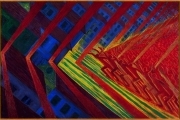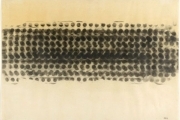德国画家乔治-格罗兹
德国画家乔治-格罗兹的后人与MoMA(纽约现代艺术馆)打起了官司。这场官司揭露了一段令人颇感尴尬的历史。“二战”期间,MoMA买进了大批德奥艺术家所作的现代艺术作品。这些作品在纳粹眼中是“堕落的艺术”,它们在纳粹统治区被查禁、没收,却通过画商再卖到了美国,卖画所得款项被用于资助法西斯战争。买家名单中,MoMA赫然在列。
当参观者在纽约现代艺术馆的售票处买票后,信步走向其雕塑园时,会首先遇到一尊巨大的“巴尔扎克像”,它没有双手,由青铜制成,是雕塑大师罗丹的杰作。1955年5月3日,该作以“柯特-瓦伦丁的友人”的名义被捐给了MoMA,当天在雕塑园还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捐赠仪式。柯特-瓦伦丁本人是纽约的一位画商,他于1954年赴意大利旅行时死于心脏病。瓦伦丁在现代艺术品交易圈极有影响力,因此,在他死后,他的130位朋友凑钱买下了这尊“巴尔扎克像”并捐赠给博物馆,以此行动作为对他的纪念。
MoMA首任馆长阿尔弗雷德-巴尔
来自德意志的“赃物”
MoMA的首任馆长阿尔弗雷德-巴尔也是瓦伦丁的老友,并与他有频繁的业务往来。他告诉博物馆的董事们,对这件礼物,他可是“深受感动,感恩之心无以言表,为能够通过此艺术杰作得以时时缅怀柯特-瓦伦丁先生而感荣幸之至”。他甚至还表示,比起任何一家别的博物馆来,唯MoMA“欠”瓦伦丁最多。
有趣的是,一件罗丹的雕塑对MoMA来说其实不足为奇,而MoMA居然给予此那么高规格的“致敬”。更蹊跷的是,早有传闻说瓦伦丁的生意“不干净”。
柯特-瓦伦丁是个犹太人,他于1937年逃离纳粹德国,来到了纽约。彼时,他怀揣德意志第三帝国美术办公室于1936年11月14日签发的授权函,在纽约西46街开了一家画廊,专卖被纳粹视为“堕落的艺术”的现代艺术品。两年后,他积累了更多的资本,就把画廊搬到了纽约西57街。
瓦伦丁的艺术品生意是纳粹经济链条上的一环。由他卖出的画和其他艺术品所得到的收益,以一定比例回流到了第三帝国,向纳粹提供了支撑其战时经济所必不可少的外汇资源。第三帝国曾经对包括瓦伦丁在内的一批犹太裔画商网开一面,让他们离开德国或奥地利并得以安全抵达纽约,条件则是他们要帮忙销售那些被查没的艺术作品为帝国赚外汇。洛杉矶艺术博物馆的资深策展人史蒂芬妮-拜伦曾于1991年至1992年组织了著名的展览——“堕落的艺术:前卫艺术在纳粹德国的命运”,她说:从柏林的纳粹宣传部的记录上来看,很多艺术作品都被批发给了瓦伦丁,然后他再将它们转售向(德奥)境外。
瓦伦丁开出的价钱通常都比市场价要低。于是,如MoMA的巴尔或纽约“非物体绘画博物馆”(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前身)的希拉-瑞贝等一干博物馆高层就开始向瓦伦丁买艺术品,并从而入手了包括乔治-格罗兹和保罗-克利等人于“二战”前和战时被纳粹没收或抢走的部分作品。这部分作品从此进入了MoMA和古根海姆的永久藏品行列,至今尤然。
纽约的律师雷蒙德-铎德在加利福尼亚的一所学校兼职教授历史,他曾著《浮士德式的交易》一书,在书中这么写道:如果我们说到纳粹德国时期的艺术,就不能漏掉那些在战前和战时纳粹自民间掠夺的艺术品,这些艺术品经由瓦伦丁在纽约曼哈顿的画廊最终进入了MoMA的永久性收藏行列,而原本拥有这些作品的艺术家或收藏者连一分钱的补偿都没得到。
获纳粹授权的犹太画商柯特-瓦伦丁
追讨行为成螳臂当车
在针对MoMA的指控中,铎德充当了画家乔治-格罗兹的两位遗产继承者马丁(长子)和莉莉安(小儿子彼得的妻子)的代理人。2009年5月,铎德将诉状提交至纽约南区联邦法院,要求MoMA将其收藏中的三件格罗兹的作品退还给其财产继承人,作品包括:两幅油画《诗人马克斯赫尔曼内斯》(1927)、《与模特的自画像》(1928)和一幅水彩画《共和机器人》(1920)。面对起诉,MoMA立刻做出了回应,声称对所涉及三幅归属有争议的作品拥有正当的所有权。
2010年1月,法官科林-麦克马洪以“格罗兹案”早已超出法定三年的诉讼时限为由驳回了对MoMA起诉,而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亦维持该判决。铎德把状子递到了美最高法院,但最终还是在2012年10月遭到拒绝审理的回复。
铎德抗议道:法庭斤斤计较于诉讼时效这种技术性层面的细节,而罔顾最基本的事实证据,这简直就像诚心要讨MoMA欢心似的。
美国艺术品回归委员会的律师查理-戈尔斯坦虽然没有参与“格罗兹案”,但当他重新检视了与该案有关的浩瀚档案之后,他表示他对MoMA很失望。他起初试图完整还原格罗兹和其他艺术家的作品如何被博物馆收藏的全过程,可是MoMA所提供给他的资料却无法满足他的研究所需。“这确实是一种掩饰。”戈尔斯坦说,“我们现在根本搞不清楚他们究竟是不是该拥有那些作品。但是从他们的做法来看,他们想要掩盖一些事情。”
戈尔斯坦认为,MoMA的现任馆长格伦-洛里作为美国美术馆馆长协会(AAMD)的会员,理应遵循AAMD的规章。AAMD曾敦促各博物馆遵守“被纳粹没收的艺术品协议”,该协议由美国国务院拟定,并在1998年于华盛顿举行的“大屠杀时期财产”大会上由44国代表共同签署。
“《华盛顿协议》上写得很清楚‘看看你们的收藏品,仔细检查每一件,把所有的信息都公布于众,如果有人主张权益,要认真对待,以取得公正、公平的结果’。”戈尔斯坦说,“很显然,MoMA早就认同一旦遇到艺术品所有权的争议,会致力于实现公正、公平的结果。但是,现在他都做了些什么?他把索赔纠纷闹上法庭,再通过司法手段来逃避责任。”
戈尔斯坦补充道:一般人会比较希望此类纠纷能够由当事人双方要么私下里、要么通过第三方的仲裁机构来协商解决。然而,无论是MoMA,或是波士顿美术馆,还是其他的美国博物馆,对藏品所有权纠纷的处理模式都如出一辙,那就是让纠纷升级成诉讼,再于法庭上以大击小解决对手,并制造出对同类索赔案的寒蝉效应。“假设你想要主张你对某件艺术品的所有权,那么你得去跟博物馆谈谈。可你很清楚一旦你走进博物馆大门,才刚开口说了句‘我想要跟你聊聊我爷爷的画’,你立刻就变成了法庭上的被告了。”他说,“很多人在看清楚这点之后,就改变了主意,于是就算了,不是吗?”
而MoMA的发言人则声明:博物馆没有不遵循AAMD的章程以及其所敦促的与《华盛顿协议》有关的内容。同时,还指出:“MoMA有专人负责协调6个部门并从事基本馆藏品的出处的研究。这些研究是基于对所有的有关藏品借入和借出、新增藏品和基本馆藏品的资料的。此类研究的动态信息与最新进展属相关团体共享,一旦某项信息涉及MoMA馆藏的艺术品,该信息会被添加到博物馆的档案记录中,并且出现在‘艺术品源流计划网站’上。”
在另一份声明中,MoMA声称他们“于近6年来,仔细研究过关于格罗兹的作品的出处……最终MoMA完全排除了任何关于这些作品涉及二战期间掠夺行为或涉及任何其他更严重的行为并因此需要给付赔偿的可能性,而与之相关的索赔主张甚至远远超出博物馆面对此类特殊情况所应承担的最大的道德与法律义务,因此MoMA对此类索赔所实施的对策实乃问心无愧之举……基于对此事件的最深入的研究以及对此类事关敏感话题的索赔请求的深切理解与尊重的基础上,MoMA得到的结论是:本馆对格罗兹的作品拥有无可置疑的所有权。值得注意的是,法院所发现并据以驳回对方索赔请求的诉讼时效问题与二战期间及此后语焉不详的藏品档案记录无关……因此任何有关通过拖延诉讼时间或其他手段置诉讼当事人于不利境地的说法俱属不实。”
柏林画商卡尔-巴克霍尔兹
被纳粹出卖的“堕落的艺术”
关于柯特-瓦伦丁档案有90函之多,它们记录着他在美国所度过的17年的生涯,目前正存于MoMA的资料室中。根据MoMA网站上所列的资料目录来看,档案所录有关瓦伦丁在德国那35年的事迹十分少。而且,MoMA网站上所刊瓦伦丁的生平介绍也简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结束学业之后,瓦伦丁成为了一名柏林的现代艺术品商人。”其中甚至都没提及瓦伦丁曾担任赫赫有名的犹太画商阿尔弗雷德-弗雷希特海姆的助手的经历。
弗雷希特海姆于1920年代在柏林和杜塞尔多夫都开有画廊,里面既展示有德奥现代艺术家的作品,也有毕加索、布拉克和夏加尔等人的作品。
在铎德提交给法庭的文件中详细叙述了格罗兹所经历的磨难和他与弗雷希特海姆、瓦伦丁以及MoMA的纠葛。1923年,格罗兹于弗雷希特海姆在柏林的画廊中举办了其第一次个展,这次展览有助于建立其艺术声誉。两年之后,格罗兹答应让弗雷希特海姆包办其作品的销售,作为交换他每月还能从弗雷希特海姆这里得到300到800帝国马克的津贴。1927年格罗兹以其友人为模特创作了《诗人马克斯赫尔曼内斯》,并于次年4月交付于弗雷希特海姆。5月,该作即于普鲁士美术学院展出。
1931年3月,MoMA举办了一场德国油画与雕塑展,展品中有格罗兹的7幅油画,其中4幅是从弗雷希特海姆画廊借来的,其中就包括《诗人马克斯赫尔曼内斯》和《与模特的自画像》。
从1931年12月起,弗雷希特海姆陷入了财务困境,虽然他仍能经营手里的格罗兹作品,但已不得不取消每月要支付给画家的津贴,也丧失了独家代理权。1932年,弗雷希特海姆的财务状况小有起色,他想要恢复往日气象。恰在此时,瓦伦丁来到他身边成为其助手。1932年5月,他派瓦伦丁面会格罗兹。这次,格罗兹拒绝了由弗雷希特海姆独家代理其作品的提议。
格罗兹那时已经做好了离开德国的准备。他并不是犹太人,但他屡屡公开批评纳粹。1933年1月12日,他离开柏林奔向纽约开始其新生活。18天之后,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又过了仅一天,纳粹冲锋队就闯进了格罗兹的公寓和工作室。“我敢肯定,要是我还在那儿,我就没命了。”画家晚年在他的自传中这么写道。
在希特勒掌权的头几个月里,计划已久的通过包括没收犹太人财产以实行“雅利安化”的一系列计划得到实施。1933年3月,画商亚历山大-弗美尔霸占了弗雷希特海姆在杜塞尔多夫的画廊。“弗美尔是纳粹的准军事化组织褐衣党的成员。”在有关“格罗兹案”的一份文件中这么写道:“弗美尔接手弗雷希特海姆在杜塞尔多夫的画廊被视为一种实现‘雅利安化’的行为。强迫弗雷希特海姆转让其在杜塞尔多夫的画廊,是一个强烈的信号,预示着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其在柏林的画廊。”
铎德在诉状中写道:事实上,在1933年11月弗雷希特海姆逃离德国之前,他曾雇用了一名德国“税务顾问”,名为管理画廊事务实则为了尽快将资产折现,或为凑足能让犹太人得以离开德国所需支付的所谓“飞行税”。“弗雷希特海姆画廊关闭了。”身在纽约的格罗兹于此后不久收到一封署名舒尔特的信上这么写道。舒尔特在信上要求格罗兹偿还欠画廊的16255马克,但是格罗兹认为他不欠画廊一分钱,因为画廊经年来支付给他的月度津贴是建立在不用退还的前提下的。
舒尔特则提醒格罗兹说:画廊尚保存着数幅他寄售的作品,“但此类作品于当下毫无任何市场。因此我无论如何要求你支付给我现金。”最后,舒尔特以1/4的价值获得了弗雷希特海姆的画廊,并避免了破产保护,但没从格罗兹手里拿到一分钱。
而弗雷希特海姆此时终于顺利逃亡至伦敦,随身居然还带上了数幅寄售的油画,并在伦敦的James Mayor画廊继续其画商生涯。在他于1934年4月写给格罗兹的信里提到,包括《共和机器人》在内的几件格罗兹的油画被带到了James Mayor画廊,而《与模特的自画像》与另几件作品则委托给了巴黎的Billet画廊。这回,连他都伸手向格罗兹要钱了,“我在德国的一切都被抢走了,只身流亡海外却分文没有!”他感叹道。事实上,他的妻子贝蒂那时还滞留在柏林,此后的8年间,她整天整夜努力推销其不动产,就为了凑足离境所需“税”款。
MoMA首任馆长巴尔对弗雷希特海姆的窘境一清二楚。1935年8月8日,弗雷希特海姆写信给巴尔说:“我失去了我所有的钱和所有的画。”他同时补充说他拼命保留下来的“唯一的作品”是一件维尔哈姆-伦布鲁克的雕塑,希望巴尔能掏钱把它买下来。“他看似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巴尔于此后给其代理人的信中这么写道,“因此,我觉得他给这件现代雕塑杰作开出的价格不会超过2000美元,而我们可以再压压他的价。”这件伦布鲁克的雕塑如今被称为《站立的青年》,由艾比-奥德利奇-洛克菲勒于1936年赠予MoMA。
弗雷希特海姆自此日益穷困潦倒。1937年2月,他在柏林的画廊正式宣告解体。而他和妻子贝蒂则在1936年就宣布离婚了,他们觉得假使他们俩没有了婚姻关系,她的日子会好过些。(那时,他们还想着能在未来复婚。)1937年3月,弗雷希特海姆在伦敦踩到一只生锈的钉子,进而引发了坏疽。医生把他的双腿都截去仍无济于事,不久之后,弗雷希特海姆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了。1941年,因听说或许要被送去“东边”(集中营的隐晦说法),贝蒂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了。
现藏于MoMA的格罗兹作品《诗人马克斯赫尔曼内斯》
犹太裔画商获纳粹授权卖画
瓦伦丁则于1934年就离开了弗雷希特海姆画廊并在柏林的巴克霍尔兹画廊找到了新工作。画廊主人卡尔-巴克霍尔兹不是犹太人,而且,根据研究纳粹时期艺术史的专家的说法,巴克霍尔兹于1938年前后成为了获得纳粹特许的四大画商之一,他们拥有专营大宗被从博物馆里扫地出门的艺术品交易的授权。
至1936年11月,瓦伦丁完成了与纳粹的交易获准出境,移民去纽约并且经营“堕落的艺术”以资战争所需。授权函上写道:“谨代表帝国美术办公室主席告知如下事宜,他不反对您在德国境外充分运用您在帝国艺术圈的人脉资源以拓宽帝国的出口贸易渠道。一旦您离境,您可以自由地收购德国艺术家在德国创作的艺术品,并在美国将之妥善运用。”
1937年1月,在巴克霍尔兹的资助下,瓦伦丁得以在纽约西46街3号开设巴克霍尔兹(纽约)画廊。根据巴克霍尔兹的传记作者,他的女儿高杜露的说法,瓦伦丁抵达纽约时,携带着无数来自德国的“堕落的艺术”作品。一般来说,犹太人即使获准离开纳粹德国,也只获准携带顶多10马克。但是,瓦伦丁的“行李由成箱成箱的雕塑、油画和素描组成,它们来自柏林巴克霍尔兹画廊”。她的说法与瓦伦丁的自述形成了戏剧性的对比,据巴尔转述瓦伦丁的话说,他“一贫如洗地来到了纽约”。
因涉嫌违反《战时与敌交易法案》(并被检获了部分由巴克霍尔兹送来的画作),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在战后传唤了瓦伦丁。而瓦伦丁则辩称其画廊的大部分资本来自于银行家E.M.Warburg。关于巴克霍尔兹的资助,他对FBI只字未提。在1942年所写的一封支持瓦伦丁申请美国国籍的信中,巴尔也对此只字未提。“瓦伦丁先生遭受纳粹的迫害,既是因为其犹太血统,也因为他与被希特勒禁止的自由艺术运动的联系。”巴尔写道,“他于1937年只身来到这个国家时,所有财物都已遭纳粹劫掠一空。”妙的是,MoMA的官网上所说的信息却更接近于巴克霍尔兹的女儿的版本,网站上的记载为:“1937年,瓦伦丁移民来到美国。他带来了数量巨大的德国现代油画作品,足以供其以‘巴克霍尔兹’的名义在纽约开设一家画廊。”
巴尔很清楚瓦伦丁与巴克霍尔兹及纳粹政权的关系,但他想利用瓦伦丁来打开收购被纳粹查没艺术品的通道,他俩那段时间的通信把这点说得很清楚。从1937年开始,纳粹从德国各个博物馆中查没了超过17000件艺术品。当希特勒从中挑选出他想要的那些之后,纳粹把剩下的大部分作品、约4000件堆在柏林中央消防局门前的广场上,于1939年3月20日将之付之一炬。
超过700件被纳粹劫掠来的作品被交到了画商手里用来换取外汇。其中126件油画和雕塑于1939年6月30日整批出现在了瑞士琉森菲舍尔画廊举办的拍卖会上。其中除了布拉克、夏加尔、高更、克利、马蒂斯、莫迪里阿尼和蒙德里安的作品,还有德国和奥地利的表现主义作品。
《与模特的自画像》
拷问良心的拍卖会
菲舍尔拍卖会向几乎所有的美国博物馆馆长出了一道道德考题。一个千载难逢的收购拍场上无价之宝的机会来了。不幸的是,这些作品实属从德国的博物馆里抢出来的“赃物”。后一点足以说服大部分的美国博物馆与之保持距离,尤其是当大家获悉3月份的那场无情大火之后。但也有人认为与其眼睁睁看着那些杰作被烧毁,还不如去参加菲舍尔的拍卖会。
私人藏家则比较少顾忌了。纽约银行家莫里斯-维特海姆在拍卖会上以17.5万瑞士法郎(约合4万美元)拍下了凡-高于1888年题献给高更的自画像。该作掠夺自德国慕尼黑美术馆,目前藏于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
巴尔带着委托人的资金赶赴菲舍尔拍卖会的时候,也悄悄地把瓦伦丁带上了。当天,MoMA一口气买进了5幅油画。拍卖会结束后一天,巴尔从巴黎写了封信给MoMA的同事:“我很高兴MoMA或我的名字侥幸没跟这次拍卖会扯在一起……我认为当我们今后再需要买进德国艺术品时,应当通过纽约的巴克霍尔兹画廊,这点很重要。”
这点很快就实现了。两个月后,MoMA宣布通过瓦伦丁画廊购进了那5幅油画。那时候,瓦伦丁已经从巴克霍尔兹手里买下了画廊(而更名为瓦伦丁画廊则要迟至1951年)。当时的艺术媒体对这次收购爆发出一片赞扬声,誉之为通过对所谓“堕落的艺术”的支持而对纳粹政权作出否定的表态。
戈尔斯坦则认为,博物馆当时本应与菲舍尔拍卖会保持距离。他提示到当“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国务院曾将MoMA列为“值得注意”那档,提示各追讨艺术品赃物的机构关注。“在被特别警告过之后,他们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买进了目前他们所藏的所有那些出处不明的艺术品。”戈尔斯坦说。
根据史蒂芬妮-拜伦的说法,当时,即使是很多私人收藏家也很抵制菲舍尔拍卖会。她在书中写道:“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对于是不是要参加拍卖会都很矛盾,这可以理解。一方面,参拍的作品都是如此稀有且拥有极高的品质,让人不忍错失;另一方面,抵制的情绪也很高涨,人们能想象出拍卖所得收益注定会助长希特勒的邪恶气焰。”然而,拜伦相信,这些买家无论出于何种动机,起码他们“保护那些艺术品免遭纳粹毒手。”
瓦伦丁从菲舍尔拍卖会开始,充当了MoMA的“现代艺术传教士”。巴尔支付给瓦伦丁丰厚的报酬,不仅把委托人送到他的画廊,自己也每周定期拜访他。瓦伦丁与巴尔长达15年亲密友谊的结果,是MoMA得以买进大量“赃物”与“来源不明”的艺术品,最终扩充了其馆藏。
《共和机器人》
时过境迁,旧事哪堪重提
1944年5月29日,根据美国《战时与敌交易法案》,联邦政府检获了巴克霍尔兹运给瓦伦丁的401件艺术品,其中至少有一件最终成为了MoMA的藏品。这件奥古斯都-马可创作的《公园里的女人》,最早由瓦伦丁卖给了收藏家亨利-珀尔曼,珀尔曼基金会于1956年再把画作捐赠给MoMA。
多年来,MoMA也偶尔会承认其藏品存在“出处误差”,并于1965年的一份文件中列出一张包含16名艺术家作品的清单,“其作品于战前俱藏于德国,后被纳粹指为‘堕落的艺术’”,其中三件作品购自菲舍尔拍卖会。MoMA于2000年4月提交的另一份清单“馆藏出处有误差的1933-1945欧洲油画”中,除去与1965年清单所列重复的那几件,又提及了共15幅出处存疑的作品,里面也有通过瓦伦丁购买的作品。MoMA声称:“我们没有确切的关于这些作品曾为纳粹赃物的证据。我们保留了它们,因为至今尚无法获悉它们于纳粹统治期间的完整或部分流转状况。”“格罗兹案”所主张的三件作品中的两件——《诗人马克斯赫尔曼内斯》和《与模特的自画像》即同时出现在上述两张清单中。
事实上,归属存在争议的三件格罗兹的作品都是在它们于弗雷希特海姆处寄售时与画廊一并遭纳粹掠夺。铎德坚持的论调是:涉案的三件画作都是纳粹从弗雷希特海姆画廊所得到“赃物”,尽管格罗兹从未放弃他对此三件作品的所有权,但当它们出现在MoMA之后,格罗兹并未获得分文补偿,依旧是一个浪迹在曼哈顿的穷艺术家。
当MoMA于1952年首次展示《诗人马克斯赫尔曼内斯》后,格罗兹在给他妹夫的信中写道:“现代艺术馆正在展示一幅我的画。我不知道他们从谁那里买到这幅画,但是卖家或许就曾参与了对我的洗劫。可是,我现在无力反抗。”他在之后写给友人的信里又提到此事:“现代艺术馆买了一幅我的画,那是一件‘赃物’……但时过境迁,旧事哪堪重提?”
事实上,早在1994年,格罗兹家族就聘请了艺术史学者拉尔夫-延奇来调查那三幅作品流传的来龙去脉。经过了差不多10年时间的挖掘,延奇梳理出了格罗兹、巴克霍尔兹、瓦伦丁和巴尔之间的关系。2003年他致信MoMA,要求将那三幅作品归还给格罗兹家族。此后三年间,MoMA与格罗兹家族“共同研究”了问题,并“进行了深入沟通以期达成和解”。直到2006年1月,延奇才猛然意识到MoMA拖延时间的花招。
2006年3月22日,MoMA的董事收到了关于格罗兹画作出处的最终调查报告。该份报告简短而切中要害:“乔治-格罗兹本人的信件足以证明他所认为的其被窃作品当时已成为MoMA的藏品,而他保持了沉默,此后也没有主动接触MoMA主张所有权,也从未要求返回作品或谋求任何其他的解决方式。”因此,报告总结道,“我建议拒绝格罗兹家的索赔请求。”2006年4月11日,MoMA的董事们投票表决拒绝归还格罗兹的画作。这一决定导致了此后长达三年的漫长诉讼。
面对诉讼失败,铎德坚信:“当全部真相了然之际,我们会跟MoMA法庭上再见!”
【编辑:冯漫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