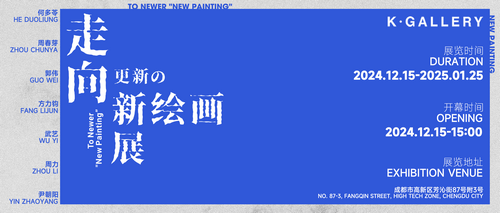钟孺乾
记者:作为一个画家,您怎么想起写这样一本15万言的理论著作呢?这本《绘画迹象论》成书的过程是怎样的?
钟孺乾:这和我自己的创作实践和学画经历有关系。我是军旅出身的画家,各种不同类型的画种我都实践过,后来水墨画和书法成了我的专业。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那时正是创新思潮最盛行的时候。我感觉画种的界定并不是主要的,它们之间有一种共同的基本元素。我尝试用色彩与水墨来创作,后来人们管它叫重彩写意。本来重彩是同工笔相联系的,而写意是同水墨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材料、技法还是理念都有所不同。我把这个矛盾的双方结合在一起。因为单纯的一种形式不能够反映出我想要表达的意念。十多年过去了,我还在进行这方面的探索。我认为和创作比较起来,这些年中国美术界的理论则显得相对滞后,首先体现在基础理论上,一个时代如果没有基础理论做后盾,无论你说多少大话,考虑问题多么宏观,还是没有根的,在半空飘着呢。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大家忽略了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大部分学贯中西,有才华的理论家或是把精力放在对外来理论的翻译和引进上,或是致力于古代艺术思想和典籍的整理工作,另外还有一些理论家在从事展览策划,艺术批评等方面的工作。总体感觉当代中国美术基础理论的研究,包括对画家的介绍也是大而化之,落实不到艺术本体上。在今天,谈到当代艺术,要么就用西方的引进概念来解释,要么就用唐、宋、元、明、清的现成画论来解释,并没有和我们这个时代的实践紧密联系的理论概念和词语。
记者:也就是说缺乏与当代艺术尤其是当代中国画相对应的品鉴语言和批评系统。
钟孺乾:即使在对古代画论的借鉴与理解上也捉襟见肘。当代两个艺术大家曾讨论过关于笔墨到底重要还是可以不要的问题,我认为这样的理论起点不太高,从我自己的实践和有限的知识来判断,我认为这不足以或不应该成为一个被争论的问题。他们的观点非常之极端,讨论的核心问题根本就不存在。
记者:这本书一出来,就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落笔成迹,因迹生象,看起来确实很简单的事实,那么你在本书的主要观点究竟是什么呢?
钟孺乾:本书的立足点还是基础理论,不是解决艺术思想或者文化策略的问题。那天同田黎明先生谈起这本书,他也非常支持我在这方面的研究,他建议如果此书再版的话就可以不用“绘画迹象论”这个题目,用“迹象论”就更开阔一些,刘骁纯先生在本书的序言中就直接用的“迹象论”。而当时加上“绘画”这两个字是程大利先生考虑到我第一次出书,圈定一个范围会使得此书操作起来方便一些。“迹象“是一个视觉领域的概念。实际上本书中所涉及的范围已经超出了绘画的范围,比如说雕塑、多媒体。整个研究的框架是视觉艺术的基本元素“迹”和“象”。古人认为迹和象都代表着有形的可见之物。由此可以看出“迹象论”是辐射到视觉艺术的各个门类的。
记者:刘骁纯先生在序言中对此书有高度评价,他说迹象论的前导理论有三:形式派理论、笔墨论和图像学。对此你怎样看?
钟孺乾:刘先生作为一个理论家这样来分析自有道理。他所提到的形式论和图像学是解决我所提到的“象”的问题。我这本书中新提出的概念就是“迹”,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概念,在书中我是从上古时期谈起“迹”这个概念的,因为是古老的,所以为大家所忽略。用一个时髦的词来概括的话,我这本书是谈的视觉艺术的基因。从视觉的发生开始,一直谈到基因的遗传、变异和拓展。开始我还想把书的副标题写为“绘画的基因”,但是怕科技知识不足反而会犯张冠李戴的错误。我任教的大学是个综合性大学,也有研究生命科学的专家,同他们讨论时,他们也说这种比喻是贴切的,如果把“迹”和“象”当成绘画的两种元素的话,它就会有传递、遗存、扩展、延续等一整套的发展体系。如果没有“变异”这种适应性的扩展,我们现在欣赏抽象派的绘画是很困难的。
记者:绘画理论一旦和科学思想联系在一起,就会让人产生理解上的玄妙感。简单来说,实际上“迹象论”就是试图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来理解艺术,即通过对一个古老概念的重新解读,把它“从日常用语转换成了学科概念”,从而使之在理论发展史上找到了一个可以连接上下文的点,是这样吗?
钟孺乾:也可以这样理解。在本书中,我一是提出“迹象论”在绘画史上有什么依据?二就是解释其有什么益处,对绘画产生怎样的积极影响。“迹象论”作为元素分析法应用于对艺术品的鉴赏时,有利于我们做综合分析。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鉴赏标准,对于当代出现的新的绘画形态,我们一直没有新的视角去理解,经常造成错位。明明是迥异从前的艺术形态,我们还用既有的理论和视角去分析和鉴赏,比方说笔墨啦。更何况这些概念也没有经过我们现代人的咀嚼与认识,不过是在旧的框架中来评价新的迹象结果,所以对当代艺术的评鉴容易处于一种盲目和有失公允的状态。如果用迹象论这种既有传统艺术理论的根基、又有同现代艺术实践相符合的基础理论来分析和理解现代艺术作品,应该是非常顺畅的。我在书中提出的简单公式就是“迹+象+X=画”。其中的X,就是观念,境界,情感,以及一切你想要表达的内涵。把问题简单化,作为一个认识事物的方法来讲是有意义的。如果看一个难懂的作品时,就可以用迹象论来分析归类。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很好的遗产就是作迹、辨迹的本能与天赋,在分析艺术作品时可以从没有可能的地方找到“象”,于无声处听惊雷。比如德库宁,他是一个抽象表现主义的画家,实际上他有“象”,这个“象”被西方人神秘化了,但在我们看来是非常简单的,根本不用去做玄奥的分析。对不易辨识的图像解释所产生的个体差异也被我们认为是正常的事情,因为要用个人判断把不确定的图像确定下来,每个人都会去主动地接受和欣赏。实际上西方人在解读现代艺术时受东方影响非常之深,但往往我们中国当代艺术家顺畅做出的作品却被贴上了西方来源的标签,被认为是剽窃别人的创造。“抽象”一词只是西方人从哲学中借过来的词,这个概念对于评鉴中国绘画并不合适。
记者:你认为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系统中有没有与之相对应的概念呢?
钟孺乾:有,就是“虚”。而且这个概念应用范围更广,从文学、哲学到艺术都可以应用。苏东坡为什么认为画得像不过是“见与儿童邻”?只实不虚,必会有局限。虚可使范围至广至大,从庄子到水墨画都是这样。
记者:你以迹象论来探究现代绘画的表现特征,如谈到莫奈的迹重于象,波洛克的迹就是象,塔皮埃斯的迹象泛化等问题时,有自出机杼的妙论。迹象在转换之际,又可进入到各种当代艺术现象的解释中。这样,整个现当代艺术的演变规律因之可以一目了然。如果用迹象论来品评一件作品,具体到一幅吴冠中先生的作品,你会如何来分析呢?
钟孺乾:关于迹象观的变异和拓展我花了很多功夫,从原始到古典的迹象观,从文人画的迹象观到印象派的迹象观,印象派以来从破坏到兼容的迹象观,我探讨了整个人类艺术迹象活动的变迁。在书的开篇我谈到,艺术中最重要的就是x,即我们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所有想要表述的意图都有与之相配套的迹象。像吴冠中的作品就是忽略了传统的笔墨,而采用了新的造迹方法。它更能代表我们当代人的思想方式,给未来的探索带来新的方法。将来如何去评价这些迹象还需要时间的沉淀,但是它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吴先生的这种迹象不是无缘无故就出现的,也不同于没有笔墨意趣的钢笔画,我们的民窑瓷器上面有很多这种无变化但非常流畅的痕迹存在。还有一位是刘国松,他创造的迹象是对于毛笔的一种革命,抛弃了笔墨。他要画宇宙,画星云,如果用传统笔墨来画是表达不出来的,非如此不能表达他内心的意愿。我在书中谈到文人画时,重点谈的是米芾。他是一位了不起的画家,过去的理论家谈到一定程度就没法深入下去了。但用“迹象论”来分析就可以继续深入进去探讨,“米点”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到了米芾这个时期就变了呢?米芾是技艺高超的画家,他用单纯的点迹就在绘画史上自成一格。对于他的点迹的专业化特点我也在书中进行了描述,为什么“米点”能够在水墨画中成立?因为他用了特殊的工具和材料,还用了莲房、甘蔗皮。别的艺术家可能就没有办法应用这些东西,他为什么能运用这些材料到创作中去?我在书中都做了分析,他的迹象类型不同。他有了成体系的方式,他的造迹象的方式同他要表达的对象是一体的,同表达的境界完全联系到一起了,我用了“迹象软件”一词来形容他的体系。所谓的“软件”就是已经成为一种程式,已经设计成了一种配套的体系了,要形成特殊的风格就要有一套特殊的“迹象软件”。
记者:你在中央美院的讲座中谈及齐白石“似与不似”与黄宾虹“借象生迹”之间的对比,给我很深的印象。他们的作品虽各有特点,但用传统品鉴方式来比较还真难一言以蔽之。
钟孺乾:我在比较他们二人的作品特点时也感觉到,他们一个注重象,一个注重迹;一个注重象的变化,一个注重迹的叠加,十分有趣,从中能够看出他们对于艺术的不同理解。
记者:你在“迹象论”里对许多传统的概念进行了新的诠释,如再释六法,讨论十八描的真相,探究点、皴、焦墨等的迹象关系,都很有意思。又以“迹象”置换“笔墨”,骁纯先生甚至说迹象论就是笔墨论的现代蜕变,并认为笔墨的世纪论辩,在这本书里才“真正结出了新的果实”。
钟孺乾:笔墨是中国画一种最典型的迹象,我在书中称之为“特殊的迹象和迹象生成方式”。对于笔墨之所以特殊的原因也从四、五个方面进行了解释。它的特殊性在于,写意画虽然每一笔都很简单,但是同文字的历史联系起来,文字又同书法联系起来,书法又同文学联系起来,文学又同哲学联系起来,它们都是相关的,所以说“一笔五千年”。每次深圳举办水墨双年展时也邀请欧洲人参加,他们画的水墨画表面看没有大的区别,但仔细分析迹象时差别是很大的。他们对于水墨迹象的理解同中国人不同,所以每一笔迹象包含的文化含量和精神内涵也不同。笔墨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带有我们民族文化内涵的迹和象。而且它可以继续向前发展,我在书中也说到水墨画不是从唐朝开始的,而是从更早的时候就有了,彩陶时代的一条鱼就是大写意的作品,那时既没有庄子也没有唐朝的绘画大师。这个基因已经很早就埋藏在中国人的血液中了,笔墨只能称为艺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记者:还有你提到一个很独特的“体”的观念,谈到传统迹象品鉴中的拟人化倾向,这与西方的审美意念是很不相同的,如书法中有颜体、柳体之说,画论中有“看画如看美人”之说。
钟孺乾:我曾经写过文章,认为这么一个有着鲜明特点的审美意识,怎么没有人重视呢?我所提出的“体”观念应该是书画鉴赏中的一种表述方式和思维方式。比如说中国传统画论是非常讲究语言的格致的,很多和艺术的形成过程有关系的词语都同“体”有关系,像体验、体察、体味等等。中国的艺术风格就被叫做“体”。我以前查过的资料中有文章称“艺术的起源与人的起源同步”,但是分析得不彻底,有学者提到人类制造第一件工具的同时,艺术就产生了。我的看法是人类“随手造迹”的历史要比制造工具的历史早得多。很多中国的古籍就充分表达了人类造迹的激情,“苍颉造字”和“伏羲画八卦”的神话传说都是深受“迹”的影响。实际上远古人类在没有工具时就在到处造迹,他们用手指在地上划出痕迹,他们的足迹随着他们的行动而到处留存。所以“伏曦画八卦”的神话传说也有合理的地方。伏羲在观察鸟的足迹和自己的脚印的过程中就象征了人类迹象意识的苏醒,对造出的痕迹进行比较那就是最早的“艺术批评”了。我们每个人都热衷于造迹,小孩儿天生也是喜欢造迹,这都是有道理的。那么造迹也要有个好坏之分哪,这就有了“体”的观念,“体”的标准。这种理论看似微不足道,但已渗透到自古及今的品评方式中了,如对某件作品不满意就会说,“不好,画得太肉,没骨头”,如果一笔失败就说好比“壮士折肱”。古人说“一人之身,情致蕴于内,姿媚见于外,不可无也。作书亦然”,似乎玄奥,其实是最简单、直白的评价方式。可以上通下达,既是高深的理论,又有通俗的表达方式。
记者:这本书,你说是把积压许多年的话说了,感触最深的是什么?作为一种基础理论,你认为迹象论能为绘画实践带来什么,为具体的艺术教学带来什么呢?
钟孺乾:有人说我的迹象论内容庞杂,覆盖面广,其实这也是它之所以能成为基础理论的一个必备条件。迹象论既然是视觉艺术的基础理论,它就要在艺术的根基上发挥影响。我给学生们开的现代重彩课和书法课,就是以“迹象论”为基础的。用迹象论来释疑解惑,指导习作和创作,学生容易领会。此书是在我女儿准备高考期间撰写的,我同时用迹象论的原理引导她理解绘画的基本知识,提高非常快。我可以把难以理解的抽象的理论分解为具体的迹和象,给习作挑毛病就像给人体做病理分析。如果“象”表达得不到位,那就要提示写实造象的具体规则;“象”没问题,“迹”却杂乱无章也同样是毛病。用什么样的迹表达什么样的象,迹与迹之间的关系如何?甚至用什么样的“排线”?是用橡皮擦还是用手揉?而这些不同的迹又是怎样对应着不同的造象要求,如体积,空间、明暗?这些有如何达成了对象的神情、画面的美感?等等。这也就是“迹+象+X”。印象深,好懂。我的这本书中较少涉及艺术设计,其实设计专业的学生理解迹象论更加直接和便当,因为设计中的迹象元素更明显,规律性更强。要构成一个有个性的象,应该采用什么样的迹,迹与迹、迹与象如何组合,迹象结果如何与所要表达的X相契合,都要仔细推敲。设计者在构思和制作中把心力集中到迹和象两个元素上面去,认识起来就非常方便。
【编辑:李洪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