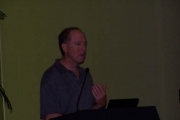研讨会现场
时间:2013年6月22日16:00
地点:北京前波画廊
艺术家:蔡锦
学术主持:贾方舟
研讨会嘉宾:高岭、高名潞、贾方舟、刘礼宾、刘骁纯、陶咏白、王端廷、徐虹、杨卫、
殷双喜、朱其、茅为清、蔡锦
贾方舟:我认识蔡锦是在上世纪90年代,1994年中国美术批评家提名展(油画部分)在讨论提名艺术家的时候,栗宪庭提出了蔡锦,之后她便是20多个被提名的油画家之一。后来,我在1995年和1998年策划的两个女性艺术展上,也都邀请了蔡锦参加。
蔡锦在中央美院进修的两年中,预示出多个发展方向,但是最后她选择画《美人蕉》。画美人蕉其实是借题发挥,借助于美人蕉这样的生命体以表达自我内心的一种生命体验,所以在这样的对象身上,投射了自己的影子,找到了适合于自己的表达方式,也找到了自己情感的载体,所以从这个领域里走过来,我们今天看到她的作品都可以跟她早期的作品联系在一起,因为她用的语言没有变,只是图式变了。变的抽象了。但这些作品很明显是在原有的美人蕉的细节上一步一步升发出来,最后离开美人蕉这一意象,保留她习惯使用的语言要素。蔡锦最近几年的新作显示出她在向新的高度突破,我想今天大家坐在一起讨论这些作品,都会找到各自的话题。
陶咏白眼中的蔡锦--女性的艺术
陶咏白:蔡锦是才女,在我国历史上绘画的才女不少,尤其是民国时期,出现一批出国留学以后回来的女画家,她们跟男性艺术家的艺术,在同一个水平上,有的甚至超过男生,比如潘玉良色彩,比男画家的色彩感觉好,在那个时期,油画色彩很贫乏,素描加色彩,缺少色彩感。而潘玉良对印象派的色彩把握得到位,色彩非常漂亮。当时留学归国的秦宣夫(油画家、美术史论家)对我说:潘玉良是中国“印象派第一人!”但因她曾为妓、为妾卑贱的身份,无法在国内生存,为了人的尊严,背井离乡,客死它乡。当时还有很多女艺术家,很有才华,但结婚生子后,杂务缠身,又由于经济的不独立,只能成为相夫教子的家庭妇女,就不再画画了。坚持下来的很稀少,真是可惜了。今天的蔡锦,经历了人生种种磨难,没有消沉,在艺术中消解了自已的哀伤,用艺术疗伤,在艺术上能日益精进,不断有新的面貌让人耳目一新,给人惊喜。从去年的黑色美人蕉以那雕塑样厚重和张力,那是对顽强的生命颂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当人们还沉浸在那崇高的生命精神感动中时,今天她又让人从她画的一滴水渍、一粒尘埃的微观世界,引向浩瀚无垠的宇宙,望星空,向海洋,放眼世界,投身于宇宙怀抱中而获得“生命不息”一种感奋。蔡锦终于走出了生命中的阴影,坚持不懈地创造着生命的奇迹。
蔡锦从《美人蕉》到《溯源》,是个飞跃,是在思想,艺术观上的飞跃。她从一种物象,一个植物形态,到无所指的一个点或者一滴水发展成一望无边的海洋,从尘埃变成一片灿烂的星空,她的心是开放的,是向着光明,广阔的天地。这些画,从无到有,就像在显微镜底下看到的微生物,让人从中看到了生命的源泉,看到了万物之源。她画的这些东西,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但人们看不到,或并不会注意。但她看到了,把它发展了,发挥了。把这样细小的东西发展到这么广阔的绘画,这源于人的经验的生命体验,但她却引发成为一种诗性的或者说是神性的生命体验,从中能有一种新的发现,幻想出新东西表现出来。所以艺术家和凡人的区别就是在对生命体验上的不同,一般人看到什么就是什么,这是经验的生命体验,只有艺术家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或想不到的东西。什么是神性的生命体验。爱因斯坦在他的《我的世界观》中说:“我们所能最美好的经验是神秘的体验。它是坚守在真正艺术和真正科学发源地上的基本感情。谁要是体验不到它,他就无已于行尸走尽。……”这个话对我们艺术家来说特别的重要,在这种神性的生命体验中,具有强烈的感受性,广阔的想象性,是一种超知性,超见解、超本质的不可言说的神秘洞见。蔡锦从一滴水渍中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小的时候看到有些水印可以想像出很多故事来,但是我们就没有她这样艺术家的思维去发展,去表现。我最近看到记录片《走进霍金的宇宙世界》,霍金是个“渐冻人”,都病得这样了,但他却还在享受着他对宇宙神奇的幻想,只有具有这样神性生命体验的人才会有这样异想天开的想象和发现,引领人们不断地去探索,创造,推进世界的前进。在蔡锦的绘画里充分体现了她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神性的生命体验。
从蔡锦的画,我想谈谈女性在绘画上有意思的地方。第一,一般画画都要先从整体结构,布局考虑,先画个整体结构布局的草图什么。而蔡锦的画是从一点、一个局部画起。然后逐渐画开去,直至完成整幅画。徐晓燕也是这样。她们竟能这么由一点开始画出宏大的场面来,从局部发展宏大,她们是以什么方法掌控画面的?这么宏大的场面,对于许多画家来说不知事先要画多少草图,理性地规划布局。而女画家却总是随着感觉走,一点一点向外、向面扩展繁衍。保持着感性的鲜活和灵动。这理性的构成与感性的抒写性这是两种创作方法,很值得研究探讨。第二,女性善于从小处着眼,从日常生活中去发现美,画花花草草是她们的长项。但也有别人看不到想不到的地方作为绘画题材,徐晓燕可以把垃圾入画,揭示了触目惊心的生态大问题;蔡锦从一点水渍来抒写着宇宙天地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她们从小处着眼,却怀着一个大襟怀。第三,有人说:男性在创作中重在结果,成就、成功。而女性创作则重在过程的享受,并不在乎成功与否,陶醉于一点,一点的发展,注入有情有调的生命感受,有点自得其乐而已。也许古时妇女纺线织布,后来织毛衣等世世代代积淀的心理素质。养成在这里蔡锦作画的过程中验证了女性的这个特点。我不知道我的这些发现、思考是否有道理,有研究价值。
贾方舟:陶咏白发言,是将蔡锦作为一个女性艺术家的角度,对她的作品做了一些分析,我觉得分析的比较到位。陶咏白一直研究女性艺术,对蔡锦的作品有她自己的视角,即从性别角度,不同性别的艺术家,在对艺术的处理上,语言表现上都各有不同。她的画确实让人感觉到不是先构成的和预先设计的,或者说有过大的构想的。她的画完全是繁殖性的,像一个生命体在不断的繁衍,又像是织地毯一样,由上而下,一点一点直到把它织完。蔡锦画画就是这样的感觉,这应该是和性别有关,特别的感性。接下来徐虹接着说一下!
研讨会现场
徐虹:蔡锦的绘画开始于一个美丽的故事
徐虹:蔡锦的绘画开始于一个美丽的故事,小的时候安徽家乡老墙壁上的水渍,水渍的不断盛开充满了蔡锦自己的想象和感情投射。当然我想,这种关于艺术的开始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源头。比如我们看到天上的一块云朵,就想象有神在上面、耶稣基督在上面、丰硕的女神和战马战车在上面。我想很多艺术的起源都源于生活中的一些非常平易的小事,艺术家在这样的小事中赋予自己的感情和发挥想象力,于是这个故事就开始生长了,生长为一个美丽的传说,生长为一个大艺术家的作品,生长为哲学家的巨篇鸿字。就因为有个人的感情和思想的投入,所以任何故事的开头可能是同样的,就像生命的开始是同样的,但是过程和结局是不一样的。因为过程和结局里有大量的个人生活的经历,有社会、时代、经济、政治,或者是有他个人文化的传统,所以在这里我还是愿意从意象开始说起,因为谈艺术家的作品,首先得谈意象,谈艺术作品不谈意象我觉得没法谈。我觉得蔡锦的作品有一个强烈鲜明的意向——美人。尽管唐冠科先生给你写的文章不承认女性主义这个提法,当然他承认不承认是他的事,至于人们愿意不愿意用女性主义的方法来评说你的作品另外一回事,包括你自己也可以说我不是女性画家,但批评家完全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来讨论。
美人,第一是美人蕉,这个是很浅显的生命怒放,随着腐朽和生命的怒放混杂在一起,一种矛盾,一种挣扎,一种纠结。第二部分我在德国看你的展览:大沙发上铺满血水,女人的小脚尖头鞋里布满了鲜花,对吧,继续是美人。美人在生活中的遭遇,美人的文化和审美的意象,和实际生活中的残酷和现实结合在一起,就像神圣的乌龟在泥里摇着尾巴一样,虽然乌龟很神圣,但是泥里就是泥水。最后是现在,我看到了结果。什么是结果?洒落的鲜花,干瘪的果子,果子是枯萎的,干瘪的,生命力虽然内涵在其中,但是外表看上去是枯萎的。所以你的作品体现了中国当代艺术的一种现代性现象,为什么?现代性就是一种分裂,就是一种个体的主体的突出,是一种反思,和一种审美的判断。当然这种分裂这种反思,必须强调要和主体的分裂抗争,主体在反思中不存在,但是主体还要努力的存在,所以在你的作品里我看到这样的不确定性,目的的游离性,努力的挣扎,努力的纠结。在这里我还是看到了你的一种努力,不管你有意识,还是无意识,这种当代性所强调的包容,强调的多层的视角,以及强调自己个体的生命力的经验,生命的经验,和文化的意象之间如何的穿插和共存,这一点是我看到的,这个大概就是中国艺术家最有希望走的一条路。
传统的文化的符号并不是直接的挪用,必然是通过艺术家的个体的生命经验和它的文化的思考和批判,经过转换以后的一种“挪用”。所以我说美人意象在中国文化里很显明,文人们的怀才不遇,文人们突然得到皇帝的赏识了又高兴起来了,文人们还有美人迟暮。中国的文化里美人是一种文化意象,是一种审美态度,是用审美的立场和姿态来叙述自己现实中的遭遇,现实中各种实际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美人的运用,实际上是在你的作品里有更大的一种含义,就是说传统中国的美人和传统文人的生命体验,和传统文人个人的际遇是有关的,它里面涵盖了各种心境,涵盖他现实的处境,也有他的理想,也有他的感慨。所以我觉得美人这个意象在当代如何能够深化和进一步的运用,确实也是一个方面。我觉得在你的作品里面这种意向就是被现代性给抓住了,而且给放大了,就是说本来在中国文化中美人意向就是矛盾的,明明是男人说自己是女人,明明是现实生活非常残酷激烈的竞争导致他的失落,但是他偏偏要说用风花雪月、轻描淡写、非常抒情的去说,“美人”这个词中国文人用的时候已经充满了纠结和矛盾,它表达了人性的一种复杂和对生命的体验和看法,但是如何用到当代文化里,现代性里就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全世界大概只有中国才是这样,我也不知道其他东方民族是不是把美人用成男人,我不知道,当然因为中国的道家文化里面、哲学里面讲究阴柔,把整个哲学基点放在女性生理的基础上,这个是中国文化非常特有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文化意向中,蔡锦恰恰是女性身份,她是以女性自己对自己生命的观察和反思,使她选择了美人这个意象。当然这个美人和传统的柔弱的美人不一样,首先看那个美人蕉,是那么的饱满,她是以审美的姿态来观看和表达人生中的愁容,她的美人蕉不美,有一个评论家看到美人蕉说我快晕过去了,它不美,它太强有力了、太血性了、太刺激了。包括你的装置作品,那么漂亮的绣花鞋,但是把血淋淋的美人蕉画在里钉在墙上的时候,它实际上充满了一种很尖锐的讽刺感,也不美。包括现在散落的花和果子,看上去粉色的很漂亮,但是你仔细看,难道它不就是霉菌传染,难道它不就是病毒体,难道它不是长着刺的各种不让人喜欢的植物的种子吗?包括那些梨子都是不美。所以蔡锦转换美人的意向,使美人不美,还要用审美的姿态来说美人不美的故事,这个就是当代的文化的表达。作为女性是非常敏感的抓住了用美人不美,用美的方法来表达不美,或者用不美的办法来表达美,这就是一种颠倒和重叠和交错和陌生化的对文化艺术的选择和表达,在这里我觉得你做得很成功。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蔡锦在使美人意象陌生化,把传统文化中的美人回归到美人,回归到女性。传统文化中的美人,经常把自己作为志向很远大、品行很高级的文士。但是蔡锦的美人让她回到了女性,这个女性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柔弱的美人,而是充满着生命活力,能面对现实各种困境,把现实的愁容揭示出来的当代美人,回归到原始的女性形象,大地女神,天上的女神,也可以是战神,也可以是破坏一切,把男人的头砍下来放在盘子里的恶美人都可以。这样的美人是充满着生命力,具有丰富的文化意味,有很多文化故事这样的美人,用这个办法来做。
第二个就是原始的经验生命的转换。虽然你看到的在你家里墙壁上的水迹,这个水迹慢慢的生发,但你对这个水迹的关注投射你的感情和你的故事,从这个开始我们又回到原始的审美状态,或者原始艺术发生状态,就是艺术是什么?作为女性,她长期地和日常的最具体的生活结合,在具体的生活里她注入自己的艺术想象,然后这个原始的、不美的、或者是丑陋的、带一点腐烂这个痕迹开出一朵最美的花,谢谢!
贾方舟:徐虹又深入了一层,她们两位都是从性别的角度来分析、判断蔡锦的作品,但是各有自己的视角,我觉得徐虹谈得特别好的一点是使用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美人,一个是审美。画家在这两者之间是纠结的,美人是不美的,和作为男性艺术家的表达完全不一样。我在1995年写过一篇文章,曾分析过蔡锦当时利用床垫,鞋子,自行车座所做的作品,全是画在床垫上,画在自行车座上,画在鞋里,这样的载体都是一种被欺负的意象,被踩,被坐,被躺,被压,所呈现的都是这样的意象,为什么画在这样的材料上,而不是别的上面,我就觉她在无意识中表达的完全是一种女性主义诉求,当然我不认为蔡锦是女性主义者,但在她的潜意识里恰恰表达是女性主义的内涵。接下来听一听男批评家从另外的角度分析蔡锦。
朱其--男性艺术家眼中的蔡锦
朱其:不太愿意用当代艺术这个词,因为你一说到当代艺术,好像又是顺着西方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然后到八十年代后的当代艺术,又是变成这样一个脉络了。实际上,这个时期的艺术还是有必要重返现代性的。刚才徐虹谈到现代性美学的问题。实际上,我们从民国,三四十年代开始了一些现代性,49年到文革有一些中断,然后,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就真正开始了一种现代性的美学。比如,蔡锦的画,她美人蕉的形象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一种血污的美学,类似于女性的经血的一种东西,包括她这次的新画,更像把一种女性的污血的感觉变成一种诗学的语言。以前可能它与装置、美人蕉的形象结合,借助于这个载体来呈现。那么,到了今天她可能完全可以抛弃这些载体了。然后,她把一种污血的美学给非常语言化了。而且,尤其像这次展出的绘画,绘画的本体语言特别强烈。
所谓的现代主义美学是什么?我觉得它就是表达一种自我分裂、变态、受虐,甚至带有一种脏兮兮的感觉,像培根的绘画。那么,其实我们这几十年更多的还是关注美国的艺术。但是,最近这些年我更关注英国的一些人物画,比如斯潘塞、培根、佛洛依德,英国这种老式的现代主义它外表是很优雅的,但是,内心可能非常变态,甚至有一种优雅又脏兮兮的感觉。可能是年龄的关系,不知为什么就偏好上这种东西了。
在中国,93年以后走向国际对话,然后中国又进入了消费社会。好像大家认为艺术在中国应该进入后现代主义,或者完全时尚化的当代艺术。但是,我觉得中国的这种语境还不完全是西方意义的后现代主义或者全球化的消费社会。其实,只要一党制还存在,中国可能就没有走出现代性。那么,我们今天的语境其实还保留了从英国圈地运动一直到四十年代存在主义这一时期的语境特点。和它相比,我们中国目前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的圈地运动比英国的更疯狂,我们今天的这个人格分裂比佛洛依德提出这个理论的那个时期更分裂。我们目前的这种虚无主义比萨特四五十年代提出虚无主义更加虚无主义。实际上,我们今天依然笼罩在现代主义的语境。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反现代性,在中国讨论现代性依然有它的精神价值。这是艺术判断的一个维度。
另一个维度是:最近,我感觉对于花卉这个题材,女的确实比男的画的好。我最近还发现一位吴冠中48年留法时期的一个同学叫刘志明。她49年后就在云南画院,画了六十年。老太太现在还活着,已经八十多岁了。她完全比吴冠中还要好好几倍,但是她的画在外界很少能看到,我前两个月去拜访过她。她的瓶花画的非常好,可以说他完全消化了后期印象派以后对花这种植物的表达。甚至,叫她中国的女梵高都是可以的。她八月份在云南博物馆有一次她的回顾展,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觉得,刘志明老太太解决了花卉题材后期印象派的一个阶段,可以说她代表了中国在这一块最高的一个阶段。那么,我看到花卉题材的绘画,除了刘志明老太太就是蔡锦。蔡锦她已经越过了后印象派这一阶段,花卉题材到了今天,到了蔡锦的手里已经完成了,而且完成的非常好。而且,花卉题材在中国自古就是个经典的题材,山水花鸟。那么,如何让花卉题材绘画具有现代性,蔡锦已经给出了答案。很难想象用宣纸画出蔡锦的这种感觉,它是达不到的,包括中国画的颜料也是达不到的。必须要用麻布、油画、丙烯之类的这种材料。其实,虽然她运用的是西方的绘画材料,但是在绘画的感觉上还是有中国写意或者诗性的东西。她的诗性其实为她注入了一种不再借助物象,尤其是画到今天这一批,直接以血污本身的一种形式主义,或者纯粹从色彩本身体现一种女性的非常复杂的一种经验,这一点实际上已经到了一种出类拔萃的地步。我是看过很多植物花卉的绘画,蔡锦把现代主义的表达在花卉这个题材上已经做的比较彻底。
贾方舟:朱其的发言很好,我在这里看不出男性批评家和女性批评家的对抗性因素,朱其也提供了一种解读,“血污美学”和刚才徐虹说到的审美和美人,美人不美有相近之处,“血污”这个经验的表达,实际上是女性独有的,恐怕这个主题男人是画不出来也不肖去画的,我们也可以看到男人画花,但是完全不一样,那种对花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女人画美人和男人画美人也不一样,女人画美人不会像男人画的那么美,不会作为客体去欣赏,而是当作自我的一种表达,向京半生中创作的所有关于女性的形象没有一个男人会喜欢,这就说明了女人眼中的女性形象,其实不是要表达美,而是要表达他们的生存经历,他们的尴尬,痛苦,表达精神上的困境,所以蔡锦虽然画的是花,但主题并不在表达花的美。朱其第一肯定女人画的花比男人画的好,第二肯定蔡锦画的花已经画到出类拔萃的地步,超越后现代,走向完成。
高名潞:蔡锦--不善于表达的艺术家
高名潞:去年在中国美术馆蔡锦已经做过一个展览,在座的很多人都一起谈过,聊过。这次蔡锦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做出来新的作品,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原作。蔡锦这个人有故事,就如刚才徐虹所说,但是她自己又不会讲故事,有话说不出来,人很朴实,却非常执着,爱较劲。画画,搞艺术,创作也是这样。
我第一次接触蔡锦是在美国,在徐冰家里,我记得是九几年,第一次看到她,蔡锦也没说什么话,打了一个招呼,也没什么交流,做了一点面条,因为我那个时候在那边好多年经常吃方便面,快餐,一吃这面条是真好吃。再有就是1998年纽约INSIDE OUT展览的时候,蔡锦帮助徐冰张罗布展。有时候徐冰忙别处的时候,蔡锦要按徐冰的要求把位置严格划分好,墙改成灰的,白的,再到黑的等。徐冰非常的严格,所以一开始蔡锦就跟着我,非催得让工人马上来,我当时觉得蔡锦这个人怎么这么爱唠叨那么执着。
那个时候蔡锦也没有参加这个展览,我记得大会上,开研讨会的时候,有听众问,INSIDE OUT展览有那么多艺术家,女性艺术家有几个?我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后来仔细一算是六个:肖鲁,尹秀珍,林天苗,台湾两个,香港一个。观众当时很不满意,为什么女性艺术家才六个。那个时候我知道对国内的女性艺术讨论非常热烈,老贾,陶先生,徐虹都是专家,而且做过展览。我那个时候听说过蔡锦,但是不太了解,也不敢邀请蔡锦,这些就是我对蔡锦的印象。
蔡锦的美人蕉到现在我觉得其中的故事性,如果用学术一点的词就是“叙事性”越来越少了。其实也不能说少,我倒是觉得蔡锦在她最近的这批画当中体现得更丰富了,我把这种丰富理解为一种不似之事,很难说清楚具体是什么东西。你也可以自己给它命名为什么东西。例如刚才朱其说蔡锦作品从美人蕉到现在,血的感觉;或者说是并非单纯的风景——心灵风景;或者意向你都可以去说。我看对面的这件作品,你看那些具体的霉菌的形象很难讲是什么,但是我们阅读的人完全可以通过想象,通过个人的经验去给它一个界定,甚至我从这个画当中感触到五代画家黄筌的《写生珍禽图》。它非常的散,就如《芥子园画谱》中非常不一样的石头,植物,树等。再看画册中的这张作品,深度非常惟妙惟肖,空间很难以3D界定。它的边框没有限制,包括这个形象本身不具体,它是现实当中的什么样的一个东西也不具体。朱其也提到了这个。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无尽的,不是取景画,也不是抽象绘画平面性,它也不是古典绘画,这里有传统的一些因素,但是我不知道蔡锦在这方面创作的时候有没有去思考,也许是凭直觉感受。
我看蔡锦的画给人感觉很难非得要用女性艺术家界定它,这样更好,我觉得蔡锦这个画很难讲纯粹的就是女性绘画,我觉得实际上更开放,而且不是看上去是女性艺术家的,女性艺术,我认为更加深厚,更加有价值的,女性艺术家,就像男人和女人,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贾方舟:高名潞在分析蔡锦作品的时候有一个问题谈的挺好,蔡锦的画是无结构的画面,没有结构性,就是散点的,随便画,既不是平面的,也不是三维立体的,但还有一种空间感,这个分析还是挺好的。有一定的空间性,就像在空间中漂浮,或者在海洋里的浮游物这样的状态,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
谈到女性主义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这个讨论已经超越艺术家个人的作品上升到理论问题了。刚才朱其也谈到不喜欢“女性主义”这个概念,他用“阴性美学”来取代。高名潞谈到非洲的一个批评家提出的“女子主义”,或者“女人主义”,这个都是觉得女性主义这样的一个概念不是很理想。但是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把这个概念看得很严重,我赞成这样的观念: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是同一个外来语,有一种说法女权主义是女性主义的早期阶段,女性主义在早期是争取权利,就是所谓平权。因为她没有权利,没有和男人同等的权利,在西方甚至学习权利都没有,上了美术学院没有写生模特权利,确实有很多限制,诺克林《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这篇文章,就是谈这个背景,女人不能和男人平等的接受教育,在这个意义上争取权利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到后期阶段女性有了一些基本的权利以后,强调的是女性自身的特性,强调的是性别差异。女子主义更普世些,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我们可以站在任何角度去解读蔡锦。
殷双喜:蔡锦作品中的女性主义
殷双喜:去年在中国美术馆高名潞主持了一个蔡锦展览的研讨会,那个时候我非常高兴地看到蔡锦的作品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原来形象化、整体化、团块化的构造越来越碎片化了,有一种漂浮感。这次看到蔡锦今年的新画表达的更加鲜明强烈。蔡锦画面上的这种感觉是现代女画家中比较少见的,呈现出像宇宙一样的比较深邃的空间感,这种感觉是她心灵的宇宙感。她不会去研究天文学等知识性的东西。蔡锦画中的空间漂浮状态,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她的画,既不是花卉,也不是静物,也不是风景,如果一定说是风景的话是心灵的风景。所以这个画面里没有起点和终点,没有中心和边缘,当然也没有结局和结果。我看她的创作照片和朝戈有点像,在画面上不需要打底稿,从任何一点都可以开始画,然后就是蔓延,迷茫状态的推进,直到把这个画布一点点渗透,或者笔墨的渍染一点点把画布浸满。这个很像生物菌类生长的过程,如果用一块奶酪培养霉菌,霉菌会把奶酪都占满了,这是不可预料也不可控的。但是作为蔡锦来说能够内控,这是她几十年的职业性的内在经验在控制。她不是“素人画家”,我们的素人画家也很少,民间艺术家的大脑也不是一张白纸。所谓的民间画家,受到童年记忆的影响,那里有民间美术的记忆。真正的纯粹绘画就是儿童没有学习之前没有信息输入之前,能够自发地去描画。这次看到蔡锦女儿的水墨画我觉得有生动的部分,但是也看出系统的水墨训练,里面有技术性的惯例,只不过孩子的天性压过了这个套路。而大多 数儿童画的水墨画,就是套路压住了天性。蔡锦到现在为止,没有展现她非常熟练的技术性套路,我觉得这一点是可贵的。
对蔡锦来说,这个社会有那么多的油画家,而她能够走到今天,持续地创作并且被关注,一定有她自己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她的执着,这个执着还包含她特有的灵感,这就形成蔡锦作品中的品质感。真正的收藏家,懂绘画的,知道欣赏的,专业画家,能够对貌似相近的东西品评出其中品质的差异,所以“品”有三个口,并不是品三次,或者三张嘴,在中国美学是反复鉴赏把玩的意思,只有在持续的重复的鉴赏过程中才能够把握艺术品那种独特的味道。所以说这个品质感作为鉴赏家和批评家的核心能力,我们会说某个人眼特别“贼”,一眼看到深处,这个是长期的积累,蔡锦作品中的品质感是长期的执着表达的过程。蔡锦最近的作品反映中国绘画的某种现代转型,它不像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美术,有强烈的社会性,甚至某种政治的对抗性,蔡锦的绘画是去对抗性的,或者叫做去文学性,我还觉得蔡锦画去性别化,因为过去女画家画花,是因为花作为植物的生殖器官,女性爱画花反映了她们对生命的感悟,甚至是描绘残花,也表达了生命的短暂性。男性画家也画花,他们是作为一个载体去研究色彩的表达,与画风景并无太多区别,并不刻意强调花所暗含的性的意味。蔡锦作品的漂浮感,恰恰是今天这个社会在价值观方面的漂浮感,有一种“失重”的感觉,失去了某些对我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东西。过去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给你一个基底你稳稳的站在那个上面,当然那个上面是可以倒塌的。但是这个框架倒塌以后,整个社会价值多元的时候,却导致了相当程度的价值虚无。在这个意义上,蔡锦也不是形式主义的抽象画,如果是形式主义的抽象画,就不会在今天有这么多人的共鸣,因为形式是很深奥的,只有少数人有形式主义的敏感。蔡锦和我们现在所谓的观念性画家的区别,一类画家画出自己对生命的感受,一类画家画出对生命的解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知识型画家和感觉型画家,蔡锦是比较纯粹的感觉型画家。蔡锦的作品可以移动观看,在这个过程当中观众可以由小到大,从不同距离和角度去品位,比如蔡锦以素描方式画的梨,梨远看就是写生,可以到近处看,逐渐的镜头推进,也可以做成三维的,我们的视线完全可以从外面一直进去,进到那个线条缠绕的内部空间,从个体的梨变到无限的空间,这个感觉特别的令人惊异。
蔡锦的一些作品如果把签名去掉,倒过来挂会怎么样?如果倒过来挂,这个画的空间感和重心感会有特殊的味道。或者可以尝试把画布放在地上画,不一定靠在墙上。如果平面上转着画,各位说的水的感觉、漂浮的感觉可能会更强。今天有许多绘画,手和心的关系被人为的割裂了,过去是被政治性的解释割裂了,现在被大而无当的观念割裂了,我们看画家的画失去了对画本身的品味的可能性,就像今天的很多使用添加剂人工培养的食品,今天的黄瓜、番茄、辣椒到嘴里没有味,木木的,看着那么大,那么新鲜,特别像工艺品,嚼到嘴里没有物种自身特有的味,这个味道失去了。今天很多画家不能叫画家,实际上是制作家。许多画不是发自内心地画出来的,而是有计划、有预谋、有套路地制作出来的。
贾方舟:我们的讨论越来越有一种深度,每个人从各自的角度来阐释蔡锦的艺术,每个批评家都有自己的视角,都有自己对作品的感悟和认识。刚才双喜说,从前后的发言来看,他是进一步阐发了类似高名潞的感觉,他的感觉是漂浮感,深邃的宇宙空间的深度,这个又进一步深化了,既不是花卉,也不是风景,到底是什么?无法界定,从题材上无法界定,无限的外延弥漫,不可控制,没有尽头,失控感等等这些描述和感触,加起来很能够说明蔡锦的作品在境界上的开拓。
王端廷:蔡锦绘画--一种新语言的转型
王端廷: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我们举办了好几个女艺术家的个人展览和群展,开了好几次研讨会,就当代中国女艺术发展的历史及其成就做了比较充分的梳理和阐述。我在那些研讨会上我也分析过中国和西方女艺术发展历程的差异性和相似性,我今天就不再重复这些内容。
我这里只想谈一谈对蔡锦绘画的个人认识。我对蔡锦绘画的最初了解也是在1994年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油画批评家提名展上,那次蔡锦的绘画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她画的是“美人蕉”,而且把美人蕉画得铺天盖地、极具视觉冲击力,从此蔡锦这个名字和她的绘画就铭刻在我的脑海里。今天我们看到的绘画,是她从“美人蕉”系列转型后的新作品。她的创作转到新的题材和新的语言,这表明蔡锦的绘画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女艺术批评家琳达·洛克林发表过一篇文章《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引起了西方学术界对女性艺术家的极大关注。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和女性主义运动的出现,到20世纪90年代,西方艺术界出现了一大批非常有成就、可以和男性艺术家分庭抗礼的女艺术家。其实,中国艺术史上也是在同一时期,亦即从蔡锦这一代艺术家出现以后,才开始出现杰出的女艺术家,包括蔡锦、喻虹、林天苗和向京在内一批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生,20世纪90年代走上艺术创造道路的女艺术家形成了群体的力量,带来了中国女性艺术的崛起,她们的创作使得女性艺术变成了中国当代艺术界难以回避的现象。蔡锦的“美人蕉”作品已经有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既体现在语言上也包括她的绘画题材,因为在此之前尽管中国也有女艺术家,但是那些女艺术家没有找到女性特有的、跟男性不同的、独立和独特的表达方式和言说主题,蔡锦这一代女艺术家找到了。也就是说,蔡锦这一代女艺术家用独特的语言表达了这个时代女性个人的独特经验,充分显示了女性的自觉意识,而在此之前女性艺术家被束缚在政治、伦理和道德等各种各样的社会学囚笼里。另外,艺术史从古典到现在、从后现代到当代以及从具象到抽象的发展演变,从某种意义上看,是人类对宇宙万物从表象到本质不断挖掘的过程。在我眼里,蔡锦的“美人蕉”作品属于“象征表现主义”风格,而在此之前中国女性艺术要么是写实的、要么是写意的、要么是工笔的,基本上可归于西方或中国古典主义的范畴。蔡锦的“美人蕉”绘画超越的对象本身,表达了对女性的隐喻,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美人蕉这种植物本身就具有女性的象征品格,而在蔡锦的绘画中,它的颜色就是女人经血的色彩,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一个女艺术家创作出这样的绘画。可以说,蔡锦的“美人蕉”绘画是独特题材和独特语言的结合。后来,她还把美人蕉绘画扩展到装置艺术,完成了包括浴缸、鞋和自行车座在内多样多种的装置作品,这都是现代艺术之后,后现代艺术的表达方式。不管形式和媒介如何变换,这些作品表达的都是象征和隐喻。毫无疑问,蔡锦的美人蕉系列绘画是她对中国女性艺术的一大贡献。
蔡锦把她的新作品起名叫“风景”,我觉得这类绘画的风格应该叫做“有机抽象表现主义”,因为画面中那些抽象的形式和色彩具有强烈的生命感,它们像菌类或苔藓在扩展在蔓延。蔡锦是用写实的手法来画抽象作品,画面上的每个细节都是精工细作绘制出来的。这些作品让人感到一种宁静的气氛,但是它们传达的信息却不是快乐、也不是欣喜,而是纠结和郁闷,这是一种糜烂的扩张,也是一种颓废的优雅。
蔡锦的这些绘画非常适合用格式塔心理学和精神心理学的方法和视角来解释和分析。刚才殷双喜先生说这些绘画可以倒着挂,我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我发现这些作品是不能倒着挂的,因为有它们有重心、有方向、有上下左右方位的确定性。实际上,这些作品就是树立着在画架上画出来的,如果倒着挂的话,视觉上会不舒服,感觉就不一样。我们中国很少有批评家采用精神分析学方法进行艺术批评,这也许与中国当代艺术界缺少这类创作有关。蔡锦的绘画非常适合用精神分析学的方法和视角进行深入的解读。蔡锦是一位把女性心理转化为视觉图像,并将女性特质发挥到极致的艺术家。我们用不着纠缠女性主义或者女权主义的概念,在我看来,一个画家如果把她心里的世界非常准确、非常完美地表达出来了,不管是男是女,都是优秀的艺术家。
贾方舟:到目前为止我认真听每一个人发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视角和解读的方法,端廷的的归纳是象征表现主义,有机的,他谈到用写生的手法画抽象,把女性的心里转化为视觉的图像,在这个意义上不一定谈是不是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就这个表达本身对蔡锦是非常重要的,用精神分析学的方法解释蔡锦很适合,但还没有一个人专门采用一种方法去深入研究某一个领域里的很个体的艺术家。
刘骁纯:蔡锦绘画艺术中的“笔墨”精神
刘骁纯:从小速写到人物到美人蕉到装置再到现在的“溯源”系列,蔡锦艺术的外在差异很大,但有一个东西前后一贯,对这个前后一贯东西,我想用“笔墨”这个概念来说,但是在油画里又不叫笔墨,油画里怎么规定这个概念?我曾用“笔触和肌理”,但太技术化,远不如水墨画中的“笔墨”二字为妙。我想了很长时间,找不到好的概括,先叫笔墨吧。
蔡锦心理结构似乎有一种十分女性化的纠结,因此对柔密的、细微的、扭动的、虬曲的、复杂的、斑驳的自然纹理十分敏感又十分迷醉,转而为艺,逐渐形成了她特有的“笔墨”——精微而虬曲的堆刮挑抹,郁结而带创伤感的油彩肌理。无论大的结构大的意象如何变,这种微观结构却始终一贯,诗意化的纠结,纠结化的诗意,在笔端以她那唯一的方式不断游走,不断生发,不断展开,不断升华,二十余年一贯。这种微观结构的美很像中国诗词的字链词链之美,一种与“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相通的美。
“笔墨”是蔡锦的命根子,是她最陶醉最关心的事。这种笔墨用于纠结的人物便有了蔡锦式的悲剧,用于纠结的红色芭蕉便有了溃烂的辉煌,用于纠结的黑色芭蕉便有了腐朽的刚强,“流”向地面便有了如玉的血腥……如今她抛弃了“应物象形”,让笔墨走出芭蕉的轮廓,更随意地在画布上自由运行,于是有了新的创作系列。
这个新系列她叫“溯源”,那源,大概就是心灵之源吧,回到心里去。心籁与天籁和鸣,心宇与广宇合一。
她的画中有形象,一种莫名其妙的形象,如霉如菌如虫如蛹如麻如丝如云如藻,但又什么都不是,只是运笔痕迹、心路痕迹,以及对痕迹进行的空间塑造和形体塑造。这么看,她的画就是抽象画,抽象写意油画,怎么非要说它不是抽象画呢?但是她的抽象画里有很强的意向性,而且是有东方特色的意向性。
她很强调走笔的随意性,因此没有预设的章法结构,画到哪算哪,这使高名潞联想到了黄筌《珍禽图》的无章法的章法,当代著名涂鸦艺术家汤步利也是这类章法,可以叫离散结构。这点是新作与芭蕉最大的不同,芭蕉有一个大的框架结构,小笔触的微观结构是围绕大结构展开的。大芭蕉的外拓结构,使女性化的笔墨结构张扬为男性化的宏观力量。去芭蕉相当于去壳,外在依托的东西慢慢去掉,笔墨得以自由释放,写心写意写性灵写胸襟更直接了,落笔见性灵,运笔即运心,直接地袒露出了纠结的诗——超旷而又伤痛,空灵而又纠结。说这些画没有空间,是没有西方写实绘画转化过来的抽象绘画空间;说这些画有空间,是自由运笔时轻时重,时散时聚,时虚时实,时明时暗转化出来的迷幻空间
“溯源”系列画的很好,它使我想起苏东坡的一句话,“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她的笔墨平淡,朴素,自然,没有硬做的斧凿痕,是真的心里画。
写意油画界有个人独特的笔墨结构的人很少,做得这么自然天成的就更少。这真是个致命的问题。
当然,我也有遗憾。去年看蔡锦在中国美术馆的展览时,我的思路一直被芭蕉系列牵着鼻子走,陶醉于她比较张扬,比较强悍的,比较有张力,比较有冲击性的画风。看到她的黑色芭蕉时,我说这简直可以做成大型雕塑;看到她的作画过程的照片时,我说那画了一半的画简直可以衍生出大山系列。没想到她的弯子转得这么大。当时她特意让我看展览中的两张画,但没有引起我太大的注意,没想到那两张画竟然是她后来的预兆,接着一下子拿出来一大批这样的作品,搞了个“溯源”系列,真的挺出我的意外的。现在我一方面对她的变化欣喜,另一方面又为失去了另外一个蔡锦而感到很遗憾。那个蔡锦的可能性确实还非常多,不要让我再也见不到另外一个蔡锦了。
贾方舟:刘骁纯一直是比较注重从语言结构的层面进行分析,给于总体上的规范。从一开始提到“笔墨”这个概念,目的是想找到一个不同的语言层面的说法,又觉得笔墨这个概念不能完全说清楚。他的“画面微观结构”的说法很好,蔡锦在美院上学的时候体现出来的那种画法,用油笔,用圆圈的线型来画层次,实际上就是自己很独特的语素或者语汇,从这个地方展开她的描述,展开她的叙事。把纠结的状态做了诗意表达。刘骁纯特别强调她的纠结,但又是诗意化的表达。还特别谈到她的遗憾,原来画美人蕉那种大的结构关系,如果做成非常有意思的装置会非常震撼,这个提示可以供蔡锦考虑。下一步怎么走都是可以的,并不一定是放弃,现在给大家呈现出这么一种转向来还是让我们很惊讶的。有一种看法说到最后发言的人会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全让前面的说完了,我们现在听一下下面几位该怎么说?
蔡锦作品《风景98》 布面油画 210x110cm 2014年
杨卫:蔡锦生命中内在的自我发觉
杨卫:我是90年代初知道蔡锦的,刚看到她的作品就感觉与很多艺术家不太一样,她作品中的自我发现,不是从外在经验得来的,而是源于内发性,是从身体的经验发散出来的感觉。这种自我发现和自我意识的觉醒,是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艺术的整体趋势,不管是男性艺术家还是女性艺术家。因为中国面临的问题与西方不太一样,要更复杂一些,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过去都是被束缚在意识形态的强权之下,所以,男人也一样在追求自我的解放。从85运动的文化宣言,到90年代以后的生命实践,我们可以梳理出一条很清晰的自我表现之路,无论是新生代艺术家,还是行为艺术的出现,都突显了这个特征。而90年代以后活跃的女性艺术,更是对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是蔡锦这样的艺术家在这个过程中更显突出。我觉得她画的作品还不像喻红她们,喻红的画更偏重于新生代一些,就是画面更有时代的形象特征。但蔡锦却不同,她一开始就是从自己的生命经验出发,美人蕉只不过是她表达的一个载体而已,她并不是去描述美人蕉本身,而是想通过美人蕉这个载体表达身体的一种反应。这个自我表现与自我挖掘,已经成了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艺术最为突显的特征。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男性艺术家后来出现了一些变化,由开始对身体的发现,对自觉意识的呼唤,后来又逐渐转向了表现社会文化的大题材,大内容。这可能跟男性的特质有些关系吧。另外,90年代初的时代背景比较特殊,整个社会都很压抑、很灰暗,在那样的情境下,艺术家无法向外拓展,也就只好转向对内的反思,这也促成了90年中国当代艺术的自我表现。可是,后来随着环境的宽松,不少艺术家都不满足于自我的那块小天他了,纷纷走向了对外界、对更多文化和社会问题的关注。
蔡锦也有这样的倾向,现在的这批作品相比她过去的作品,应该说要更有文化感了,无论是跟我们的传统文化,还是跟前面的很多先生说到的表现主义,或者意向艺术等等,都有了更深刻的联系。但是,在这个拓展的过程中,她身体里的那种独特经验,还是自觉不自觉地呈现了出来。我对贾方舟老师刚才说到的蔡锦笔下的这个梨非常感兴趣,我读她笔下的梨有种挠痒痒的感觉,甚至毛骨悚然。这是一种特别经验化的表达,能把画表现到这个程度的艺术家很少,尽管有的人也有很强的造型能力,画得也很好,但面对这样一个简单的梨,能画出毛骨悚然,画家一种像蜈蚣在身上爬的感觉,确实不多。蔡锦有这个本事,她不但能控制画面,而且能让画笔随心游走。刚才刘骁纯老师提到蔡锦的纠结和痛苦,我感觉她是沉溺在自己的痛苦与纠结中,把这种情绪转换成了艺术资源与创作能量。这样的艺术家男性里面也有,比如毛焰也是这样的艺术家,很自我,也很纠结,能把自己的小痛苦无穷放大,最终转换成揪人心肺的艺术语言,但这样的艺术家确实不多。
前面有先生说到蔡锦是感受型的艺术家,我觉得非常准确。这类艺术家比较自我,甚至自我到有点封闭。通常,她们不愿意打开那扇通往社会的大门,而是小心翼翼地把自我空间维护起来,将痛苦作为思想资源,把纠结作为抒发的冲动,转换成艺术语言,生发出自己独特的笔意。只有找到这种独特的抒发方式,她们才能自我安慰,否则就会更加痛苦,更加纠结。应该说蔡锦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艺术家,她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表现语言,这个语言是什么?我暂时也说不好,就目前这些作品来看还是更接近抽象艺术一点。其实,有的时候越抽象的东西,对我们感受的撞击却是越具体。这就像鲁迅对传统糟粕的批判所打的一个比方:“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他是把感觉抽象出来了,反而是一下子就击中了要害。我想,抽象艺术,或者说意向艺术的魅力,大概就是在这里吧,就是把我们现实中得到的感觉更加强化了。蔡锦迈出的这一步就带给了我们一种非常具体的感受,虽然她画面的形象不具体,但感觉却很真切,很具体。至于下一步怎么走?我想,如果以蔡锦原来的《美人蕉》作对比的话,是不是以后能呈现出某种有“天女散花”般的意向呢?也就是说画面可以更加灿烂,甚至可以是崩溃的,可以往末路狂花的方向去走。我想,在蔡锦的画面中是有这样的意向的。我就说这些,谢谢!
贾方舟:杨卫从最初的90年代的大背景说起,艺术家转向内心,转向自我,因为我们再无法关心国家大事,无法声张社会正义,我们只有关心我们自己,总的趋势是这样的,正是在这样大背景下,女性艺术家出场了,女性艺术出现在90年代,从1990年《女画家的世界》展开始,女性艺术才真正的展露出来,这个发展线索非常清晰。就是内在经验的自我表述,走向内心的自我探寻之路。刚才杨卫说到有没有可能出现如仙女散花,最后变得非常单纯非常灿烂这样的画面?
高岭:蔡锦不断创造独立造形的语汇
高岭:很高兴参加蔡锦的研讨会,刚才看了最近新的作品,她的新画与我最近几年感兴趣和关心的问题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蔡锦事先也寄了很厚的一本画册给我,前一些时间认真看了,在我的印象里虽然和蔡锦的本人接触不多,但是她的作品在最近20年里面是非常突出的。其实从画册上看到她早期1990年以前,就是80年代的素描和人物画作品,用笔开始有意识的在人物的肢体上用团块性的色彩来画肌肉,通过色彩和明暗关系来塑造每一个肌肉,让它鼓起来,已经开始有团块的征兆和迹象。在这个时期和喻红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但是,蔡锦和喻红们不同的是,她逐渐意识到要让这个团块状的东西强化独立出来,而成为了最近十七八年来蔡锦独立造形的语汇。这个语汇我们在看喻红们一类的很多女性绘画,包括男性绘画的时候是看不到的。倒不是说喻红们不重要,画得不好,而是说蔡锦比她们走得更远,清醒意识到这个可以独立出来,就形成团块形的,圆圈这样的造形的语汇。这是她不同于其他画家特别是女性画家的最重要的部分。至于她是不是画美人蕉,是不是画其他题材芭蕉都不重要,这个是她个人非常独特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语言,也是她和其他的画家不一样的地方。
20年来,一直到今天被命名为《风景》的系列绘画,都表明她的画面一直在不断的独立,不断的抽离,自我意识的深层的阶段,而不是像很多画家依然停留在用笔,用色,画人体。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大部分画家最终还停留在改善和改良画面形象上,而少数跟优秀的艺术家是提升性和蜕变性,像蔡锦是蜕变型和不断提升型的,准确说像蚕脱茧这样,是有本质不同的。
蔡锦回国以后看到她很多的作品,大量的用在实物上,空间装置上,用在自行车上,浴缸,鞋上,地面上很多,这应该算是她拓展绘画空间的努力与尝试。
21世纪前五六年开始,我们看到她的第二个重要的转型阶段。在这个阶段,她打开纠结,就是打开团状语言词汇的阶段。这个阶段以她最新的作品为例,在这个系列里,没有具体的现实的形象,没有具体的现实的题材的定义物(而九十年代她的绘画有生命体的形象),有的都是非形体化,或者叫烟雾化、气雾化的图形这样一种形状。
什么叫非形体化,非实体化?就是用短促、旋转和不连续的线,这些线并不是为了勾勒我们看到的亮度形体的,其实那个亮度的色彩和形体线是分离的,是非叙事化,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离叙事化的状态。她新近绘画中形象,包括用色,都是浮动,游离,就是弥漫的状态,这样的状态她称之为风景系列。但其实不是风景,风景的概念是西方一百多年前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本身中文翻译成风,风化,风俗,风气。景用的是更多是侧重于景观的意思,人文地理的层面,换句话说它是作为外在的对象,被画家凝视,捕捉,表现,还是属于一种二元分离的再现性对象。西方的学术界早已经不用二元分离模式的概念评价和探讨了风景画了。
离风景化、去风景化是当代涉及表现自然事物对象时的一种国际化的趋势,蔡锦是吻合了国际化的趋势,也就是说又和东方人的传统精神,有了某些所谓的溯源,有了某些回归。比如在中国古代,讲的所谓的天人合一,没有主体,没有个体,没有二元的分离,画家、观赏者在创作或者欣赏一个风景的时候,其实人和风景是一体的,在画面中间的,不是说站在风景的外面。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古人用“俯仰”这个词,“抚摸”这个词来表达人跟外在自然或者事物的关系,身体之外所有的,包括心里想象的,用“抚摸”、“亲近”这样的词。所以我觉得蔡锦的绘画体现出这样的弥漫性,更多的跟我们中国传统中间的虚和实,有和无,似与幻,象、像与相这四者之间的关系有关,都引起了我的兴趣。中国的传统讲,像即非真,真即非像,一切形迹的东西都是幻相,如果执着于行迹则会过于执着,为物所累,世界和宇宙就其本质而言一切皆为幻相,大爱也好,大真也好,大象也好,只有追求天地的大和永恒,才能不执着于形迹,才能超然于纠结。
最后,我们横向的比较像蔡锦这样语言形态的画家最近几年不在少数,我看到很多这类的绘画,这样的绘画已经形成了小气候,如果大家都来这样画的时候,彼此之间在风格和手法上能不能区别开来,是很关键的。我所担心的是,这样的绘画是不是过于空洞,过于类型化了,因为它已经成为一个小气候。我的意思是说蔡锦因为个人的用笔,20多年形成的短促、非连续、带有圆圈和云团状的用笔,用色,甚至带有书法式的短小的方式,可能这些个人的些微的气质,些许的特征,有可能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画这样没有形象的绘画的时候决定彼此之间差异的最重要的依据,这是一个艺术家面貌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总之,回归东方,溯源东方是重要的,同时又要警惕,不要最终在画面中完全不着痕迹,完全类型化。
贾方舟:大家畅所欲言,把自己想要说的话说完,杨卫是用男性艺术家和蔡锦做比较,用毛焰和蔡锦做比较,找相似性,这个点找的非常好。高岭通过和喻红们的差异来体现蔡锦的特殊点,而且对蔡锦做了很具体的描述,烟雾化,微形体化,去风景化等等,我觉谈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从纠结到打开纠结,这是他对蔡锦的解读,原来是纠结的,现在这些画面是打开纠结这样的状态,下面我们请刘礼宾发言。
刘礼宾:中国当代艺术的批判
刘礼宾:首先谢谢贾老师,让我有机会见到蔡锦这位艺术家。此前一直看到《美人蕉》系列作品,当收到《溯源》画册的时候,很喜欢这些新作品,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变,整组作品非常轻松,这种“轻松”在早期的素描作品中已经呈现,现在扩大了整个画面。
我谈两个问题。
中国当代艺术30年不缺两种批判:第一种是基于题材的批判,伤痕美术、乡土写实、政治波普、艳俗艺术、青春残酷,卡通绘画基本上都属于此类绘画。题材批判特别注重政治题材,或者底层题材。只要表现它们,作品很容易进入“中国当代艺术界”。90年代中期批评界有关于“明确的意义”的讨论,因为各种原因停止了,到现在为止,这个讨论还没能继续下去,很可惜。我高中时候看过莫言一本小说,对我影响特别大——《透明的胡萝卜》。这本小说并没有像他的《红高粱》、《蛙》那么强的政治性,现实批判性。但莫言早年制作的这个“意象”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经常回避这样的问题。第二种批判强调“立场”,从星星美展,到2000年左右的“后感性”,都特别强调“立场”的存在。
但还有一个批评脉络就是形式语言的批判,从上世纪70年代末吴冠中开始,到1983年的抽象艺术讨论。2006年左右,抽象艺术在中国再次大量出现,发展到现在,有泛滥化、装饰画的情况出现。这个脉络是一个隐含的脉络,现在需要被提示出来。
以前看蔡锦的画,认为她是女性艺术家,或者认为她是是画美人蕉的艺术家,她就这样被明确化了。以这样的思路,如何看她最近的这些作品呢?这些作品充满了模糊性、意象性。在中央美院毕业生作品展的时候,每年都有这类作品,表现有机的,神秘的,暧昧的的意象,但这样的创作在美院里都获不了奖,为什么会这样?长征空间挖掘了郭凤仪,最近在美院一食堂的一个女工作人员,也在家里每天画有机线条,我们怎么样去看这类创作?
第二个问题。2005年我接触到了王光乐,我为什么对王光乐有兴趣呢?是因为当时中国正在流行“卡通绘画”。革命时代过来的画家就画革命,经历青春的画家就画“青春残酷”,卡通时代艺术家就画卡通。当时我在想这是不太简单了?太视觉了?太讲究视觉的二元对立了?王光乐的画不强调视觉性的,而是强调“触觉”。包括谭平的画,他在一件作品完成之前是不去看画的,画完以后再回头去看。
蔡锦现在的画也是这样,从局部衍生,并不强调视觉性,强调笔触的敏感,这里面积累她多年的绘画感知。高老师提出的“极多主义”也好,“意派”也好,背后都有类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