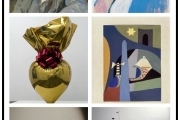左:六本木Crossing开幕酒会现场,摄影:Rachael Binnie;右:Shugo Arts的佐谷周吾,森美术馆策展人荒木夏实和日本文化厅文化财产部参事官林保太
在日语里,爱吃甜食的人被称为“甘党”,但它的对立面既不是“苦党”,也不是“咸党”,而是“辛党”,而且“辛党”也不是指爱吃辣的人,而是指爱喝酒的人。如果说语言习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该语言所属的文化,那么如上述例子所示,很多界限分明的二元对立项一放到日本,关系就迅速变得暧昧起来:“大型当代艺术双年展”的展览现场,最抢眼的观众也许是一些年过半百、西装革履的日本大叔和他们身穿和服,宛如从昭和年代穿越回来的妻子;而“国际艺术节”开幕派对最后的余兴节目很可能是本地居委会合唱团的倾情献唱。比起中国各艺术机构在追求“国际化”的道路上“不能神似也要形似”的直白努力,日本同行的做法显得更加让人难以捉摸。
的确,在六本木Hills 51楼的俱乐部大厅里,窗外是东京市区的豪华夜景,室内人头攒动,手里的香槟和鸡尾酒温度正好,你开始后悔没能穿得更正式一点儿。欢迎回到你所熟悉的艺术界。
“六本木Crossing”是森美术馆自创立翌年(2004)以来就一直坚持举办的大型群展,三年一度,集中盘点日本当代艺术的最新动向。而今年不仅恰逢森美术馆建馆十周年,也是2011年3・11地震以来的首次展出,加上东京刚刚申奥成功,各种时间、事件重叠在一起,馆方显然在策划上颇具野心也颇费苦心。主题“Out of Doubt”一语双关,明确点出了由片岡真実(Kataoka Mami)、Reuben Keehan、Gabriel Ritter三人组成的策展团队给自己定下的宏大选题:福岛核电站事故以来,日本国内民众对政府和现有制度的不信任感日益加深,从这种普遍存在的怀疑中是否能产生富有建设性的动议?或者如何走出走出怀疑,(走向坚定的行动)?
进门第一间展厅里,五十年代“报道绘画”代表作家中村宏(Nakamura Hiroshi)的“冲绳美军基地”系列、赤瀬川原平(Akasegawa Genpei)在七十年代初学生运动开始显露颓势时发表的讽刺漫画《樱画报》跟1972年出生的版画家風間サチコ(Kazama Sachiko)的作品放到一起,暗示新旧世代之间的联系与差异同时,也开门见山地吐露出强烈的社会问题意识。小泉明郎(Koizumi Meiro)的双屏装置将东京街头的日常生活片段和对年轻人(每位受访者都戴着头套,只露出嘴巴)的采访背靠背并置在一起,音画之间的断裂和偶然的一致酝酿出的不安气氛到下一间展厅就变成丹羽良徳(Niwa Yoshinori)的抗议标示牌和“在罗马尼亚将社会主义者抛高高”或“让日本G。C。D把马克思像挂起来”这种半介入半表演性质的行为记录文献。
如果说到此为止的作品都偏向“社会批判”,接下来以海外日籍艺术家为主的展厅就更强调作为“后物体艺术”的“行为过程”。不知道三人组成的策展团队内部具体如何分工合作,但海外单元估计是来自昆士兰美术馆亚洲当代艺术部的策展人Reuben Keehan和来自达拉斯美术馆的助理策展人Gabriel Ritter重点负责的部分。除了在纽约广受好评的荒川医(Arakawa Ei)和美国出生的田島美加(Tashima Mika)外,其他现居海外的参展艺术家大都来自澳洲和欧洲。唯一的例外是目前活跃于东京和西孟加拉邦两地的年轻艺术家岩田草平(Iwata Sohei)。这次他带着来自印度农村地区的原住民艺术团体Prominority中的五名成员在森美术馆楼下的毛利庭院用本地营造方法制作了一间“珍客亭”。五位桑塔利原住民都不会讲英语(日语就更不会说)。正式晚宴结束后,他们在岩田的带领下又加入了朋友饭局,但五个印度人似乎始终都保持了不舒服的沉默。
走过荒川医x南川史門(Minamikawa Shimon)的新作时,碰到刚从里昂回来不久的艺术家竹川宣彰(Takekawa Nobuaki),就顺嘴问他对荒川作品的意见。“如果对艺术史没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就很难体会这类作品的好玩儿。我还是觉得艺术没必要做得这么难懂。”竹川一向对东亚地区的文化思想感兴趣,最近一直在网上就日本国内对朝鲜人的仇视问题积极发言。对他而言,在社会历史学上下功夫显然比钻研如何回收利用艺术史资源更有魅力(或作用?)。“但你看了他上周在TOLOT / heuristic SHINONOME的行为表演了吗?超感动,简直可以改写艺术史。”旁边另一个热爱hip-hop的年轻艺术家做了个鬼脸,不知道是真情还是假意。
我承认自己在开幕当天就错过了一件“难懂”的作品。如果不是去听了第二天的艺术家接力讲座,很难想到奥村雄樹(Okumura Yuki)那间看上去像学生作品展一样的简易房间里藏着这么一个让人心情复杂的故事(请检索:Hisachika Takahashi)。接力讲座的主角是“海外组”艺术家。今年“六本木Crossing”的看点之一就是把旅居国外的日本艺术家(甚至包括藤原・西蒙[Simon Fujiwara]这种日裔外国艺术家)也纳入了关注范围。现居澳洲的艺术家Akira Akira在讲座前开玩笑说:“虽然我英语说得不如日语,但既然是侨民艺术家,今天还是用英语介绍作品,不然美术馆得找我退钱了。”不过荒川医还是很快乐地跟合作伙伴南川史門云里雾里地说了半个小时日语,每隔五分钟就问观众有没有问题。
当然,除海外艺术家以外,策展团队为观众准备的看点还有很多。光美术馆新闻稿上列举的关键词就包括:日本的自然观和不可见能量,nonsense和后物体艺术。可能是因为覆盖面太广,开场营造的张力到了中间就感觉渐渐消散在几个关系松散的不同方向上。物派代表人物之一菅木志雄(Suga Kishio)的作品被安排在展览快结束的部分,也许是为了画龙点睛,但现场只让人觉得落寞,仿佛在再次提醒我们物派诞生的六十年代与今天的距离。展厅里不见菅老先生的身影,倒是酒会上看到代理他的画廊老板小山登美夫(Koyama Tomio)正费力地想要穿过人群。
当我终于到吧台端上了一杯香槟时,有朋友说刚在展厅看到了中田英寿。这位前国足、现财团法人代表理事2009年发起了旨在振兴日本传统工艺的“Revalue Nippon Project”,并邀请森美术馆馆长南條史生担任顾问,此刻出现在开幕式上也不奇怪,不过倒让人想起隐藏在今天展览上所有社会问题、忧患意识、左派历史、日本自然观背后的另一个重要背景:2020年东京奥运。作为东京最大的地产集团之一,森美术馆所属的森大厦株式会社必然将在未来几年的东京都基础设施建设更新中发挥重要作用。可以想象,三年或六年后的“六本木Crossing”开幕酒肯定会更热闹,只是展览又将为观众呈现怎样一幅日本当代艺术全景。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