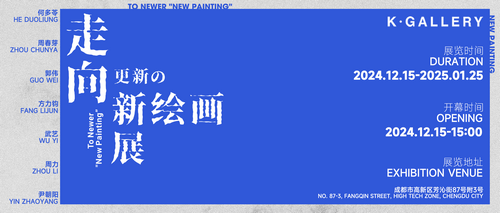美国洛杉矶盖蒂中心展示的反映航海图景的约1750年手工上色版画《巴达维亚,城市,堡垒和荷兰总督的官邸》(局部)
19世纪末佚名摄影师在柬埔寨所拍摄的吴哥王城和吴哥窟的史料照片
海洋对于当下中国的发展一直是热点话题,如果回顾历史上的航海,对于西方而言,几百年前那些由航海家们带回来的各种物品和记述文献改变了整个西方世界的发展轨迹。然而,中国的航海到底发现了什么?改变了什么?记者通过对美国“四海踏破”航海图展及首都博物馆“海上丝绸之路”展的剖析,试图对此进行一些呈现与思考。
海域对于当下中国一直是热点话题,无论是东海,还是南海,抑或太平洋、印度洋。
然而如果回顾历史上的航海,对于西方而言,几百年前那些由航海家们带回来的各种物品和记述文献引起了巨大的震惊,也由此改变了整个西方世界的发展轨迹。另一个问题,无论是远古的中华先民,抑或郑和、郑成功,中国的航海到底发现了什么?改变了什么?
曾几何时,航海是人们探索外部世界的主要途径之一,也由此生发出天马行空的遐想和无限的激情。冒险家们满怀好奇心,历经艰险漂洋过海,在彼岸奇遇陌生的文化。那么,他们眼中的亚洲、美洲、非洲是什么模样的?而当时人们又是如何看待、表现、传播那些传奇的历险经历和新发现的?一批珍贵的手稿及时记录下了早期航海家们的所见所闻,而随着印刷术的西渐,相关的文字插图得以大量出版。不久前,在美国洛杉矶盖蒂中心刚刚举办了一个名为“四海踏破:一部发现与相遇的图史”的大展。凭着盖蒂研究所的丰富馆藏,展览将500年间鲜为人知的航海图史展现在世人面前。
一部“理解”与“误解”的航图史
美国洛杉矶盖蒂中心关于这一航海图景的展览包括罕见的文献、印刷品、地图、照片及一些日常文物杂件。记者了解到,展出的一个亮点之一,由17世纪德国耶稣会成员、著名学者阿塔纳修斯·基歇尔(AthanasiusKircher)所著的代表作《中国图说》在欧洲早期汉学史中具有重要地位,是研究西方汉学史之必读之作。该书英文版译者认为“该书出版后的200多年内,在形成西方人对中国及其邻国的认识上,《中国图说》可称得上独一无二的、最重要的著作”。法国学者艾田蒲(Etiemble)认为,这本书当时在欧洲的影响实际上比利马窦和金及阁的《中国札记》影响更大。该著作1668年由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书中反映了中国的宗教、世俗、各种自然、技术奇观等众多面向,附有几十幅精美版画,包括著名的《着中国官员服的传教士像》、《中国皇帝像》等。而此次展览就呈现了书中一幅手工上色的版画《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von Bell)与星盘》。另外,还有18世纪末描绘穿越沙漠去叙利亚巴尔米拉地区商队的蚀刻版画、19世纪初关于巴西奴隶市场的石版画、19世纪末佚名摄影师在柬埔寨所拍摄的吴哥王城和吴哥窟的史料照片等。
通过这些珍贵的图像资料,人们可以一窥当年欧洲等地的冒险家们是如何与未知、生疏、异域、异俗打交道的。同时,展览也希望从一个伦理的维度,和观众一起反思不同文明间“理解”与“误解”的历史。这段历史复杂而漫长,时至今日仍在延续。我们如何学会接纳和宽容?如何学会在这个共同的地球村里,保护乃至欣赏人类文明的多元化以及自然生态的多样性?这些命题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展览分别为“导航世界”、“远征与探险”及“贸易与殖民”。第一部分主要展示了早期冒险家们海上导航所使用的一些工具和技术。众所周知,海上航行面临着巨大的风险,而对天文导航的认知以及航海仪器的发明便成为了应对挑战的两大法宝。当然,绘制世界地图更是探索未知的第一步。展览中那些难得一见的展品揭示了当年人们感知世界的视角,很多在今天看来甚至稀奇古怪、天方夜谭,比如由盖蒂研究所收藏的一幅世界地图木刻版画,
它所描绘的是一个三叶草形的世界,三片叶子分别代表欧洲、亚洲和非洲,而位于世界中心的是耶路撒冷。这幅地图由德国新教牧师、神学家、地图制作师海恩里希·本廷(HeinrichBünting)绘制,刊于其1597年出版的著作《神圣抄本之旅》(Itinerariumsacraescripturae)之中。凡此种种试图勾勒整个世界的大胆尝试,来自竭力延展的感官体悟,夹杂着经验和想象,更激发了远行的脚步。而随着航海和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人类对世界的认知也越来越接近今天熟识的模样。
通过航海,人们看清了整个世界,而在丈量与其他文明关系的同时,也更加明确、理解了自身在这个世界中所处的位置。展望与想象,测绘与探索,相遇与捕捉,勇于去感知一个个有别于自己的陌生世界,这是几百年来西方以及非西方的探险家们所共有的壮举。
对于西方而言,那些由航海家们带回来的各种物品和记述文献引起了巨大的震惊,也由此改变了整个西方世界的发展轨迹。而早期的许多游记却往往天马行空,那些道听途说的报告引发了对于彼岸以及彼岸文化的诸多古怪的误解。本次展品中有一幅名为《亚洲荒野里的人》的木刻版画就生动地诠释了这一点。该作品被收录在意大利人乔万尼·博泰罗(GiovanniBotero)17世纪早期的书中,画面中的亚洲人没有头,他的脸直接长在胸前。
对于彼岸大陆的探究大约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才慢慢进入了较为学术的层面。探测、收集完资料后,紧接着就是分析和研究。这种严谨的治学方式受到了启蒙思想的巨大影响,当然,也时常为欧洲统治者的帝国主义野心所利用。拿破仑就曾召集一批地理学家、考古学家和科学家为他在埃及的军事行动助阵。回到法国以后,这个专家团队出版了第一手的、准确的观察报告,不仅如此,还发表了关于整个埃及世界具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小到一种昆虫,大到一座古迹。逐渐地,对于异域文化的研究成为了一些学者的专业领域。他们看重在当地的实证经验,并且采用系统、科学的研究手段来分析问题。其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就是德国博物学家、自然地理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vonHumboldt)。其游历了拉丁美洲的广袤土地,带着珍贵的标本和大量笔记回到柏林和巴黎,据此潜心钻研,并最终发表了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成果。随着相关学科的兴起,这种学术性的视角在19世纪和20世纪被进一步强化。
然而,在欧洲与非欧国家关系上,贸易与商业还是成了主导的因素。探险、殖民、剥削是现代殖民主义时期的主要特征,各个欧洲国家竞相争夺非洲、亚洲和美洲领土的控制权。而在当时欧洲和北美的一些国际展会上,不仅展出那些来自远方大陆的产品,还包括许多据此制作的复制品等。本次展览中一幅由英国水彩画家、平版印刷家约瑟夫·纳什(JosephNash)制作的彩色石印画,就生动描绘了1851年伦敦举办的“万国工业产品大博览会”上中国展区的场景。而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关于种族的种种理论和观点可以在各种印刷品、杂志、照片,甚至儿童游戏中找到端倪,例如盖蒂研究中心所藏的一副1910年代的德国跳棋,由彩色石印画等不同艺术工艺制作而成,其内容就是殖民游戏。另一种诞生于二战期间的法国“贸易游戏”色彩鲜艳地标出了法国各块殖民地及所占有的自然资源,让孩子们在游戏中就能了解这些殖民地是如何支撑法国本土经济的。
不过有些遗憾的是,关于中国的航海这一展览涉及并不多,明代的中国航海家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的经历在这样的展览中也无从觅踪。
收录在乔万尼·博泰罗17世纪早期书中的木刻版画《亚洲荒野里的人》
约瑟夫·纳什的彩色石印画,《1851年伦敦万国工业产品大博览会上的中国展区》
1579年墨西哥人想象中《天堂般的耶路撒冷》
“用西方航海观来套中国是有问题的”
盖蒂研究中心主任托马斯·W.盖特根斯(ThomasW.Gaehtgens)说:“这次展览中的大部分展品都根植于西方的传统,从西方的视角出发。不过一些来自于其他文明的珍贵文物已经发出了一个重要的转变信号——我们希望随着藏品的日渐丰富,这个新的方向在今后的项目中体现得更加清晰,也就是能够更全面地呈现出整个世界的文化交流史。”这种广博的人类学的立场,以及严谨的学术态度深得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鲁西奇的认同,他认为:“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而对于整个世界来说,诞生于不同文明的航海历史确实也展现出不同的生态。
就中国而言,航海的历史同样十分悠久。厦门大学特聘教授、海洋考古学中心主任吴春明认为:“在过去的100年里,主要是建国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考古工作者在沿海地区发现了史前上古时代大量的百越、东夷文化遗产,这个历史可以把环中国海洋史上溯到距今一万年前,在这期间都有持续的传承过程。比如说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位于胶东半岛到辽东半岛之间,山东长岛群岛距今6000年以来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甚至“东周到汉代前后的东南沿海地区有一系列百越王国,比如说于越、东瓯、闽越、南越,或者是在越南红河流域的骆越,长江以南所有王国的都城都在海边,大江大河的入海口。所以,东南沿海地区的百越先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活动是趋向于海洋活动的”。但正如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葛剑雄教授所言:“单纯用西方的航海观来套中国是有问题的。”中国古代核心文明是农耕文明和大陆文明,内向型的发展所形成的海洋观念和生存状态和西方有着本质的区别。
记者在调查采访中发现,和西方大体上有官方支持的、带有殖民、探险、传教目的的航海不同,中国的航海更多地来自民间。鲁西奇表示:“中国航海的主流是民众的自发行为”,其中滨海地区百姓的航海与生计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他们的“社会信仰、文化”也大抵都与海“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中古时代的大部分沿海港口城市,与其所在州县的治所之间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分离,这不仅是距离上的疏离,而且在社会制度、法律管理上,也比较疏离,换句话说不太受官府的管控”,进而构成“具有鲜明海洋特征的地域社会”。当然,其中有些人就沦为海盗。而在中国历史上,海盗的形成一定程度上与朝廷的海上禁商不无关系。谢杰所著的《虔台倭纂》成书于明万历年间,是一部典型的以防倭御寇为主要目的的著作,其中就讲道:“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吴春明则指出:“从文化圈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主体是‘中华先民’,包括东夷和百越。东夷与百越先民分别通过早期的航海活动,将中华海洋文化的分布范围扩展到朝鲜半岛、日本以及东南亚与太平洋群岛等地,奠定了中华海洋文化圈的初期格局,远远大于我们讲的四大海域——东海、南海、渤海、黄海。那为什么我们中华海洋活动空间只有四大海域了呢?实际上跟我们在海洋上的退却有关。我们把夷越先民分离出去了,把明清时期的东南沿海的海商看成是海盗,给予打击。假如我们那时能够站在海洋的立场上尊重海洋文化,发展海洋文化,那么中国现在所控制的绝非只有四大海域,而是‘环中国海’。”而这些不被当时官府所接收的海商,却也发展出了强大的航海能力。葛剑雄对《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表示,明朝虽然海禁严厉,但一些地方由于生计困难,而海上贸易的利润又相当丰厚,所以走私贸易十分活跃,到后来发展成武装走私集团,比如王直和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他们的航海是发达的。郑芝龙还在台湾建立了基地,其作为先于荷兰人开台先驱的汉人,继承李旦和颜思齐等人及部众在台湾西南海岸魍港建立基础,为汉人移台的主要据点。
当然,中国航海史上同样有举世闻名的官方航海活动,郑和下西洋就是最为著名的一例。但其宣扬国威、和平尚礼的远洋与西方航海依然有着本质的区别,在传播中华文明的同时,却亏虚了国库,但也的确创下了多个世界航海之最。而朝贡贸易也是中国古代航海较为独特的一种生态。当然,外国来华的大批商船也为沟通中西贸易,为“海上丝绸之路”作出了贡献。德国著名东亚艺术史专家雷德侯(LotharLedderose)教授在他的著作《万物》中这样记述:
整个18世纪中国瓷器的外销依旧兴盛不衰,荷兰人所记录的详细数字能证明这一点。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荷兰的一个单项的订购统计如下:100个鱼盘、200个汤碗、200套餐具、1000个茶壶、1000个痰盂、1000个带托盘的饮料杯、1400个牛奶壶、2000对正餐用盘、8000件汤杯、10000件巧克力杯、14000个带托盘的荷兰式两件套咖啡杯、40000件带托盘或不带托盘的咖啡屋用咖啡杯、130000件带托盘的大型荷兰式咖啡杯。
这年,东印度公司的六只船到达广州。每次单程航行一艘船能带回150000件瓷器。荷兰的公司在这类公司中是最大的,但英国、瑞典、丹麦和其他几个国家也参与了瓷器贸易。英国所占的市场份额,据说在1700年前后就已经与荷兰不相上下,1730年之后甚至超过了荷兰。根据各种各样的、有时还很详细的历史记录,可以大致推算出中国在17、18世纪期间外销瓷的生产总量,一定会达到好几亿件的数额。
航海沟通了世界文明,好奇、激情、迷恋、共鸣,伴随着误读、偏见、刻板印象一路走来。一件件珍贵的文物将文明碰撞的一个个瞬间定格还原。然而,航海于不同文明有着不同的形态,亦产生了各不相同的影响,因此,也需要以更多元、更包容的眼光来看待,以更诚实的态度来面对历史。全球化的今天,海洋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国是不是能够从自己的航海史上总结、吸取一些经验和教训?而人类文明交流的密切程度也已今非昔比。或许,以史为鉴,能够让我们更好地面对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