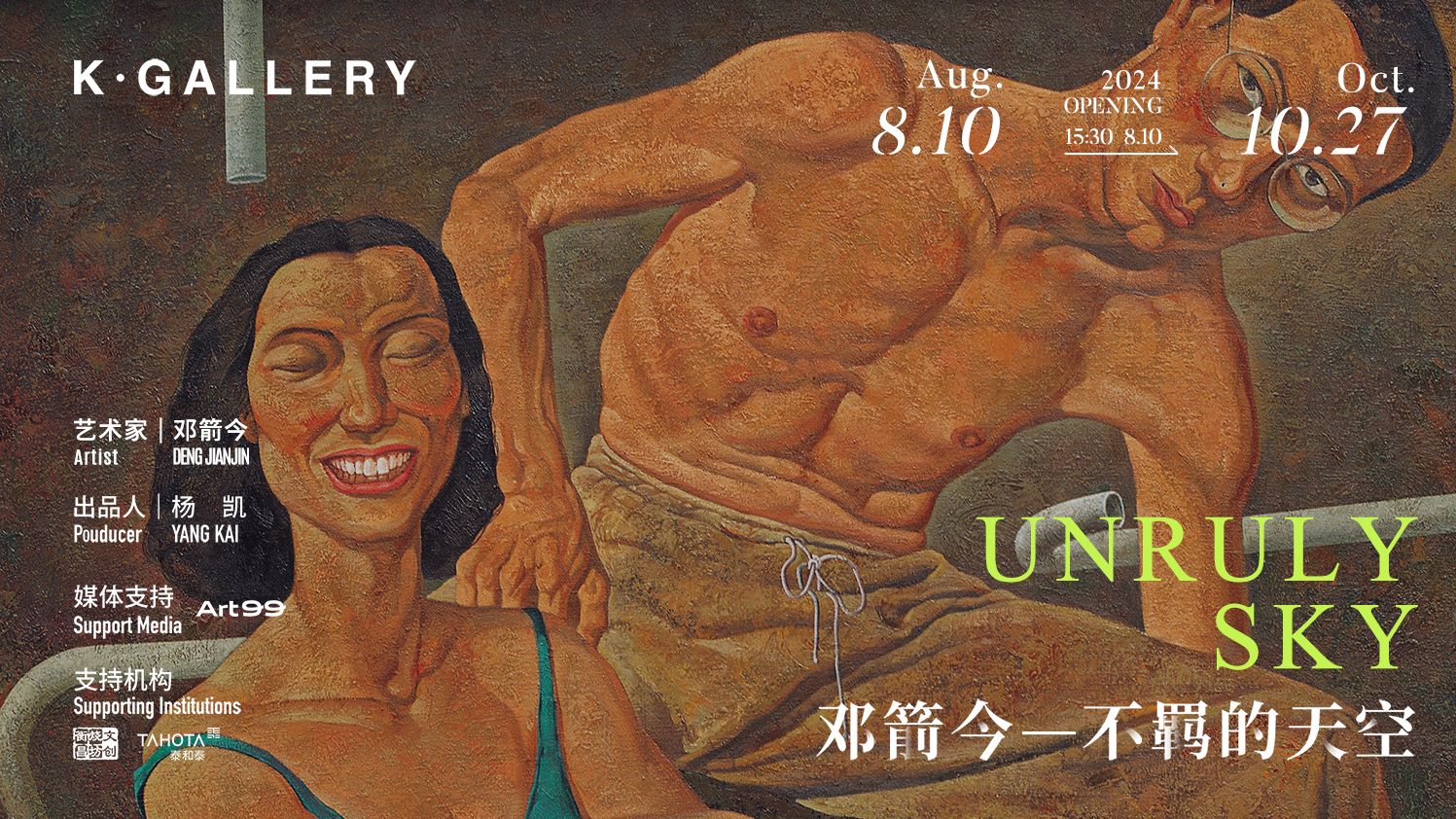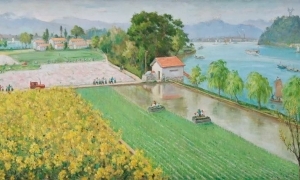现代日常生活已经全面的异化,异化已蔓延于现代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但是,日常生活概念在曾妮那里不仅仅是消极的,它还具有积极的意义。艺术家认为,由于日常生活是联系所有其他活动的纽带,它也就有可能成为对这些活动的直接批判。"当日常生活成为一种批判,成为对这些高级活动和它们所制造的东西:意识形态的批判时,白日的曙光就出现了……直接的批判取代了间接的批判主义;这种直接的批判包括对日常生活的重新占有,将使之更清楚地显示出其积极的内容。"(列斐伏尔)
曾妮的绘画表现出一种对日常生活欢娱幻灭的伤感与追忆,是"生活的甜蜜" (the sweetness of life)而不是"甜蜜的生活' (the sweet life)。"这点特别耐人寻味。植根于日常生活的世俗美,既不属于"甜蜜的生活",同样也不同于"痛苦的生活",而是努力表现"生活的甜蜜",这才是曾妮绘画的实质。
曾妮是一位擅长将艺术与日常生活混淆的艺术家。在她看来,日常生活审美化有两层含义:第一,艺术家们摆弄日常生活的物品,并把它们变成艺术对象。第二,人们也在将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转变为某种审美规划,旨在从他们的服饰、外观,家居物品中营造出某种一致的风格。以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亦即人们把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周遭环境看作是艺术的对象。
在艺术史上,审美化一直是一个带有乌托邦性质的未来目标。尤其是近代以来,艺术常常不是在早已逝去的古希腊时代寻找意境,就是对尚未到来的某种美好未来憧憬期待,严肃的艺术似乎很难把审美化直接派付给琐碎平庸的日常生活。韦伯现代性研究的一个著名论断,就是断言现代日常生活是一个"铁笼",而审美则具有某种将人们从"铁笼"的压抑中拯救出来的世俗"救赎"功能。尼采说,"诗人"可以被界定为"作为使人生变得轻松的人"。世俗美的根据在于神圣性的脆弱。唯其如此,一部艺术史并不能由神圣美所主宰,事实上一直以某种"隐蔽"的方式,呈现着由"神圣美"与"世俗美"分庭抗礼的格局。
曾妮的绘画描绘那些夜夜笙歌的浮华世界。在她的观念中,世俗与神圣的关联不可缺少,世俗性的对立面其实是"非人性"而不是"神圣性"。世俗美之所以能超越市侩趣味而进入审美视野,就在于其中内在地拥有一种"日常生活的神圣性"。如何能够从看似无足轻重的平凡生活中发现存在的神圣性?这才是关于曾妮日常诗学思考的重心所在。她讨论世俗美学的目的,同样也并不是对神圣美的否定,而是要通过对这种二元论的超越,建立新的诗学格局。"一切生命都是神圣的,包括那些从人的立场来看显得低级的生命也是如此。"她将游戏性与神圣性融为一体,总是表现那种给人以慰藉、使每个聆听者都感到惬意的转化。曾妮的绘画从未表现过悲剧气氛,她嬉戏,不停地嬉戏。观看她的作品而内心又不为所动、不参与嬉戏,谁就没有真正看懂。曾妮的绘画诗学"举重若轻",具有一种内在严肃性。如尼采所说:"一切神圣的东西都是轻轻地走。"
人们在频频举杯的热闹中、在声嘶力竭的宣泄里力图抓住转瞬即逝的一点快乐。快乐点,再快乐点,为自己,为他人。是否人们以短暂的聚、虚假的欢娱和夸张的喧嚣来刻意掩饰内心世界的荒凉和相互之间疏远?显然,这是一种悲剧性的生存经验,只不过,它经常以一种貌快乐的方式呈现。作为一个经常穿梭在各种名目聚会中的女人,曾妮此有自己亲历的体会和洞察。人生是一场时聚时散的宴席,终有曲终散的幕落时刻。曾妮小心翼翼地把这些感受收拾起来,为每一点快乐此存照。她的作品将一场场欢乐聚会定格在画面上,让所有耍的瞬间结为在的永恒。在《我耍故我在》系列作品中,曾妮有力地抓住了现都市人乐此不疲的"快乐"经验,但那些极其主观的俯视角度是否流出这些"快乐"的飘浮感?而凌乱的笔触与暧昧的色彩效果又是否呈了难以遮掩的悲剧性?
彭肜,艺术评论家,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曾妮是成都艺术圈的活跃人物。其热得发烫的为人态度,以及艺术活动的频繁出场,奠定了她组织力与亲和力的个性特色。有意味的是,她的作品的价值取向,也与其熟知的艺术生活密切相关。《我耍故我在》是一个广泛猎取艺术生活资源的作品系列。作品的内容,均取自各种与艺术家相关的或展览或生活的现场。这些看起来吃吃喝喝拉拉扯扯的普通内容其实是艺术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们过去说的带有意识形态倾向的"生活",与当下健康自在的"生活",有着本质区别。前者是指定性的政治性的,后者是原发的野生的。这里涉及到的逻辑关系,显然已脱离了曾禁锢人们思想的伤感年代。它是当下的,鲜活的。只有在充分自我的生活状态里,才能找到充分自我的艺术面貌。如同对"成都"概念的新解,有了成都就有了生活,有了艺术就有了成都。听其似无理,然道理却在其中。曾妮作品的语言,带有情绪书写性。这种书写,有些书法的直抒胸意,有些涂鸦的即兴冲动,有些古典的精雕细刻。将各种鲜活的场景内容,与恰当的书写进行煽情化的融合,使得写与被写的价值,均得到有效提升。同时,因为所涉及的活动现场,都是在动中存在的。动,本也是情绪的诱发源。情绪,既有作者的自我成份,也有现场的情态元素。二者产生共振,诱发出情感杀伤力,必然辐射至阅读,并产生阅读的快感。她的作品中所含的叙事版本意义,可以从另一层面考量本土当代艺术的发生史,使得我们的史学不再枯燥。
在一个阅读日趋图像化的时代,传统的耳听口传眼读,正逐步让位于数量惊人的视觉信息。而由艺术家创造的各种图像版本,是读图时代的主流内容。它们是社会机体的必要组成部分,在成为新文化亮点的同时,也以自身的魅力进入历史。
陈默,艺术评论家,策展人,四川音乐学院成都美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