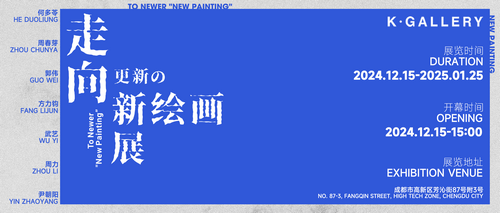3月9日,松美术馆的最新一期“松间对话”如期进行,此次对话由《艺术商业》联合松美术馆共同举办,题为“从梵高到‘松’式生活”。这次对谈邀请艺术家向京与佳士得印象派及现代艺术资深专家谭波,一起分享了她们对于梵高创作的理解以及东西方艺术思潮如何互相影响、互渗等话题。
松美术馆展出的梵高作品《雏菊与罂粟花》
为什么我们都爱梵高?
岳岩:大家好,松美术馆这次展出的一幅作品叫做《雏菊与罂粟花》,由梵高创作,很多观众为它而来,我们这期对谈的主题也是从梵高切入的。这次的两位重量级嘉宾分别是艺术家向京女士,以及佳士得印象派及现代艺术资深专家谭波女士。
主持人《艺术商业》副主编岳岩
梵高是一个自带流量的艺术家,从去年年底一直到现在都热度不减,日本目前有三个大展都在讲梵高,挖掘了梵高与东方艺术的关联。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2019年春也将迎来梵高的大展,讲的是梵高在伦敦时期的生活与创作。今天我们首先想请两位嘉宾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次知道梵高大概是在什么时期,以及看到梵高原作时有什么样的感受。
梵高作品《罗纳河上的星空》将于2019年春季亮相泰特美术馆
谭波:在我读中学的时候,我的邻居是一个画家,他有一套在台湾买的《大英视觉艺术百科全书》,那套画册中我特别喜欢梵高的《向日葵》和《星夜》。第一次看到梵高的原作,是在纽约MoMA看到那幅著名的《星夜》。还记得看到原作的第一反应是,原来它的尺寸并不大,不到一米左右,但是给我的冲击力还是非常强的。梵高的笔触非常粗犷,油彩堆积得很厚,《星夜》充满了像旋涡一样的动感和能量,星星们好像在爆炸在扩张在旋转,只有角落的村庄是安静的。连接天地之间的是像火焰一样跳动的丝柏树,一种通常种在墓地的代表死亡和哀悼的树。但是死亡对于梵高来说,并不是可怕的事情。我当时就想到他写给弟弟提奥的信说起过,“看着星空常常令我幻想,为什么,我问自己,为什么这些天空中闪亮的点,不像法国地图上的黑点一样容易接近呢?就像我们通过火车去塔拉斯康或者鲁昂这些城市,我们通过死亡到达星辰。”
佳士得印象派及现代艺术资深专家谭波
梵高《星夜》
向京:我接触梵高是在上央美附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十几岁,自己正处在青春期,赶上中国80年代,是一个强劲的文化复兴的时代。当时我们附中进口画册比较多,但是我们能借到最新艺术形态的图书就是关于印象派的,包括老师讲艺术史,其实也是讲到印象派就结束了。
艺术家向京
印象派当时给我们的感受就是一种最新潮的艺术,当然这是今天完全想象不到的蒙昧状态下的一种接触。那个时候也有大量的日本画册,日本曾一度追捧印象派,我觉得谭波肯定知道,印象派几乎是被日本人在市场上炒起来,包括梵高也是被日本人炒起来的。
梵高《向日葵》
东京安田·葛西艺术博物馆藏
谭波:日本人非常崇拜和迷恋梵高。去年圣诞节假期的时候,我去日本东京都美术馆看了一个梵高的特展,叫做“梵高:流转的日本之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点是:它不仅把日本的浮世绘和梵高原作并列展出,同时把1920年代日本的知识分子、艺术家崇拜梵高,到梵高生活过的地方去朝圣的照片以及登记簿都留下来了,作为文献展出。
“流转的日本之梦”海报
向京:我记得第一次看到梵高原作是在巴黎,我看了之后相当震撼,那种震撼其实是很难言说的。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颜色怎么那么亮?我相信梵高没有钱买特别的颜料,但是他的画作是那么的闪亮,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本雅明所说的“Aura”,即灵光之类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今天在传播路径当中无法被复制的。而这也是我心目中认为艺术里面最核心的一个价值。
奥维尔小镇上梵高的塑像
谭波:Aura,我们只能在梵高的原作面前感受到,还有就是在他曾经生活过创作过的地方。去年夏天,我去了一趟奥维尔,梵高生命中的最后69天是在那儿度过的,他在那里创作了大概90多幅油画,属于一个创作的高峰期。奥维尔地方非常小,我很惊讶是已经一百多年过去了,它还是很淳朴,基本上维持着原来的样子,我们还能找到梵高风景画中的许多地方。
奥维尔小镇的教堂与梵高笔下的教堂
梵高著名的《麦田群鸦》是七月画的,所以我当时也特意在七月去了奥维尔,寻找画作中的那片麦田。当时我从去梵高墓地的一条小路往镇子外走,突然一下就视野开阔起来,我正好站的位置较低,而麦子的高度大概在齐腰的位置,大片大片的麦田一望无垠,无边无际。正午灿烂无比的阳光,照耀在金黄的麦田上,我完全看不到地平线,那种大自然给人的震撼,带来的是排山倒海的情绪,我当时一下子眼睛就红了。立刻联想到梵高写信给弟弟说,他在麦田里面感到那种孤独,还有作为人类的极其悲哀、孤单的感觉,这让我一下子对梵高的麦田系列有了更深的理解。
梵高作品《麦田乌鸦》
奥维尔小镇的田野
梵高如何受到东方影响?
岳岩:从梵高的画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黑色的勾线会很像东方的版画,因为他受到日本浮世绘很大的影响,两位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述一下梵高或者说印象派的艺术家当时是怎么受到东方影响的?
“松间对话”对谈现场
向京:我觉得西方古典主义绘画很多时候是从以一种科学性的技术和态度去找到复原现实的方法,从这点来看,东方的绘画肯定是给了西方人很大的冲击。这既是一个美学系统的东西,也是如何看待、转换视觉上既有的视角。这些艺术家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可以获得新的方法,比如说勾边脱不脱线,包括把画面怎么样平面化,这在后印象派的作品更凸现。
梵高《花魁》 临摹日本浮世绘画家溪斋英泉的作品
谭波:后印象派艺术家最重要的一个创作的特点,就是浮世绘启发了他们摒弃文艺复兴以来单点透视的传统,在日本的浮世绘里面,更多是散点或者多点的透视,比如说一幅画的上部可能是一个平视的视角,下部是一个俯视,也不会像单点透视那样注重表现进深感也就是立体空间,你看梵高的作品是很平面化的。浮世绘用线条勾勒轮廓以及平涂色块的特点,在后印象派的另一位画家高更的身上更加明显。
《身穿云龙打挂的花魁》
1820-1830年代,溪斋英泉,千叶市美术馆藏
印象派是怎么进入中国的?
岳岩:向京老师之前讲到80年代我们美术界对于印象派的一个狂热和认知,但是其实倒回到一百年前,大概是1880年,当时欧洲对东方艺术也是很好奇和追捧的,所以也就导致了梵高在当时狂热地去学习东方的艺术和文化。结果百年之后,东方这些人又开始狂热地喜欢印象派这些艺术家。关于印象派,谭波老师要不要再给大家做一些解释?以及它当时是怎么进入到中国的?
“松间对话”对谈现场
谭波:印象派可以说是整个西方现代艺术史上第一个在绘画领域的运动,1860年起源于巴黎,1874年举办的第一届印象派艺术家的群展标志着它的成立,在1886年最后一届展览后走向式微,它的影响遍及欧洲远至美国。在西方艺术史上的地位,可以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因为它上接19世纪的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下启20世纪现代主义艺术形形色色的艺术流派。1880年代中后期也就是印象派后期开始,到1905年野兽派刚出现的时候,这一段大约20年间的艺术风格的称为后印象派,其中最有名的三位艺术家是梵高、高更和塞尚。
李叔同(弘一法师)自画像 东京艺术大学馆藏
印象派最早传入到中国的西洋画概念之一。早在1905年,弘一法师去日本留学,师从黑田清辉,他的风格其实就是印象派的风格。随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量留学法国和日本学习西洋画的画家学成归国,通过撰写文章、创作和教学将印象派和后印象派介绍到了中国。中国现代西画运动这段时期的兴盛,是印象派在中国传播的高峰。
“松间对话”对谈现场
新中国成立以后,受前苏联的文艺理论影响,印象派成了资产阶级艺术的颓废流派。1964年开始的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以印象派为代表的西方现代艺术都成了“黑画”,被批判的对象。直到文革结束,印象派才开始复苏,1979年北京中山公园举办了印象派画家第一届展览,而且这个展览以今天的眼光来说很搞笑,因为都是图片展,并没有原作。但这个展览在当时非常轰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完整地公开展出印象派作品,当年吴冠中看了这个展览还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印象派的前前后后》。
当年留言簿里有一个热心观众留言是这样的:我的妈呀!可怕的印象派原来是这么回事……太可爱了!吴冠中就说道, “印象主义绘画在我国曾被认为是禁区,遭到批判。其实,学过西方绘画的,不管你是直接或是间接,专业或业余,教授或学生……都吃过印象主义的奶,何苦要批这个一百年前的老奶妈呢?
吴冠中 (1919-2010)《英国乡村旅店》
因为大家想想,印象派产生是1874年,这都是一百多年的事情了,可是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还是一个崭新的东西。70年代末80年初的时候,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家和流派被介绍到了中国,包括那个时候中国当代的艺术家,比如说张晓刚他们,80年代的创作风格都有受梵高和表现主义的影响,如周春芽1980年的《藏族新一代》和《阳光下的若尔盖》有着块状的笔触和浓重的色彩,张晓刚1981的《暴风雨将至》和1982年的《天上的云》都能看出来这种。到了八五新潮时期和之后,有更多的西方当代艺术及理论被介绍到了中国,印象派也好梵高也好,不再对中国当代艺术有那么直接明显的影响。
周春芽1980年的《藏族新一代》
张晓刚 暴雨将至 纸本油画 83×110cm 1981年
张晓刚《天上的云》
岳岩:应该是开始有了新路线之后,印象派变得没有之前那么重要了,变成了一个分支,但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分支。
向京:我觉得应该80年代迅速把西方现代主义历史整个自己演一遍。
今天我们还需要东方性吗?
岳岩:我们谈印象派、后印象派也好,谈的其实都是中西碰撞的事情。近年来我们特别喜欢去强调中式的概念,一带一路也好,传统文化的复兴也好,都是这样。但是作为生长于全球化语境下的年青一代,我们对于地缘身份已经没有那么强的认同,是网络中生长出的一代,所以我们还有必要谈东方性吗?
“松间对话”对谈现场
向京:我觉得有必要。我们现在特别喜欢谈的一个词:全球化。全球化在我的理解里面,就是世界化。我们透过这种信息的发达,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文化,我们理解这种多元化,尊重和宽容各种各样的不同,这在我眼里是更理想的全球化。
我们现在都有很多出国的经历,比方说当第一次去出国,是去巴黎,我碰到了一个法国的小孩,他从来没有到中国,但是说得一口非常流利的中文,他疯狂地邀请我看博物馆里亚洲艺术的一个展览,他说自己已经看了五遍了,觉得最棒的还是中国艺术,毕竟还是一个非常大的深厚文化的格局。
这个事情当时给我一个挺大的刺激,我想拿高更的那幅名画《我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来解释,其实所有文化最终级的问题都是这个。我比较不赞同刚刚讲的观点,我们不需要这个家乡。确实,我们在世界游走的时候穿的衣服跟国外一点区别没有,我们的发型,化的妆,包括头发的颜色也可以改变,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背后隐含的是什么问题:我是谁?我从那里来?我才知道我要到哪里去。
高更《我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谭波:我觉得这个很难回答,需不需要寻找东方性?我觉得肯定是需要的,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五四文化运动开始,其中一个议题就是中国如何应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我们要创造自己的东方素养,中国独有的现当代的文化、艺术,掌握自己的话语权。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如何发展自己国家的文化,像向京老师所说,其实不仅仅是中国遇到这样的问题。
观众提问
提问:我想问一下谭波老师一个八卦的问题,梵高跟其他与他同时代的艺术家关系也是很不好吗?
谭波:他在巴黎的时候,跟劳特累克关系挺好,两个人经常去咖啡馆喝酒,跟高更也是短暂好过一段时间,两个人曾经一起住在阿尔勒的黄房子,一起创作过几个月。但是任何人跟梵高住在一起久了,估计也会被他搞疯,因为他不注重个人卫生、狂抽烟狂喝酒,东西乱丢乱放。有时脾气挺暴躁,他很害羞,他不知道怎么样跟人正常交往,所以他常常会无理由的让人觉得他好像在发脾气。他跟弟弟提奥一起在巴黎住的时候,后来他弟弟也受不了他,以前提奥很多朋友,会来家里做客,因为梵高住在那儿他的朋友根本不敢上门。
梵高《夜间咖啡馆》
提问:我想问一下向京老师,现阶段您个人创作,面对这么复杂的世界更倾向于表达的东西是什么?
向京:别问我现阶段,现阶段是失语状态。这不是跟整个艺术史有关系,中国艺术史没有问题的,像我们现代史都没有特别好的被书写,当代艺术史更没有被好好的书写过,这确实会对我们的艺术生态,对我们的艺术家创作有很大的阻滞。而且这个时代会特别容易养育大量的消费者,我们又常常会碰到很多的机会,艺术没有被很好的在学术工作里面消化掉,马上转化为特别容易被听懂的语言教给普罗大众,这是艺术生态面临挺困扰的问题。
其实常常会比较感动,包括我愿意参与这样的活动,其实也是感谢美术馆的功能,这些都是私人藏家,用他非常有限的知识、精力试图做这样一个场所,把自己的收藏、热忱跟更多人分享。我经常会说,你做一个美术馆就是一本艺术史,中国应该有各种各样的美术馆,大大小小的,最好是小而美的多一点就更好了。西方、欧洲到处都是,真的随便一个什么小东西就做一个美术馆,这就是一个关于线索的梳理,让我们在混乱当中找到某种秩序,找到接序的血脉和文化逻辑,这都会帮助我们接近艺术本身。
松美术馆外景
更加深入详尽的内容请关注《艺术商业》4月刊。松美术馆首展《从梵高到中国当代艺术》正在进行,是不容错过的观看中外世界级大师画作的机会,展览将持续至3月24日,还不赶紧行动。
更多现场图片
佳士得印象派及现代艺术资深专家谭波(左)与艺术家向京
“松间对话”对谈现场
“松间对话”对谈现场
“松间对话”对谈现场
嘉宾交流
嘉宾交流
“松间对话”对谈现场
嘉宾合影
万叶集为本次对谈创作了一束以梵高《雏菊与罂粟花》为灵感的花束,向梵高致敬。花束主要创作方式是临摹,采用了罂粟科虞美人、银莲花、洋甘菊与飞燕草,希望可以复现出梵高花瓶里花束构成。
特别鸣谢宣明典居为本次活动提供玫瑰椅
“玫瑰椅”流行于中国古代明清期间,因其外形纤巧秀美、富有灵气,所以被文人雅士所喜爱。除此之外,由于玫瑰椅仅供端坐,能够很好的衬托出东方女性的优雅和端庄,这使其逐渐演变为中国传统家具中唯一有性别指向的一把椅子。宣明典居历时三年,改版十余次推出的这把玫瑰椅,在原有的基础上强化了几何造型,使得其更加简练、理性,柔中带刚,刚柔并济,更契合新时代女性独立、知性的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