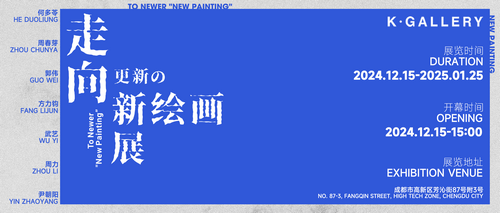《岸边小筑》 薛松 50x100cm “重塑经验”展览现场
从历史性的方面考掘当代绘画的“不安感”,先谈及观看方式,即是我们如何看的问题;再者,画面本身闪耀的独立性责任,涉及在美学观念上的使命感。作为视觉艺术的两个秘密,薛松的创作竭力地呈现了秘密发现中的普遍意义。
《繁花似锦奔前程》 薛松 150×200cm 布面综合材料 2010
一、观者寻找一种陌生感
初看薛松的绘画,远看取势,近看取质。最后停留在阅读和思考的层面上。画面凸显的时代元素、材料和它们的拼贴方式,给读者留下不确定性的空间。取材的意义在读者的浮想联翩中,为什么要以传统的取境方式,时间上和行为上它们贯穿创作的始终吗?传统形式和现代方式是如何相撞的,焚烧的意义是什么,与“种植”相比,它是否具有摧毁性?那些响亮的符号,标志、明星、摇滚、书法、人民等,在时间的长河中,能否从先锋观念的意义上下架,成为一种经典美学。我们看到的形象,在脑海中成为记忆,不论有没有对记忆形成加工,多年以后,当记忆成为追忆的时光,它们是否会像小说家那样,变成伟大的加法行动。不过,这在艺术家那里,已经实现了这种行动,将过去和当下的记忆,进行敏锐的捕获和重读,努力将它变成一个对公众有现实意义的行为。
《货币符号》 薛松 250×180cm 布面综合材料 2010
薛松作品的显著陌生感,来自细处的实写和虚处的果断性制作。每个可见形象的轮廓中,都展示着更可读的符号或标志,一种无限性置于其中,例如背景的英文字符。远看它们是杂乱无章的,近看又是根据画面形式的秩序来安置的,在一定的构思规则中散发写意的意味。另外的矛盾是,密集的拼贴小实物与大的物体的对比,这中间的分辨性轮廓又带有坚硬感,联想坚实的大地和现代社会封闭的机械复制,它们具有同时代的气质。这是艺术家最敏锐俘获信息的地方,也是艺术创作灵魂的需要。建筑是统一硕大的、单色人物像北方的山脉、肖像具有纪念碑性、传统山水被解构成平面结构,艺术家将一个具体的因素放大,进行描述,再在这个具体因素上寻找与时代相关的重要形式,在核心的经营力量上,其他地方反而体现某种的“便捷”性处理。精力在具体内容的描述上有所分离,虚实相冲又抱合,体现中国古典美学的传统精神。
画面还彰显的一种陌生感,是人物的木偶状表现。区别于蒙克式的呐喊,情感的直接爆发。但理解上的相通的地方,都有着深不见底的情感积蓄,好像总是差那么一点点就要爆破,将绝望隐含其中,出于礼节的“温文尔雅”,又是现代社会的典型情绪。并且还带有复制感,机械性的、可操作的、数据一般。有别于传统的唯一性。他们是集中在一个区域或者时间里可替代的,就像每天8小时的规律工作,集体的无意识症候。薛松的作品诉说了他的批判。这让人想起莫奈的《酒吧间》。绘画的创作,用形象诉说了世界的荒诞,无法理解,始终如一。在人物刻画中,有的面容没有具体的五官,甚至没有眼睛,都市男女呈现呆滞的表情,色彩斑斓又极端冷漠,且你看向他(她)的时候,他(她)也在看向你。观看的人与被观看的“人”透露着情感的交流。
《时尚男女》 薛松 2(200×100)cm 布面综合材料 2009
《紫气东来》 薛松 150×100cm 布面综合材料 2018
二、解读和误读
解读的功能在画面中并没有消逝,反而还是加强的。现代派绘画希求哲学的介入,文本的阅读与说明。图像具有象征意义,连接某种亲缘关系,从形式上的一脉相承。过去是讲述一个故事,将事情的缘由、发展和结局一一呈现,暗示人生的道理。如今这个封闭的思路被现代派绘画消解了。它不诉说故事,始于无端,终于描述。更多的是直接呈现,但呈现的方式带有隐喻、自由、偶发的因素。它们平常在生活的每个角落,本身并不负担着某些人类的责任,但艺术家将它们取材,在不改变其物性的前提下,再造或进行二次创造,变成一件带有精神的物什。于是存在的完整性必然需要解读,也同时避免不了价值性的误读。这是创作中最闪耀的时刻。
唐 韩干《夜照白》 纸本设色 纵30.8cm横33.5cm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艺术模仿现实,还是现实模仿艺术,这在文学史上是个有趣的问题。柏拉图倾向前者,一些激进的天才作家说出后者才是秘密所在。薛松的作品中强烈的现实因素,并且伴随偶然现象,就地选取的文件中,还包括艺术史中的熟悉影像。在形象本体中,它们是审美的,产生着视觉上的愉悦感受,例如徐悲鸿的骏马。马在中国绘画史自秦汉便有高峰,从雕刻到绘画,无一不体现中国文人的既现实又浪漫的情怀。一个审美事物的出现并不是偶然,它在反复的历史性研究、比较、实验中诞生,例如若是换做元代赵孟頫的马,那种文人情怀、清癯淡雅、线条细瘦的特征就未必适合当代绘画的语言,或者艺术家可掌握的语言。再早的唐代画马大家韩干,他的《照夜白》名闻天下,但那形态更多的取决于水墨的本质和趣味,在当代绘画语言中就具有了局限性,当然并不排除特殊的现象。徐悲鸿近代水墨的马,在装饰意味中有其重要的特质,这与唐宋文人画的高峰品质占据了两个不同的审美观念。徐悲鸿的马和水墨意味都更为直接夸张一些,写意的特性使得它们更为亲近大众读者。淡雅和奢华是一个社会的两个方面,不存在单独讨论的意义。薛松采用了这个时期的这类风格符号,样貌虽然夸张、热情奔放的,但在严谨的拼贴技术中,又读出了情感的克制,甚至淡漠。在原本写意的轮廓中,填充了严谨甚微的材料排列。另外一个动物老虎,有年画和版画的味道,将原本具有上海奢华气质的绘画取材于一个最为平凡的民间画种中,增加了观看和阐释的趣味性。画面中老虎的表情是木讷的,与同为观众熟悉的、奔放的烈马形成鲜明的对比。
有解读就生发误读,误读中生长另外的解读成分。事物换一个说法或者讲述另外的故事,它本身就作为观看的意义,甚至批评性的,达到二次创作的领域。作品“符号”系列,更多图像处在当下的,它们并未过时,因此理解的方向也是无限的包容,像货币符号。符号轮廓中进行了纸质货币的拼贴,并且来自各个国家的货币种类,它们具有不同的颜色、人物、大小,其本身就有审美的功能,同时又唤醒了人们内心深处共同的语言。潜在的话语。一种我要说、如何说、就这样说的冲击力,同时直接的面貌又不浅尝辄止,它们均衡地分布在画面中,平铺直述,反而具有了不可替代的力量感。潜台词充满幽默和严肃,又拾遗了大众的话语。另外的“加减乘除”的符号,影射复制工程之无限,也表征时代某些方面行为的高度密集,不可计量。
《向梵高致敬》 薛松 100×100cm 布面综合材料 1988
三、物性材料
作为拼贴,它为语言和观念服务。艺术家访谈录中,提及到工作室曾遭遇一场大火。但在大火之前的实验性创作中,已经尝试了绘画语言的多种可能性。画面诉说着渴望性的探索,寻求解决真理性的新观念或者新阐释。这就为后来的新语言做了思想和行为的铺垫。失火事件发生在1990年,为方便理解风格成长的过程,可以择事件之前的绘画作品与风格,并进而探索其中的观念倾向。
1988年(23岁)《向梵高致敬》、《无题》两件作品还有着西方现代派风格的影子,处在摸索的时期。前者是二联画,分四个绘画的块面,已经有了超现实和拼贴的影子,各个元素的组合很多出于无逻辑、不相关的安放。后者《无题》视觉上更容易分辨出是纯绘画的,痛苦的面容周旋在几枝干枯的树杈中,流露生命死亡的气息,或者说是:激情。可以说这时期的作品还处于漂泊状态,风格和观念的归属感不那么显著,像游子的心灵。1989年(24岁)《迷墙》、《无题系列》,前者也呈现了片段的布局(2012年“与罗斯科对话”系列已走向成熟),《无题系列》有明显的超现实感受力,还有表现主义的视觉印象,用笔粗犷,形象呈不安分的混沌状物体。1990年也是《无题》,已经有了焚烧书册的块状物,重要的是影像和书法嵌入其中,还有青花瓷的样式,说明开始了探索中国文化的启程了,体现个体的民族性和本位感。同样现代派的激情还存留在画面。据此分析,1990年处于创作风格转折的重要年份。92、94年的作品就有了自主的拼贴和多元材料的运用了,书法文化占据重要的位置。
《与罗斯科对话之五》 薛松 80×60cm 布面综合材料 2012
《与蒙德里安对话之四》 薛松 140×160cm 布面综合材料 2012
艺术家本人说:火把身边的书本、画册、杂志、报刊及其他印刷品从有形中解体,这些材料了神形走出了框框,隐含了大量原先不见的信息。创作便从可见到不可见的信息中拾遗自己的语言,以综合材料为媒介,重建一个领悟的艺术境界。这里隐藏了一个文学观念的秘密:隐喻的作用。焚烧带有仪式感,例如祭奠、拜祖、告别等社会习俗,甚至还会联想宗教。古老的人类篝火欢庆、商议大事,火作为甲骨文象形字,昭示生命之光。燃烧的过程中,灰烬作为结局呈现出的物性,就有了无尽的所指。但它的本身就只有一个概念:燃烧剩余物。出于哲学和诗的传统功用,在它身上就发挥了无尽的阐释,灰烬是一,也是一万。由此,物之先是大量的、有形的、可见的信息,经过艺术家的主观焚烧,变成了另外的物性,不可逆转的、彻底变性的物态。再由这个可见的东西,隐喻的力量赋予它承载一切的信息,包括焚烧之前的信息,这个转化的过程达到了真正的,中国道家学说中的“生万物”。也通过这个方式和桥梁,艺术家传达当代社会中的城市秘密,他本人说的:上海的秘密在于它没有历史。创作从无端开始,以自己的语言无限复制一种单一的话语,又走向无限的阐释。
四、绘画的传统性
作品中的传统书画形态是整体风格的重要方向,艺术家本身曾习过水墨山水。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记忆由来已久,它存在创作中的一切行为中。包含了秘密的发现。以“与罗斯科对话”系列为参照(2012年)。作品上的山水形象并不复杂,多是一个枝头、一处人家、一朵祥云,继承了中国绘画的精神:得意忘象。罗斯科的抽象绘画,单纯的色彩散发威严、仪式、纪念碑性的感受,与中国禅意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薛松稍微改变了一下形式,将色域变成了拼贴的具体形象,但远观的整体感受力还是不变的。当代艺术理解观念出发,到达另一个观念的发现,解决了绘画本质的命题:绘画过去是什么,现在是什么;绘画这个地域的思想,绘画那个地域的思想;从历史而言,艺术如何建一个桥梁让观众便于理解经典的魅力。同时在局部的细处,大量的碎片又承载了社会的数字化、信息化、复制性特征,以反讽的方法,批判性地描绘了城市的现状。2013年的“对话蒙德里安”系列也传达了视觉由简约到密集的矛盾,打通了中西思想的共通性。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不仅如此,画面甚至只采用了教学材料中的《芥子园》图像,采用人们耳熟能详的范式,来传达观念的所思所想。
《罗斯科上的芥子园之七》 薛松 80×60cm 布面综合材料 2012
在过去,中国绘画的历史以笔法的创新来论大师,例如皴法始于五代,之后便成为分辨绘画风格的主要特征。而现在,创作摆脱了技法的传统束缚,以观念的重新阐释和解读为重要辨识方向,对绘画物种的本体的认识,同是理解当代艺术现象和本源不可趋避的问题。
薛松
“重塑经验”展览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