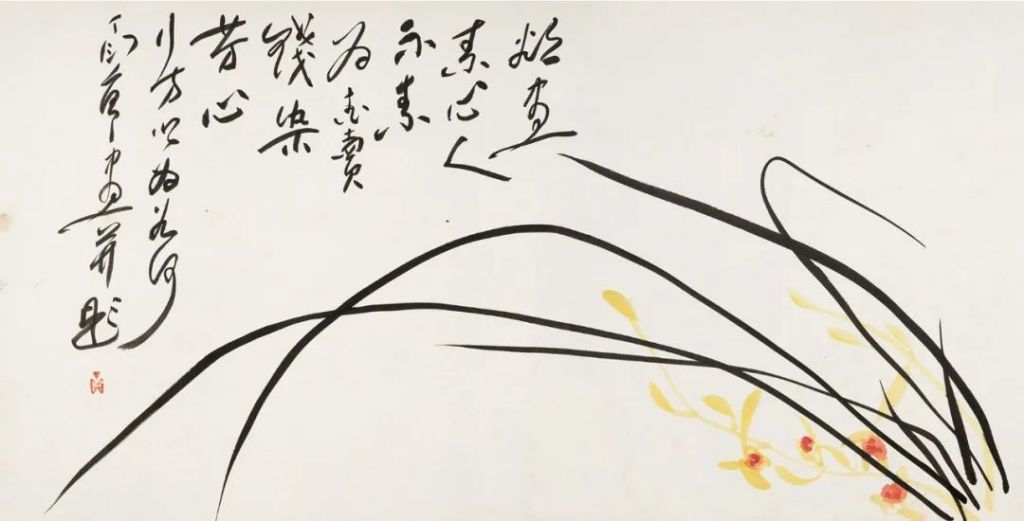广东历来是融汇中西、创造时代艺术的文化重镇,除主张折衷主义的岭南画派以外,更涌现出林风眠、关良、丁衍庸等一代大家。而与林风眠早年留法经历不同,关良和丁衍庸均在日本大正后期留学东京,二人先后入读同一学校(川端研究所),甚至师事同一老师(藤岛武二),彼此乃知交,最后同样选择回归中国水墨作为创作的归宿。
1940年代,丁关二人同在大后方的重庆国立艺专共事,作为现代艺术家阵营,与林风眠、赵无极、倪贻德等通过“现代绘画展览会”“现代绘画联展”“第一届独立美展”等致力推动“洋画运动”,是中国现代主义美术最重要的推动者。
抗战胜利后,二人不约而同选择京剧人物作为主要的创作题材。虽在应用材料、强调变形以及笔墨意趣等方面皆有相近之处,但在创作呈现上却各异其趣。关良的风格形神兼具,戏味、画味、趣味俱佳;而丁衍庸则逸笔草草,藏巧于拙,于马蒂斯式的拙稚中演绎人生百味。二人在线条与墨彩的融汇中,表现出以往文人画所难以传达的意蕴,开拓了画坛一个新天地。
 关良
关良
关良先生有深固的西画根底,同时更深入国画的堂奥。他认识绘画内在精神的可贵,以西画作躯壳,国画作灵魂,以西画单纯明快,坚实浓郁的技巧来表达国画恬静、洒脱、淡雅、超逸的神韵,企图创作一种时代的、前进的、发扬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新绘画,但他绝不是“折衷主义”者,因为他的目的在于创造。
——郭沫若
郭老一席话精准捕捉到关良油画艺术之精髓,实则,反用于关良国画艺术中,亦然。在中西流派纷呈的艺术探索上,关良孜孜以求,融会贯通,领悟出中西艺术在画理上的殊途同归,从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划时代的独特图式。以稚拙天真的绘画风格和中西调和的艺术理论追求,在近现代画家群体中脱颖而出。
 LOT 436
LOT 436
关良 花果图
立轴 设色纸本
1977年作
127×66cm
华艺国际(广州)2021春季拍卖会拍品
野兽派的艺术理念对关良颇具影响,其花果图擅以西方之形写东方之韵,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粗犷与细腻兼备,稚拙与鲜明并存。作品精细微而臻广大,往往尺幅偏小,以小见大,然本幅足有七平尺余,实为少见。
 关良 花果图 局部
关良 花果图 局部
画面中花瓶置于中左,瓶身绘以花鸟,蕴藏“喜鸟报春”的美好祝愿;瓶上五彩斑斓的各种花卉显得格外醒目,错落有致又缤纷烂漫;瓶侧置放的果碗和玩偶与瓶花主次分明的立于台面之上,形成稳固的三角形构图。
 关良 花果图 局部
关良 花果图 局部
是幅作于1977年春,为良公晚年得心应手之作。其取材西方静物画,一定程度上借用了西方绘画的明暗、空间与阴影处理,但并没有过分拘泥于比例、透视,反而将中国水墨画的散点透视自然融入。
 关良 花果图 局部
关良 花果图 局部
其笔墨简练而不失笔趣,古朴而又鲜明,体现出传统中国画独有的平淡天真。再者用色、用墨大胆夸张,亦明显带有野兽派绚丽大胆的色彩,可以看出画家贯穿中西,力图推陈出新的探索精神。
 丁衍庸
丁衍庸
丁衍庸早年对现代主义野兽派尤为倾心,从20世纪30年代起,开始研究朱耷、石涛等清初具有强烈个性的传统画家,其绘画既借鉴马蒂斯绘画中的形式语言,又继承八大山人的“金石用笔”,从而摆脱了中西画彼此界线森然的束缚,最终形成极富个性的艺术风格,被誉为“东方马蒂斯”和“现代八大山人”。
 LOT 445
LOT 445
丁衍庸 花鸟
手卷 设色纸本
1976年作
46×652cm
说明:赵行方上款。赵行方,丁衍庸弟子。
华艺国际(广州)2021春季拍卖会拍品
本幅《花鸟》写于1976年,逾6.5米长卷,实属珍稀。时画家虽届古稀,仍精神抖擞,铺纸下笔,全局了然于胸,构图舍繁取简,布景主次分明,运笔准绳,疾速凌厉,线条长而含韧劲,精力盈贯于画中。
 丁衍庸 花鸟 局部
丁衍庸 花鸟 局部
展卷披览,图中所绘幽兰、墨竹、红梅、秋菊、锦鸡芙蓉、草蜢海棠、雏鸟桃枝、翠竹、牵牛螳螂等十品,构图上或对角分割,或作左右比衬,或作扇式展开,或作纵列掩映,枝叶舒卷穿插,花朵主次向背,均有巧妙安排,随物赋形,各极其趣,一派天成。画家借传统题材之旧瓶,注入文化接续之新酒,纵放写意状之,时代精神现诸笔底!
丁衍庸一生追求者正是这种活泼自由、不受绳规拘限的创作心境精神。他从不扭曲己志以屈从世俗,从不拘其创作精神境界之超脱,亦从不规限其画中天地之包容广宇。观此近30平尺巨幅,笔力雄健恣放,取法八大之余,却舍其冷傲孤绝,洋溢了乐观通达的热情。其心与物化,无穷出清新者也。
 丁衍庸 花鸟 局部
丁衍庸 花鸟 局部
尽管自上世纪50年代起关良与丁衍庸在地域上分隔两地,但二人在西洋艺术的个性表现与传统文人画的重性情之处,和西洋艺术的形式美感与传统中国画的笔墨情趣之间,寻得中西艺术表现之共通,为中国画的发展开启了更加自由且别具一格的笔墨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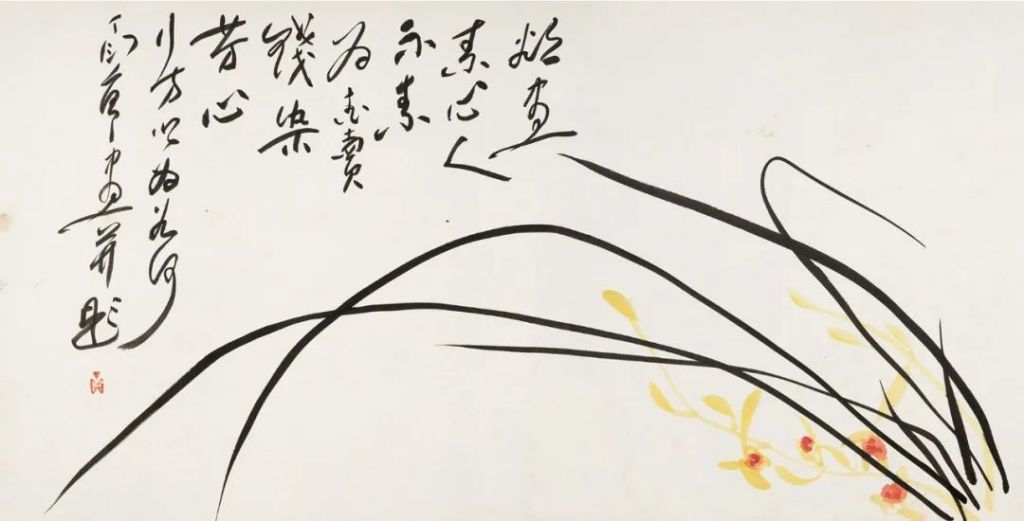
 丁衍庸 花鸟 局部
丁衍庸 花鸟 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