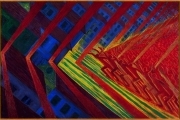每个人都会在生活中不经意间和艺术相遇。一张画、一件雕塑、甚至是一把椅子,人人都可以欣赏艺术,但了解艺术史的人会有更深的体会。
如何在浩如烟海的艺术长河中了解每一个流派、不同艺术风格及其代表艺术家?对于初学者来说,会常感无所适从。99艺术网会在艺术史专栏中系统地以中国艺术史和西方艺术史两条线索,以不同的艺术门类、艺术流派为切入点,深入浅出地向读者介绍国内外著名的、具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以及他们的艺术作品。
现代艺术因许多原因被讨论、被欣赏、被争议甚至被质疑、被审查,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它的外表看起来不像任何“真实”的东西。
人作为视觉性的动物,其视觉上的认知观念早已被社会建构,大多数的人们更愿意接受具象的、模仿自然的艺术,在他们看来这才是真正的“真实”。而那些抽象的、几何化的艺术,在他们看来是不现实、不真实的。
图片来源于网络
然而,康斯坦丁·布朗库西利用艺术挑战人们固有的认知观念,打破学术传统,帮助人们塑造了非具象性的现代主义原则。在他看来,“有些白痴把我的作品定义为抽象,而他们所谓的抽象才是最现实的。真实不是外在形式,而是观念,是事物的本质。”他将这一观念融入自己的艺术作品,将其作为艺术创作的核心,最终行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1876年,布朗库西出生于罗马尼亚的一个偏远的农村。家境贫寒,9岁时便离家出走,在附近相对富裕的地区打工来养活自己。18岁时他在雕刻方面的天赋被一位实业家发现,并将他录取到克拉约瓦工艺美术学院。之后,布朗库西就读于布加勒斯特美术学院,在那里接受了雕塑学术培训。在解剖老师迪米特里·杰罗塔的指导下,他的《écorché》作品在1903年成功在罗马尼亚雅典娜神庙展出。虽然这只是一项解剖学的研究,但也预示着布朗库西之后努力揭示本质的艺术作品并不仅仅是对外表的复制。
“就像一场梦,默默地激荡着石头或木头深处的精神,我让我的材料表达了无法表达的东西,它背后的想法。
——布朗库西

图片来源:Christie's网站

图片来源:Christie's网站
01
“大树下什么也长不了”
1907年,布朗库西在毕业后被聘为雕塑大师罗丹的助手。对于一个有抱负的雕塑家来说,在大师的指导下学习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但仅仅两个月后他就离开了罗丹工作室,他说:“大树下什么也长不了。”

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布朗库西看来,罗丹用黏土或蜡制作雕塑模型后,让助手将其转化为青铜或大理石的间接雕刻方法让他感觉是在欺诈。这种方法如同工厂的批量生产一般,产品并不具有唯一性,它可以被其他相同的商品代替。显然,这使得作品本身独特的艺术价值在间接方法的转换过程中消失。

图片来源于网络

图片来源: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网站
在罗丹的雕塑中,艺术家将人物姿势所讲述的故事和表达的情感表现到了极致,但却忽视了材料本身固有的属性——纹理、曲线、平面、质感——以及它们与周围空间环境的相互作用。布朗库西发现并抓住这一问题,他认为一件艺术品的意义不在于它的外观,而在于隐藏在材料中的基本能量,尊重和揭示木材、石头或青铜所固有的形式,并释放它们的力量是雕塑家的责任。
“一个假装复制自然的东西只能是复制品。”
——布朗库西

图片来源于网络
02
浪子回头
浪子是在新约圣经中关于一个挥霍无度的儿子的寓言故事。他要求从父亲那里继承遗产,然后离家出走,奢靡享乐地花光这一切。多年后,他变得越来越穷,同时也慢慢地开始领悟、忏悔。最终,他回到家,扑到父亲脚下,祈求宽恕。

图片来源于网络

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罗丹的手中,《浪子回头》的雕塑变得有力而坚定。高度反光的青铜雕塑呈现出崎岖的表面,人物扭曲的姿势、拉伸的张力传达出悲伤和痛苦的忏悔。这件艺术作品的情感是由内而外的、爆发式的宣泄,是戏剧性故事达到高潮的一瞬。
与罗丹的作品不同,布朗库西《浪子》这件雕塑作品是隐秘的、安静的,人物的力量内聚在下跪低头的动作之中,这是一种无声的忏悔。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为了能够最大程度地将材料与主题联系起来,布朗库西选择了一块从旧橡木房梁上切割下来的废弃木块,上面还带有历经沧桑的裂纹。艺术家用锯子将木头锯掉,只留下三根不同形状和角度的柱子作为四肢,支撑着庞大的不规则的身躯。
“像奴隶一样工作,像国王一样指挥,像神一样创造。”
——布朗库西
一个前来赎罪和忏悔的人,背负着圆顶弯曲的重担,浪子低头无眼,目光向内沉思,左手和膝盖着地,所有的情感和能量都是向内集聚。石灰石的底座将它的忏悔向前投射,前面的空白空间,是为他的父亲预设。这样的设置不仅给观众留下更大的想象空间,而且也突出了浪子的虔诚和孤独,以及正在等待着父亲的回应。

图片来源于网络

图片来源于网络
雕塑的平衡、不对称和各种体积的复杂性归功于布朗库西对非洲艺术的兴趣。《浪子》是布朗库西最早以原始状态保存下来的木头雕塑。
“一个真正的形式应该暗示无限。表面应该看起来好像它们永远存在,好像它们从质量中出来,进入了某种完美而完整的存在。”
——布朗库西

图片来源于网络
03
吻
布朗库西创作于1916年的雕塑《吻》与罗丹创作于1882年的《吻》,都展现了两个恋人相拥亲吻的状态。但罗丹的雕塑人物栩栩如生,石头的质感如肌肤一般柔软,如同真实的两个坐在岩石上的恋人。而布朗库西的雕塑则是两个恋人拥抱的块状形状,人物就是岩石。这两件作品从美学上几乎没有办法比较,它们看起来完全像是来自不同的世界。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与罗丹动人、肌肉发达的人物不同,布朗库西的《吻》是块状静止的。毫无疑问,这对夫妇已经完全与那块石头合二为一。他们扁平的手臂、手以及身体紧紧的相互缠绕,两人对称的发际线形成单一的弧线,男人卷曲的头发齐肩,竖直的纹理垂直向下,而女人则长发及腰,侧边头发的纹理倾斜45°向耳后延伸。他们之间只有一条刻线将其隔开,如果这条刻线消失,它们就如同一个人形,在嘴唇接触的那一瞬间就已经融为一体。

图片来源于网络

图片来源于网络

图片来源于网络
英国《独立报》已故的首席艺术评论家汤姆·拉伯克曾评论道,将这两件作品放在一起探讨暴露了试图定义什么是一件“好的”雕塑作品的缺陷:“在罗丹作品面前,布朗库西的作品看起来如此荒谬,荒谬的粗俗,荒谬的难以言表;但当站在布朗库西的作品面前,罗丹的作品看起来同样荒谬,荒谬的如此浮夸,如此直率。那到底什么是崇高,什么是荒谬,这只是一个品味问题。”

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布朗库西《吻》这件作品中,布朗库西对现实主义的技巧并不感兴趣,也并没有试图要超越罗丹的技巧,也不意味着他的雕塑看起来更像两个接吻的恋人。相反,他迫使人们与一块大理石对话,使观众思考人类爱情的结合意味着什么。
“简单就是解决复杂性。”
——布朗库西

布朗库西喜欢引用法国诗人尼古拉斯·布瓦洛的一句话“没有什么比真实更美丽”。这里面的真实不是人们肉眼可见的真实,而是一种思想的呈现,是对事物本质的理解。正如布朗库西一直坚持认为的那样:“真实不是外在形式,而是观念,是事物的本质。”他的作品一次又一次地表明,对美或真实下一个定义是不公平的,甚至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