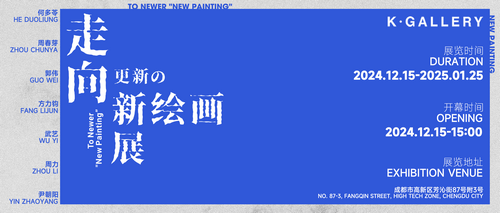德语文学出身的苏伟,博士毕业之前,一直在德语文学和当代艺术两个领域之间切换。而他最早进入到策展领域也是从翻译和写作开始的。

苏伟
策展人、艺术史研究者
今年7月,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两场具有艺术史意义的展览——“几何:赵大钧绘画实践的基本线索”和“回到何地:1993年之后的王广义创作草稿”。这两个大型个展的策展人都是苏伟。
这两个展览都与苏伟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长生涯”有关联。“长生涯”关注的是1949后的创作个体,以同代人的视角关注他们在漫长的艺术生涯中的关键片断,或是未被充分论述和遮蔽的创作线索。在苏伟看来,这个项目是针对今天的艺术史现状而展开,意欲挑战或重新审视当下艺术史的盲点、缝隙等。“1949后”这一议题也是苏伟当下工作的一个核心,试图“谨慎地摸索‘前三十年’与今天之间的对话。”这也是我们这次访谈的一个重点。
深入从事研究和策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对这份职业和工作本身的审视。作为艺术生态中的重要一环,策展人的工作基于的是艺术在历史中的演变和其与全球艺术语境的互动。在“前三十年”的中国当代艺术中,需要重新审视的也许不仅是艺术创作的历史,也是艺术史写作和策展人在不同时代塑造的现实情境中的思想演变的历史。
苏伟在采访中数次提到的对自己的一些惯性思想的反省,也许可以为我们重新看待中国当代艺术策展提供一些新的角度。
1
中国当代艺术“前三十年”
与今天之间的对话
Q:
您目前的研究方向是什么?是如何在策展工作中体现您的研究成果的?
苏伟:
我最近这些年的工作一直在关注 “1949后” 这一议题,将“1949后”视为一种当代情境,通过一系列聚焦于我挖掘的艺术史新议题和艺术家个案的展览项目与写作——包括最近策划的 “几何:赵大钧绘画实践的基本线索” 和 “回到何地:1993年之后王广义的创作草稿” 两个个案研究展览,以及2019年策划的 “动情:1949后变局中的情感与艺术观念” ——谨慎地摸索“前三十年”与今天之间的对话。

“几何:赵大钧绘画实践的基本线索”展览现场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2024.7
“前三十年”艺术实践受制于极端的政治条件而体现出两极化的特征,所以基本的挑战是,如何在政治/艺术、集体/个体、形式/内容这些被给定的框架中重新叙述艺术及其思想的脉络;以及在这种重新描述中,如何寻找到“前三十年”中被压抑的部分或者无意识的部分,勾描其与今天的对话。
这样一种工作其实还是在曾经的“全球化”和今天的“去全球化”背景中发生的,它诉求于“本地”、“内部”,但这种诉求与“全球主义”之间不是一个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希望在提出、辨认特殊议题和具体情境的前提下,反复体会普遍与特殊的张力,让特殊议题和具体情境变成一个思考的基础,而不是把本地作为“全球主义”之内的替代性实践。

“几何:赵大钧绘画实践的基本线索”展览现场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2024.7
当然这样一种工作方式也是一个走钢丝的过程,它很容易让人陷入到再次神圣化“前三十年”的情绪中,或者过于轻易地持有某种不经思索的“异见”姿态。
在这个“古今对话”的过程中,我越来越体会到这种对话 不全是由事实性的线索勾连的,它极端地要求作为一个研究者的“我”的参与。 “我”不仅是一个历史之外的研究者,也必须是一个参与到其中的行动者,“我”的想象、“我”的生活实践是处理这些历史问题的倚仗。除了把“我”作为前提,两个最基本的问题是: 如何在揭示艺术制度、社会情境与人之间的互动的同时,保持一种伦理的目光 ,而不是如今天在中国盛行的、有的是带有投机性质的左派研究一样,仅仅满足于用欧美左派学院、学科训练出的分析方法,完成一种近似于文化经济学的梳理,进而把“怀旧”强行书写在未来之中?由于这一持续到今天的历史的复杂性,它不仅牵涉到真相与谎言的问题,也牵扯到(后)社会主义文化的实存与虚构的问题,那么,如何在研究与想象、研究与行动之间寻找到一种本质的平衡?从这两点上讲,这样的研究要求“我”去进行近乎于“隐秘书写”的工作: 它内含的科学分析工作,必然地与这一仍亟需祛魅的、正在进行的历史的正义性和伦理问题,其从未完全显身的思想基础发生碰撞,而这种碰撞往往使研究者陷入不能自圆其说的境地,也是我经常在工作中面对的情况。 身处于交叠着个体、公共与历史维度的情感结构的深层之中,恐怕也很难做到绝对的清醒吧,不过这也许正是带有实践性的研究能吸引人、触动人的地方。

“回到何地:1993年之后的王广义创作草稿”展览现场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2024.7
在我的观察中,1949至今的历史是以不连续的连续形式展开的,而其中的人和作品,都不能被视为完整的、自觉的,它们从历史的深处召唤后来者的回应,要求后来者必须做出重新连接、兼具批判性与创造性的补充以及本质上的重塑。 1949至今的历史进程中,张力处处可见 ,我一直记得翻阅《美术》杂志浏览标题时,所感受到的那种充满紧张感和紧迫性的讨论态势。
不过,虽然时代的张力巨大,除了整一的艺术制度和政治意识形态是统摄性的—— 这一统摄性也在所谓的短20世纪和今天投下了漫长的阴影,这段艺术历史所留下的思想线索,无论是在创作个体层面还是在其历史被应允展开的地带,都呈现出完全的碎片化的特征。 比如我们今天经常提及的社会主义艺术中的“现代主义”、“功能性”或者即使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样的议题(有趣的是这个议题本身是空洞的,它只是在50年代短暂地被确立过,而在之后漫长的时期内被视为一个要“反思”的标靶),都呈现出 “落地即转身” 的形态,从未以一种有机而具有时空连续性的完整形态向我们呈露。和这些“碎片”、“断章”的相处,是研究者的日常,在这个情形下,“我”也只能通过想象、行动和研究的结合来处理这一碎裂的、缺乏实质性的思想基础的当代史。

“回到何地:1993年之后的王广义创作草稿”展览现场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2024.7
我尝试在策展和写作中摸索叙述“1949后”的可能性, 这种摸索本身面临着双重挑战: 既不是重新神化社会主义艺术的历史、并从中得出中国的艺术领域早已全球化或者“前三十年”的艺术实践比今天更具主体性这样的结论——这在今天的艺术学院中广为流行;同样也不能仅仅将“重新发现”作为唯一的工作动力,并以此召唤理想化的“个人主义”创作、“中国气象”的历史线路或者超然独立的“艺术作品”。
Q:
在您这些年的策展工作中,有哪个或哪几个展览项目对您来说是意义非凡的?
苏伟:
2012年我联合策划的深圳雕塑双年展 “偶然的信息:艺术不是一个体系,也不是一个世界” (深圳OCT当代艺术中心),这个展览启发了我对90年代中国艺术实践的观察,很多当时和后续的讨论也启发了我去从全球史的角度理解中国的艺术和知识生产; “动情:1949后变局中的情感与艺术观念” (北京中间美术馆,2019年),从这个展览开始,我希望把“1949后”视为一个连续的当代情境,去研究和辨认包括自己在内的艺术实践,它们的思想基础是什么,它们与时代精神之间不可能完成的交接是什么。


“动情:1949后变局中的情感与艺术观念”展览现场
中间美术馆,2019
“1949后”的提法,也受到了文学史家洪子诚先生的教诲和影响,但稍有不同的是,我把重心更多地置于作为历史实践者的研究者这一边。这个展览将艺术视为一个复杂的历史情感结构中的核心地带,通过它,那些公私之间、集体与个体之间、时代与艺术之间的碰撞得以发生;也是通过“情感”,一些有限的、具有与今天之间对话潜力的思想脉络才在某些特定的宽松时刻释放出来。另外,这个展览也是一种不全部基于“历史”的历史研究,正如上面所说,我不认为所有我勾连的线索或者甚至是我试图通过想象、非事实的历史提出的线索,能够一直在一个坚实的实证的历史逻辑里或者文化理论逻辑里成立。不能自圆其说,只能通过研究、想象和行动的实践推进建立这一艺术历史与今天的关联,因而做这样的研究的人就不能被称为任何意义上的“历史学家”,而只是“历史研究者”。

第七届深圳雕塑双年展
《偶然的信息:艺术不是一个体系,也不是一个世界》
深圳OCT当代艺术中心,2012
同时,我现在在联合策划和展开一个名为 “海岬上的瞭望” 的项目,这个项目的题目衍生自“动情”展的一个小章节,也是诗人艾青1954年拜访聂鲁达之后写下的一首诗的题目。项目以工作坊的形式推进,通过委任这一区域各地的研究者考察东亚、东南亚以及南亚20世纪50-80年代的跨区域艺术交流,形成一种不基于某一理论预设(比如全球南方或者后殖民)的开放的讨论框架。
开展这个项目,最初源于我对中国20世纪50-60年代艺术内外交流的观察,尤其是其在与他者的相遇中体现的自我投射、自我想象的特征,这一特征当然是兼具封闭性和主体性的。这种特殊的“主体状态”通过中国文艺得到体现,也让我尝试从封闭的中国移步开去,看看“冷战时期”亚洲其它区域建立主体性的努力,尤其在这种努力遭遇文化冷战时期的区域政治和文化政策时展现出何种形态和紧急议程。
这个项目以工作坊和研讨会的形式在亚洲的不同城市展开, 已经在万隆、北京、首尔、河内完成了四期线上和线下的工作坊, 其讨论密度和成果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我们从跨区域的文化政策、政治机制、机构历史与艺术个案的对话出发,展开了既是艺术史的、又进一步超越了狭义艺术史的大量讨论。

“海岬上的瞭望:20世纪50-80年代东亚、东南亚和南亚艺术的内外交流”
越南站工作坊“超越殖民的回声”现场
2
从事策展人职业的内心动力是什么?
Q:
如何看待“策展人”和“独立策展人”这个身份?在当下中国当代艺术环境中,策展人与画廊、美术馆、艺术家和艺术市场的关系是什么?
苏伟:
的确今天策展人这个词受到很大的挑战,展览是不是一个艺术实践者进行表达的必需载体也在动摇。我自己也经常问自己,从事这一职业的内心动力是什么,文化精英的姿态也像个甩不掉的影子出现在工作中。
策展人这一概念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出现,首先是和艺术史的书写权力和划定艺术家文化位置和系统位置的权力紧密相关。展览制作权在当时还并不是首要问题,这一语境下产生的策展人本身就带有精英色彩。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从90年代走来的艺术家,当他们想去发起一些非个人的、带有冒险和挑动系统意义的项目时, “去策展人化” 几乎是他们认定的一个天然前提。

“内部的流动:‘明日笔记’巡回展III”
艺术家 杨威作品展览现场
策展人 苏伟
南京四方当代美术馆,2021年6月25日-2021年9月5日
图片致谢艺术家
而在2000年之后的时段,中国的策展人因为亲自参与了整个中国艺术行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涉足艺术中心、画廊(或者以艺术中心名义出现的画廊)、美术馆、双年展、艺术市场、艺术史书写、继承自90年的艺术批评写作以及替代性的艺术项目,其身份属性不仅变得暧昧不清,也缺乏足够的对于行业规则的尊重和形成志业的内在动力。此时,中国的当代艺术从业者也加入到顶峰的全球化的时刻,人们对多元文化和跨越时区的稍纵即逝的知识交流产生了极大的心理认同, 这使得本地的去历史化冲动和当时具有某种积极意义的虚无主义冲动变得更为可视 ;策展人也在此时依赖于更加职业性的动作去塑造个人的权力,他们和艺术家一样,在社会中扮演着孤傲的、自诩为边缘的角色,建立自己的工作室,游离在学院内外的空隙中,但在艺术系统中却行使着一种靠艺术机构、资本和基金会赋予的、近乎中产阶级的文化旅游和快速的知识生产特权。
此时, 策展领域的精英主义是一个逐渐淡去、被少数人怀念的事物,他们希望召回那种真正的批判知识分子的精英感, 我自己在开始从事这一职业时也怀有这种情绪,也在这样的局面里开始了自己的工作。当然,这种怀旧也有不同面向的动力来源,沉迷于朴素的思想和观念世界的探索,还是享受知识书写的权力感,有时很难分辨。

“不信则无”展览现场
策展人 苏伟
Click Ten Gallery,2024.8.24-2024.10.8
这种图景其实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事情现在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无论是疫情、战争还是我们在多重危机的全球世界所经历的一切,都迫使以快速知识消费和旅游主义式的知识生产为特征的全球化艺术时代退出了历史舞台。 我还记得2023年底在上海参加一个亚洲策展人的研讨会时,某些策展人仍然使用着那套知识精英权力游戏的语言,通过介绍自己的跨区域、跨国展览,进行资源交换和继续铺展老一套的全球化权力政治。在一个“生活实践”逐渐变成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的时代,这样的动作不仅显得尴尬可笑,也让人深感震惊。他们对现场的忽视,让人不禁怀疑曾经引领艺术行业的策展人角色是不是已经失去了活力。
同时, 机构的角色今天也必须重新审视。 举个例子,很多艺术机构都在做历史总结的工作,我也借助过这样的机构平台策划过与艺术史研究相关的展览,但是这些机构工作的动机——除了美术馆必须进行艺术历史的梳理这一今天看起来其实早已成问题的理由——都需要去辨别。除了显而易见的权力动机,需要提问的是,通过展览制作进行艺术史的重建这一曾经发生在比如东南亚地区的动作,在中国的地缘情境和文化上下文中的意义是什么?如果说在东南亚,这一工作策略性地利用美国的东南亚叙事而将区域的艺术史放置到全球的理论框架中,并以某种方式挑战了西方的东南亚想象和民主诉求;那么在中国,我们进行这一重建的心理状态和政治是什么,以及,我们应该通过什么方式连接到全球史之中,我们可以提供哪些带有挑战性的叙述线索,这些线索如何具备了足够的独特性以至于我们可以说,它们是历史性的时刻或者可以成为我们重新想象全球与地方的可信任的起点?

“不信则无”展览现场
策展人 苏伟
Click Ten Gallery,2024.8.24-2024.10.8
我们需要质问的是:
1、这样的工作在论述上是否充分,逻辑上是否禁得起艺术创作和跨越时代的批评话语的检验,并尝试这一历史嵌入到全球史之中?比如最近有的机构开始着手关于2008年之后中国当代艺术的创作实践的历史总结,这种历史化的动作,是否具备带有超越庸常叙述的思考和方法?
2、这样的工作是否真正打开了中国的内部,并真正创造了与全球史的联系?
Q:
在从事策展的工作中,有哪些展览是您一定不会去策的?您对于选择展览的标准是什么?
苏伟:
在不久之前在一篇访谈中,我用 “流氓主义” (vandalism)来指称一种生存的、也是工作的策略,这可能是可以保护自己的研究和实践唯一的策略。我想这也是今天策展人面临的严峻现实,即 无法完全通过对于机构的道德位置和系统位置的辨认,来为自己工作的合法性进行辩护 ,那么我们只剩下了一种不断被临时化的游击战术,以及对于志业的欲望。
Q:
比起20多年前,批评家、策展人的重要性降低了很多,大家各有各的路子,各自为战,似乎也不再抱团,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这是否意味着策展人的身份和角色在发生变化?
苏伟:
策展人不能仅仅凭靠假想敌去工作,尽管这种方法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有效的,也能部分真实地反映策展人在工作中积累的体验。但是,把假想敌作为前提,往往会把策展实践转化成单一的立场问题或者艺术内部问题,而一些天然的内在于策展实践的问题,比如公众或者文化政治问题,就被排除在外了。我们也往往发现,假想敌不过就是自己,这把策展也变成了自我想象的工作。

苏伟策展单元“幕间:四个案例”之一:
“赵银鸥:2023.5.1-6.4”展览现场
“云雕塑——首届学术邀请展”,松美术馆,2023
Q:
从疫情开始至今,中国当代艺术从创作到生态,您觉得发生了哪些变化?
苏伟:
生活实践重新回到视野之中,这与我们在过去十几年所经历的职业化的策展实践之间有了巨大的冲突。 这并不是说,生活实践与策展之间本就是矛盾的关系,而是在一个新的、需要被从多重角度重新辨认的当下情境之中,重提“生活实践”。
在中国20世纪60、70年代的历史中,我们也曾被不断要求达到生活与艺术、政治、信仰之间的统一,这一讲法的实质,是将个体及其生活奉献给更大的愿景。今天重提生活实践,是将我们身处于多重危机的世界的经验,谨慎而精确地与我们的策展实践并置在一起,但这种并置不是强行的,更不是将两者化约为一个事情。如何动用生活经验中的想象、痛感和欲望,完成一种真正的具有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属性的工作?在中国的情境中,这种紧迫性是在虚无主义被强化、历史正义和人的伦理都在被极度弱化的前提下产生的,也混有那种伪称的(中产的、自诩为身处“社会边缘”的知识精英的、与系统权力紧密捆绑的)“自由”和“清醒”的生存策略,这些都内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却被视而不见,而在艺术之中,那种诚实的根植于生活的异见与具有指认这一现场能力的策展实践,仍然很稀少。

苏伟策展单元“幕间:四个案例”之一:
“阎实:原地生存”展览现场
“云雕塑——首届学术邀请展”,松美术馆,2023
Q:
在当下,严肃的艺术似乎是缺乏观众的,是难以生存的;相反,随着自媒体的蓬勃,年轻艺术家们在用新的方式踏入当代艺术领域。作为一名策展人,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苏伟:
的确在最近几年的工作中,我遇到了来自公共领域的一些挑战。这也让我重新思考对我的策展工作来说公众意味着什么。
最近策划的“几何:赵大钧绘画实践的基本线索”展览,一位热情而敏锐的观众在小红书上写了一篇相对社交媒体来说很长的文字,去讲作为一个非专业人士和这个展览的策展思路相遇的过程,她的分析对我也有很大的启发。这种惊喜并不多,它会给你一点继续在公共领域进行表达的动力。 因为你必须是公众的一部分,而不是声称是生活在社会边缘的高贵的游荡者 (这正是在全球主义顶峰的时期中国艺术实践者的自我定位),才能去进行这种表达,去创造复杂生动的公众政治,去真正触及平权、共同体、跨越阶层的知识交流、文化责任等等这些议题。我想很少有策展人包括我自己能做到这一点。这正是我所尊敬的少数几个同行者正在做的工作,而他们的角色也或多或少地超越了策展人的角色。我希望自己能在这一领域做点什么,但现在缺乏足够的信心和思考。
我也提出过“远离公众”这样相对激进的表达,这里面除了一些对现状的愤怒和恐惧,以及避免将公众强行编辑到自己的工作里的自我警示,我想也能传达出一种关于“错位的时空”的想法,这也是我从一些经历了时代巨变的艺术家生涯中真正体会到的东西:对现在的我而言,也只有在错位的时空中,展览和公众才能真正的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