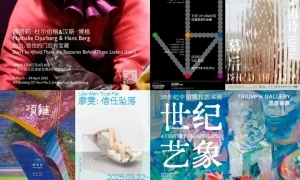刘家琨建筑作品,西村大院(局部),摄影:存在建筑
2025年3月,建筑界国际公认最高奖项普利兹克建筑奖宣布刘家琨成为本年奖项得主,也让这位来自中国成都的建筑师成为第三位获此殊荣的华人。消息一出,在国内外得到广泛传播。
概览刘家琨的建筑作品,想要用一组确切的词汇去精准描述他的建筑风格变得有些难以实现。历史中那些赫赫有名的、居住于象牙塔中的建筑精英们,无疑都希望用个性的建筑风格给世人留下无限的视觉震撼,铸就建筑史中鲜明的符号。相比之下,刘家琨则低调得多,好的建筑在他看来,应当是:“概括、凝练和展示地方的内在品质。它有能力塑造人类行为和营造氛围,提供宁静和诗意的感觉,唤起同情心和仁爱,培养休戚与共的社区意识。”
相比于传统建筑的强势介入,刘家琨的建筑作品显然更关乎建筑所蕴含和传递出的人文力量。他拥有纯粹的艺术理想,但又从不将建筑从人的生活本质中抽离,他深切地拥抱在地性,将建筑艺术的理想和市井中的现实调和,正如评审辞中所述:“刘家琨接纳而非抵制反乌托邦/乌托邦二元论,他向我们展示了建筑如何在现实和理想主义之间达到协调”。
滋养刘家琨的,不仅仅是众多宣传中所说的川渝文化中那迷人的烟火气。实际上,他的“当代艺术”含量相当高。在这篇文章中,99艺术带读者走进那个成天“混迹”在当代艺术圈子的刘家琨,那个距离当代艺术最近的建筑师。

建筑师刘家琨
由普利兹克奖官方提供
壹
在刘家琨近四十年的建筑师职业生涯中,完成的项目遍布全国,其中拥有为数众多的文化艺术机构。事实上,刘家琨与艺术之间颇有渊源。
刘家琨从小热爱绘画,甚至大学专业选建筑的理由都是“建筑学是理工科,可以画画”。不过他逐渐发现建筑学的绘画和自己理想中的完全不是一回事,有些失望。硬着头皮继续学习,即便毕业后被分配到成都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期间,自愿外派到西藏,在参与设计的那曲群众艺术馆前廊上,他还挥舞着画笔创作壁画。

大学时期的刘家琨(中)和朋友们
毕业后的十年间,刘家琨对建筑都没能产生真正的兴趣。直到看到大学同学汤桦的个展,突然意识到建筑师可以不只是生产线上的工程师,搞建筑也可以有很强的个体性,也可以像绘画一般去“创作”。正是这股“创作”的劲头,加上认知上的改变,成为他建筑生涯真正的萌发点。于是,在成都的日子,很少能看到刘家琨和建筑师们在一起,反而与当代艺术家们成天“厮混”在一块儿。
于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成都,能看到刘家琨和艺术家们聚在酒馆、咖啡馆里畅聊艺术。这群艺术家们包括当下我们熟知的张晓刚、周春芽、何多苓和诗人翟永明等,他们在刘家琨设计的“白夜酒吧”和“小酒馆”里举办诗会和展览。他们的互动浸润着成都特有的松弛与温度,成为构成这座西南城市文化肌理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正如艺术家张晓刚所言:“他们那一代人的互动,像上世纪初的巴黎或二战后的纽约,充满创造力与理想主义”。1984年,何多苓与艾轩合作创作的油画《第三代人》无疑就是成都那群艺术青年们友谊的见证。

何多苓、艾轩
《第三代人》,布面油画,1984年
那时,刘家琨、张晓刚、周春芽、翟永明等被邀请担任模特。刘家琨表情严肃地站在诗人翟永明左侧。其中还有个有趣的历史细节:刘家琨最初并不情愿担任模特——寒冬中画室没有取暖设备,他冻得直抱怨“长冻疮了”,但何多苓和周春芽以“画完送给你”为条件哄他坚持完成。最终,刘家琨不仅圆满完成了模特任务,还收到两幅画作作为答谢。

上世纪八十年代青年刘家琨(右一)与艺术家何多苓(左一)、诗人翟永明
贰
热爱绘画和创作的刘家琨,无疑被那些极具才华的艺术家朋友们深深吸引,更能从他们身上汲取灵感。
刘家琨与艺术家何多苓的友谊始于青年时代,两人同属成都文艺圈核心成员。1994年刘家琨为何多苓设计了一处位于成都郊区的工作室,于1997年建成。建筑以极简的混凝土结构为主,有着金石印章般外形。墙与墙之间的间隙、孔孔相套的窗洞强调出内部的空间层次感,一条飞廊凌空斜穿而过。空间的分割与光线布局让流连其中的每一次目光停顿,演变成一幅精心设计的画面。设计过程中两人曾多次讨论,最终达成共识——让建筑成为“画布的延伸”。何多苓评价:“刘家琨的建筑像一首诗,既有力量又有留白。”

刘家琨为何多苓设计的工作室外景,图源网络
刘家琨认为:“画家的工作室不需要花哨,重要的是光线和空间能激发创作。”工作室通过天井引入光线变化,让人们对难得留意的天空、壁端的阳光、飞廊的投影变得敏感起来。而迷宫化的空间和线路设计让建筑成为“能感受节气的迷宫”,也让“时间私有化”成为可能。而设计中最为难得之处,是刘家琨充分考虑何多苓作为艺术家的独特气质,让这一建筑不再是单纯的建筑,而近乎是一个艺术品——一件贴近何多苓诗意画家气质的作品。
虽然目前工作室已没有使用,但其设计的精巧至今为人所称道。**基于刘家琨设计的这座工作室,何多苓还创作出系列绘画《庭园方案》**。2017年山艺术-北京林正艺术空间的展览“居之渊渊”——何多苓与他的工作室就展出了这一系列绘画作品,并在展览现场展出刘家琨设计的工作室模型。

“居之渊渊”——何多苓与他的工作室展览现场
刘家琨为何多苓设计的工作室模型
图片致谢山艺术文教基金会

“居之渊渊”——何多苓与他的工作室展览现场
刘家琨为何多苓设计的工作室模型
图片致谢山艺术文教基金会
绘画中细腻的笔法与建筑造型的细节遥相呼应。刘家琨在天井中选择种植一棵玉兰,在厚重的四壁中,玉兰的花开花落默默倾诉着时光的流逝。玉兰的意象来自诗人埃兹拉·庞德:“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湿漉漉的枝条上的许多花瓣”。

何多苓
《庭园方案之一》(双拼)
200 × 280 cm,1995年
图片致谢山艺术文教基金会

何多苓
《庭园方案之二》(双拼)
200 × 140 cm,1995年
图片致谢山艺术文教基金会

何多苓
《庭园方案之三》(双拼)
200 × 140 cm,1995年
图片致谢山艺术文教基金会
叁
尽管刘家琨没有成为职业画家,但他通过建筑设计中的空间构图、材料质感和光影运用,间接延续了对绘画美学的探索。他认为,他与当代艺术家们长期的密切交流,成为他“整个人的生态土壤”。
鹿野苑石刻博物馆的留白光线设计、西村大院的环形坡道空间布局等都与他早年对绘画的敏感度密切相关,尤其是在空间节奏和场景营造上体现出类似绘画的构图思维。

刘家琨建筑作品,西村大院,摄影:陈忱
同时他重视建筑中的“物质性”,刘家琨认为,建筑的本质在于通过物质空间传递非语言的力量,他希望“以诚实的态度展现纹理材料和加工工艺的本质”。虽然在他看来,这与艺术的感性表达形成对比,但实际上这与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代艺术发展出的一系列以“物”为导向的前卫实践有着千丝万缕的思维相似性。刘家琨在采访中提到:“建筑的力量就在于它的物质性,它无需言说却能塑造人类行为。”而当时的当代艺术界中正是以现成品及装置去回应代人文关怀的核心问题。
在为四川美术学院黄桷坪校区改造雕塑系教学楼时,刘家琨与川美师生展开了一次独特的合作。他摒弃了当时流行的瓷砖外墙,选择“搓砂工艺”——一种重庆传统的砂浆抹灰手法。为了保留手工痕迹,刘家琨邀请川美版画系的师生参与外墙铝板的腐蚀工艺处理。这些铝板被刻上抽象图案,与混凝土墙面形成粗犷与精致的对比。川美原副院长郝大鹏回忆:“当时大家都觉得他疯了,但他坚持要让建筑‘长’出艺术感。”最终,这栋楼的外墙成了川美师生日常涂鸦的背景,甚至被戏称为“会呼吸的画布”。

刘家琨建筑作品,重庆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学楼,摄影:存在建筑

刘家琨建筑作品,重庆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学楼,摄影:存在建筑
肆
刘家琨被当代艺术所吸引,但他同样深谙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异,即建筑的价值在于对社会生活的实际介入,而非符号化的艺术姿态。他强调建筑需在功能、技术和社会责任的限制中寻求创新,而非单纯追求艺术性。他与艺术家何多苓的对话中提到,建筑是“戴着镣铐跳舞”,必须解决实际问题。

刘家琨创作的燃烧装置“竹塔”,图源网络
同时,刘家琨对当代艺术中的某些倾向性持批判态度,他曾提到,当代艺术常陷入“粗鲁成癖”或“形式至上”的误区,而建筑需要以“常识和智慧”回应真实的社会需求。他认为“颠覆建筑传统”需基于对学科本质的深刻理解而非艺术性的姿态。例如他创新性提出的“低技策略”是在充分强调对古老历史文明优势的发掘利用的基础上,以低造价和低技术手段营造高度的品质,在经济条件、技术水准和建筑艺术之间寻找平衡点。

刘家琨建筑作品,文里·松阳三庙文化交流中心,摄影:存在建筑

刘家琨建筑作品,文里·松阳三庙文化交流中心,摄影:存在建筑
伍
刘家琨从当代艺术界领悟的,绝非仅局限于上文所述的所谓“绘画美学”。实际上,他的建筑作品摆脱了各种美学或风格上的束缚,对新世界的建筑规则进行想象和建构,因而很难直接描绘其外在的建筑特征,正如普利兹克建筑奖评委会的评审辞中指出,“他所首倡的是一项策略而非某种风格,从不依赖于重复的方法,而是基于每个项目的具体特征和需求,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评估……他将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整合在一起,并保持了微妙的平衡。”正是这种新的建筑思维和方法,在这个城市化高度发展的时代,给当下人一种关于生活、对待生命新的态度与思路。

刘家琨建筑作品,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摄影:刘剑

刘家琨建筑作品,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摄影:刘剑
这同样也给生存于这个时代当代艺术家们提供启发和警醒。受当代艺术圈滋养多年的刘家琨,毫无疑问用多年的实践在反向提醒着当代艺术所追求的目标。绝不仅仅是现代主义所倡导的过度“风格化”、“符号化”或全球化浪潮中刻意的“全球风”、“科技风”。那么他给予当代艺术界的深层密码是什么?需要当代艺术界发自内心的反思。
值得一提的是,刘家琨常被建筑学术界冠以地域主义建筑师的美誉。但他的“地域主义”或者说“在地性”,不是“怀旧式地使用传统建筑语汇”,更不是夸张地“追逐国际化的艺术潮流”,而是在对传统文化和自然美学的现代转译的基础上,对于本土文脉的认同和坚持。

刘家琨建筑作品,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摄影:毕克俭

刘家琨建筑作品,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摄影:毕克俭
他在鹿野苑石刻博物馆中通过光影与混凝土的对话呼应佛教艺术,在二郎镇天宝洞改造中让建筑与自然山体共生,这种“对本土的坚持”不是对地方和乡土建筑的单纯模仿,而是对当代的技术、工艺、材料资源的积极回应。他拒绝将建筑视为“冰冷的物体”,而是让艺术家的创造精神与市民的生活自然生长,在现实的张力中实现人文关怀的落地。正如画家方力钧评价:“刘家琨在做一个整体,他考虑的是人的整个感受。”
杜绝空喊口号,不刻意标新立异,真正关心“人”的感受,作为中国现代化发展中最接地气的“文艺复兴”践行者,刘家琨的建筑理念也许也能为当代艺术创作带来一些启示。

刘家琨建筑作品,西村大院,©家琨建筑

刘家琨建筑作品,西村大院,摄影:浅深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