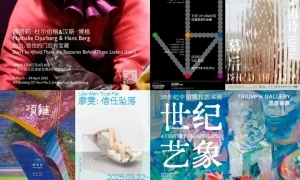“每个人都有过关于痛的经验,包括身体的痛觉与精神的痛苦,因此个体的痛可感;移情与共情的能力让大多数人能够感知他人的痛,以此产生互助的行动或精神的联结,并以此止痛,这是人群对于痛的可知;而艺术创作能够更广泛、更准确地呈现痛,这种表达超越个体、地域与时间,成为一种现象,让痛可见,进而被接受,甚至被消解。”
——蓝庆伟
3月15日-6月8日,何多苓美术馆举办了一场个性鲜明的主题展览——“痛作为通感”。展览邀请忻海洲、熊文韵、徐坦、章燕紫(按艺术家姓名首字母排序)四位艺术家参展。在这场以“痛”为主题的展览中,艺术不再是悬置的美学符号,而成为解剖时代历史之下,从个体到群体生存境遇和情感体验的利刃。
从章燕紫歌颂痛感的诗意表达,到熊文韵由药盒和箭头构建的生命寓言;从徐坦架设于健康人与抑郁症患者间的精神栈桥,到忻海洲青春画布下暗涌的集体阵痛,艺术家们以迥异的创作路径,共同指向一个了核心命题:当“痛”从私密体验向公共话语打通时,艺术的价值不在于“止痛”,而是将处在隐秘角落中的痛转化为可凝视、可思辨的对象,从而让我们认识痛、理解通、接纳痛,甚至是消解痛。




“痛作为通感”展览现场
何多苓
如何看待这四位艺术家对“痛”的表达?

何多苓
艺术家、何多苓美术馆创始人
四位艺术家对“痛”的表达的差异性恰是展览的核心价值。“痛”作为人类共有的感官经验具有双重性:它既是生物神经系统的普遍反应,又因个体生命经验裂变为无数独特的精神密码。此次参展艺术家们的创作恰好印证了这种辩证关系:徐坦通过抑郁症患者的影像档案,将隐形的精神之痛转化为可感知的公共议题;熊文韵用母亲住院期间的药盒构建记忆符号,通过私人创伤引发共情;忻海洲笔下的青春叙事则通过时光滤镜,将特定世代的迷茫升华为具有普世意义的成长寓言;章燕紫则将视角由个人转入群体,探讨在大环境下,个体之痛被时代巨轮推动前行的宿命与无力。这种认知的多样性,正是艺术超越生理痛觉、构建精神对话的深层价值。

“痛作为通感”展览现场
蓝庆伟
艺术家如何超越个体,在私人叙事与群体经验之间达到平衡?

蓝庆伟
本次展览策展人
相较于直接言说痛苦,东方文化更倾向于将创伤转化为隐忍的内在体悟,这种禅宗式的思维转换,使得私人化的痛往往被缄默包裹,成为埋藏于个体精神深处的隐秘情感。
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中,对于情绪的表达,既缺乏类似基督教忏悔室的宣泄渠道,又常被集体潜意识规训为“树洞式”的自我消解。所以,我们惯于用虚假的正面叙事来覆盖真实的内在创痕;习惯于将向外倾诉,通过自我的化解和转换,升华为某种内化的精神体验。
每个人的人生故事都有独特性,比如八旬老者讲述他们的爱情往事可能比当下更富传奇色彩,但这类个体经验终究只停留在私人领域。艺术创作需要警惕陷入个体叙事的窠臼,真正的艺术应当具备穿透力,将个体经验淬炼为群体性的通感。
这也正是我将展览命名为“通感”的原因:艺术家不应止步于叙述特殊个体的生命片段,而需通过创造性转换,使私密感受转化为群体“通感”。当作品中的情绪在更大维度引发群体共鸣时,艺术便实现了从“我”到”我们”的跨越,生成新的文化现象。
真正影响生命体验的核心在于认知而非年龄。痛感本质上存在两种形态——生理层面的伤痛与精神层面的困顿。不同时代的人所承受的痛存在差异:上世纪物质匮乏时期更多受限于生存需求,当代社会则普遍面临精神世界的空虚与情绪价值的缺失。这种差异并非全部源于时代本身,而是取决于个体的认知维度与生命阶段。

“痛作为通感”展览现场
忻海洲
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压力对青春主体的隐性撕扯

忻海洲
艺术家
忻海洲的其中两件参展作品《黄桷坪的英特纳雄耐尔》创作于2019年到2020年,这正是疫情前的全球化高速发展期,作品试图呈现全球化语境下的在地性思考。忻海洲谈到:黄桷坪作为承载他青春记忆的场域,既是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又是充满现实荒诞感的中国小镇标本。当工作室迁至北京后,回看故地获得了新的认知。
作品中的涂鸦墙是一种西方街头文化的自由象征,但也在与中国小镇风貌的视觉对撞中产生魔幻的错位感。位于画面中心位置正在化妆的人物与井盖下的艺术家自画像形成一组隐喻,既是艺术家个人经历的切片,也是对网红时代景观社会的回应。
两件作品中,艺术家自画像前方的CD也隐藏深意。其中一张来自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的《The Wall》(迷墙),暗示着对教育体制的反思;另一张《Wish You Were Here》,是关于对友谊的唱诵。画面中的物件,来自不同的文化、时代和记忆片层,在错位的叠加关系中产生新的意义。
在“痛作为通感”中,并置了忻海洲2007年和2019-2020年两个时期的作品,以素描作为创作母体,经历黑白极简阶段后重返色彩实验,艺术家认为,这种对照恰呈现了某种创作基因的延续性:“相较于直接的情绪外化,我更关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压力对青春主体的隐性撕扯,这种内伤式的痛感通过图像得以转译。”

忻海洲
《白·哪来的扳手》,200 × 200 cm,布面丙烯,2007

忻海洲
《白·哪来的飞刀》,200 × 200 cm,布面丙烯,2007

忻海洲
《黃桷坪的英特納雄耐爾No.1》 ,200 × 540 cm,布面丙烯油画,2019

忻海洲
《黃桷坪的英特納雄耐爾No.2》,200 × 540 cm,布面丙烯油画,2019-2020
熊文韵
妥协与抗争间不断校准的存在状态

熊文韵
艺术家
此次展览中,熊文韵的作品主要围绕“药盒”与“箭头”两个系列展开。这两个系列均始于艺术家陪伴母亲住院的经历。
在“药盒”系列中,那些堆满病床的药盒成为生死命题的见证。艺术家通过拆解、重组药盒结构,在将这些将物质载体演化成尺幅不等的绘画过程中,符号转化为了对生命存续和意义的视觉探讨。在医院里,熊文韵在母亲的各类药盒背面记录医院日常,她发现西药、中药与藏药,展现出截然不同的价值观,比如藏药,它始终与藏传佛教的生死轮回观紧密交织。
“箭头”系列虽然也源于艺术家在医院期间的所见所感,比如那些通往急救室箭头的血色指示,但在后来与艺术家的心境和生活产生更多联结,成为各种力的争斗和力的叙事。近几年世界局势动荡不安,箭头的颜色变化和形态则开始呈现对抗与逃逸的形态,是对外部暴力的控诉,也是对内心焦灼的物化。这些作品通过箭头方向、色彩与质感的博弈,记录着个体在时代震荡中的精神轨迹,以及在妥协与抗争间不断校准的存在状态。

熊文韵
《藏药2023(12)》,100 × 100 cm,丙烯综合材料,2023

熊文韵
《箭头黑白2022》,100 × 100 cm,丙烯综合材料,2022

熊文韵
《西药2023 (5)》,100 × 100 cm,丙烯综合材料,2023

熊文韵
《西药2023(10)》,100 × 100 cm,丙烯综合材料,2023
徐坦
突破健康群体与抑郁群体间的认知壁垒

徐坦
艺术家
蓝庆伟谈到:“‘痛’与艺术的关系总是在‘疗愈’中被提及,‘艺术疗愈’也因此成为一种时髦话术和口号,让艺术的感性驾驭疗愈的科学性,这本身是一种矛盾,也是艺术家徐坦反对的方向。”
通过多次实地交流与文献梳理,徐坦始终秉持着源自生命体验的清醒认知,也在提示着人们对于抑郁症的认知仍处于蒙昧状态。他持续进行的《白鹭、请留下,让我们谈谈心(2020— )》,虽在表现形式上与常规艺术疗愈实践存在表象的相似性,但他明确否定将其纳入该范畴。
这个极具个体经验色彩的作品,实质上构建着社会群体间的情感通道,其核心价值在于突破健康群体与抑郁群体间的认知壁垒。

徐坦
《白鹭、请留下,让我们谈谈心(2020— )》第一、二阶段,视频截图

徐坦
《白鹭、请留下,让我们谈谈心(2020— )》,视频截图
章燕紫
残酷也是诗性的,痛也是值得歌颂的

章燕紫
艺术家
展览呈现了章燕紫的多个系列作品,包括《我们》、《多面者》、《苍穹之下》等。章燕紫作品中对“痛”的表达更为直接和犀利。
章燕紫的艺术创作始终游走于“痛”与“疗愈”、“个体”与“集体”、“传统”与“当代”的多重张力之间。她常以身体经验为起点,逐步拓展至对历史、社会与人性的深层叩问,形成了一套既具东方哲学思辨又直面当代困境的视觉语言体系。
《多面者》中,层层颜料覆盖下的所有面具的最深处都藏着一层带血的纱布,隐喻着在表面的愈合之下,是未被消解的内在创痕;《我们》和《苍穹之下》中,她通过纱布、螺丝与人偶的组装,暗示每个个体在历史巨轮下的被动性——伤痕累累的不仅是肉体,更是被无形力量裹挟的精神状态和对人类普遍命运的终极追问。
章燕紫曾说:“残酷也是诗性的,痛也是值得歌颂的,不一定要把它全部消灭掉。不要止它,有时候。”在创作中,她并没有沉溺于解构虚无且情绪化的“痛感”,而是通过持续的自省与实验,将痛升华为一种诗性的存在宣言。

章燕紫
《我们》,纱布、螺丝、矿物颜料、线、人偶,60cm或30cm一组,2023

章燕紫
《苍穹之下》,直径60cm,车轮、电机、纱布、棉花,2023(作品助理:艾格格)

章燕紫
《多面者》,综合材料,20 × 35 cm(单个),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