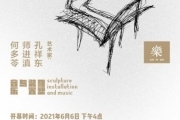何多苓
今年5月,何多苓将在上海举办自己的一个大型回顾展,而这只是他的世界巡回回顾展的第一站,这意味着,在将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何多苓和他的作品都会停留在我们的视野里,而与此同时,他的创作也在继续走上坡路,去年和今年,他一共新创作了十几幅作品,找到了一种新的绘画感觉。我们知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何多苓年过六旬还仍然保持着对创作的热情,而且相信自己仍然在进步。保持这样的状态真是不容易,而且令人尊敬。让我们从和他的交谈中去了解他更多。
主持人:今年5月份你要在上海做一个大型的回顾展,这个回顾展应该是有很多新的探索在里面吧?
何多苓:这个展览已经说了快两年了,最初打算都是展新画,后来因为我画画挺慢,数量老是不够,后来就决定办一个回顾展。所谓回顾,这是一个阶段性的回顾,因为我现在还在画新画,十几幅新画是我从去年到今年的一些心得和作品,还有很多是借了一些藏家手里的作品,再加上我自己藏的一些,我母亲的像、我父亲的像,代表一些生活的痕迹,有些阶段性的东西,从80年代我大学毕业以后到现在,每一个阶段的作品都有。
主持人:你把自己的作品可以分成几个阶段?
何多苓: 80年代是一个阶段,90年代是一个阶段,2000年以后又可以算一个阶段,当然还是风格没有阶段的划分,风格还是以抒情的体裁为主,很个人化的一种画法为主,跟中国大的美术潮流没有很密切的关系,这是它们的共同性。区别是,80年代我是以我下乡的那个地区,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以那个州的风貌和人物形象为依据,画了一系列的作品。整个80年代的作品都是以这个为脉络。90年代就开始对中国传统绘画感兴趣,引入一些中国符号,和一些个人符号结合起来,处于不断的变化中,不像80年代风格那么固定。2000年以后又逐渐转回到80年代有点抒情、有点个人化的一些东西和客观的形象结合起来的作品,但是跟80年代不同,现在不是以乡土的荒野风景作为背景,人也不再是少数民族,而是当代人,一些熟人、朋友,以他们作为符号作为题材,风景也就变成比如城市郊区的小树林什么的,随时可以见到的东西,不是遥远而荒凉的地平线。但是它就回到80年代那种人和自然界某种意义上的结合,那种感觉的题材又回来了。我觉得我的作品这三个阶段比较明显。
主持人:看您的新作绿色的调子特别多。
何多苓:对。色调上能够看出来,80年代我们下乡那个地方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我当时受美国画家怀斯的影响,当时画的色调都是褐色,很单一的颜色,绿色很少。因为那个地方很荒凉,而且当时也喜欢,整个中国文艺界也喜欢荒凉的人文环境。当时主要是画那种色调。90年代以后改变体裁,色调也就变化挺多了。到现在这个阶段,好像比较爱用蓝绿色调来画,好像能够体现目前的感觉、心态、对艺术的体验,现在就觉得这样的色调比较合适。
【相关资讯】
主持人:您的展览的名字叫“士者如斯”,士不是我们通常知道的逝去的逝,还是士大夫的“士”,怎么理解这个名字?
何多苓:这是策展人起的这个名字,他们提出这么一个概念,据我的理解,士在这儿应该理解成广泛知识分子的立场,我觉得可能就是我坚持的一种个人化的立场,我也不敢说自己就是知识分子,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作为知识分子都不是太够格。但是可能是坚持了一种个人的立场。这种士。也可以理解成隐士,中国关于士的说法很多,不一定是士大夫,士大夫这个提法很大,因为我其实跟那些没什么关系,也不是隐士,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广义上独立的知识分子,应该是这种身份。
主持人:您的作品画面往往都是一个人,这是不是你特别注重的一个着眼点?
何多苓:我的画始终是一个人,从最早开始画《春风已经苏醒》,算是成名作,后来从来几乎没有画过两个人的题材,除了有一张叫《第三代人》,那个画准备画我们这一代人的倾向,所以画了很多人,但这个题材我不太适应,而且是比较陌生的题材,所以我很快就回到画一个人的作品。可能跟我内心有种孤独感,跟这个有关系,我也挺享受这个状态,画面上出现第二个人很不容易,即便有最后也去掉,不管是多大的画,只有一个人。07年最多画过有4个人,但都是背影,出现两个以上面部的绘画,我也画过,画着画着就把旁边的那个人也去掉,不自觉的就会去掉,还是跟个人性格有关,跟个人的审美取向有关系,老是喜欢最后画面上出现一个单独的人,甚至于没有人。
主持人:我们看到你的这些新作品都是女性,都是裸体,如果有人把你的画视为是情色范畴,你怎么看?
何多苓:其实我也画过情色,但是现在画的比较少了,一个原因是画多了不让展出。我觉得女性是我始终喜欢画的,我喜欢画女性,男人作为画家是可以的,但是作为画画的对象我找不到感觉。男的其实也都能画,但是我觉得女性始终是我想表现的题材。裸体很大程度上是被我当做裸体肖像,也不是跟情色有关。当然说实话,裸体是一个很传统的题材,在西方绘画里边,我们学的时候也画模特。其实所有的裸体绘画,它都是跟情色有关,都是男性审美趣味占主流地位的这么一个社会里里对女性的一种审美需求。说穿了还就是一种情色的需要,我想也不必回避这个题目。当然她必须在一种道德或者是伦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之内。我也画过色情意味很浓的题材,这次也都没办法展出。这次的画减弱了一点,因为我还是根据我自己的需要,构图、情节需要画什么就画什么,倒不是一定非得画裸体或者是非得有什么特别的,故意去做什么样的表现,我还是根据我现在表现的需要而言。可能我以后一直会以女性为题材,当然还有风景画什么的。我画这个确实比较得心应手,而且能够找到感觉,在里边可以延伸出很多我想表达的东西。
主持人:你这次画的这些,看画面有一种戏剧性,一个女的头上长一个兔耳朵之类的,有一种神秘的氛围在里面,你想通过你的绘画去传达一种什么样的东西?你刚才说你有一种表达的需要,你目前想要表达什么东西?
何多苓:这一阶段,我画着画着就画一个兔耳朵出来,这样更好,她就是有点像人跟动物的混合体了,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人,脱出了肖像这个比较窄的范畴。兔耳朵是一个最简单的符号,笔一挥就画出来了。这么一个简单的符号和人很复杂的符号结合在一起,能够延伸出很多含义。当然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看法,觉得兔是什么,或者人加上兔耳朵是什么效果,东方和西方都有很多说法。但我的绘画没有这么确切的含义,如果非要说出一种什么意思,可能还是我刚才说的,结合了80年代有点抒情性的表达,人跟自然的关系,现在扩大成加上兔耳朵,也可以想象成一种动物跟自然界的关系,或者人跟动物和自然界的关系,这么一种关系,处理在同一个画面上,在有的画面上体现出一种诗意的感觉,体现出一种比较紧张、比较脆弱的联系,这些都是我比较感兴趣的一种表达。所以,对绘画来说也只能比较广义的想它的含义。确切地说有什么故事,或者确切地说它有什么意义在里边,也还是比较牵强。
主持人:我们知道你80年代去美国讲学,呆过一段时间,这段生活对您的创作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何多苓:有影响,但是这个影响很怪,我在美国反而看到很多中国传统绘画,在中国的时候反而看不到,因为中国不展出这些东西。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有很多中国历代绘画,收藏得非常好,而且常年展出,我看了以后很震撼。因此,我从一个远离中国的地方反而触及到了中国,这可能是距离审美的结果,多年因为都从事西画,从来都没有注意中国画,很戏剧的是我在美国看中国画,而且对这个特别感兴趣。所以,1991年回到中国之后,我马上改变题材,把80年代乡土,纯西方的画法,大部分都突然放弃,增加了一些中国符号,至少我自以为是中国符号的一些东西,开始在这方面加以关注。如果说到美国对我的影响,影响最大还是这个。
在国外看西方绘画,看多了就不想去看了,有种审美疲劳的感觉,。真正喜欢的也不是太多。反而是东方绘画的感觉开始出现。这一方面可能是在美国看了原作,另一方面,年龄大了,中国知识分子,骨子里面的血液出来了,开始喜欢这个了。很多画家都是这样的,最后都是回到这个原点,不管走得多远,我中学时代对中国的绘画是没有什么兴趣的,就是喜欢油画,我从没画过国画,但是在美国看了原作以后,一直很喜欢,当然也还是没画过。我现在试图在我的画面上画出一种中国精神,可以追溯到在美国那段经历。
主持人:其实,你出国前画的也有这种感觉在里面。
何多苓:也是有的。只不过现在企图在技巧上有借鉴。把中国的笔墨趣味用在油画上面,这是技巧上面的探索,这个非常有趣,怎么用油画笔画出中国的笔墨之味?所以画起来有很大的乐趣在里面。当然在题材上,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这不是用油画的方法来画中国画,把山水画看成东方精神的代表,不一定。而是要继承一种精神,纯精神,而且被抽象出来的精神元素,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主持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写实绘画,就是用西方的技巧来画中国风情的东西。比如陈逸飞,比如王沂东。
何多苓:我跟他们是相反的,他们是用西方的技法来画中国的。我正好相反,我画的东西,也许看起来有点洋气,不是特别像中国的,但是我的技法更中国化一些。我用油画笔来画的,笔墨的,写意的感觉。甚至包括书法的那种趣味在里面。从这个角度,我是跟他们相反,我画的题材,可能不是那么典型的中国画。
主持人:画面传达出来的气息很中国人的。
何多苓:这个是更重要一点。
主持人:能感觉到和社会生活的一种关联。
何多苓:作为一种中国画家,虽然你也没有刻意这么做,但这些东西会流露出来,中国画家的一些基因,会慢慢的显现出来。当年听人说,油画要民族化什么的,事实上,这种事情都是自然而然就民族化了,我现在是很充分的民族化。现在用的技法是上学的时候没有的。有时候是正好相反的,但是这个问题过于专业,就不多谈,油画民族化应该体现在这个地方,一种精神,有一种东方的,中国的精神,那才能称之为民族化。而不仅仅是画中国题材,仅仅是内容上加以模仿。
主持人:是这样的。就像现在写实市场特别好,大家特别容易接受这个。你最初画得挺写实的,现在慢慢就没有那么多写实成分了。
何多苓:我当年画的乡土题材,也是很写实的。像这样整整画了十年,自己觉得有点疲劳了。后来到了美国,隔中国那么遥远,如果去画中国乡土的东西,自己都觉得不太真实。而且对于自己,完全变成一个纯粹构图上的演绎了,就是不断的重复。我这个人不太喜欢重复得太久,至少在当时那个时间,感觉到不想再重复了,就放弃了。
后来很多人为我惋惜,觉得当初的题材画得那么成熟,技巧也很熟练,而且尤其是商业的艺术市场出来了以后,那种画也能够卖好价钱,但是我断然放弃。很多人感到惋惜,画这种画在中国是一流的。为什么自己不去用它,是扬长避短的感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非要这么做?是不是受了现代思潮的影响,想跟着这个潮流改变自身什么的,真都不是。原因,第一是中国传统绘画的影响加深了,第二是自己想改变了,不想画下去了,老那么画就麻木了。自己现在想起来,也还是挺奇怪的,为什么一点就不画了,后来那种显然很有商业价值的时候,也没有回到那个路子去。这一点在同代人里面是很少有的。但是我自己不后悔,这种改变既然是发自我内心,就是自然、正常的,否则就是不正常,不自然的。
主持人:像你的作品价值在艺术市场上并没有被体现出来。你同时代,同样艺术造诣的艺术家,他们的市场价格就很高。你平常会不会关心这样的问题?
何多苓:我真是不关心这个问题。我从来不看这个拍卖信息事件的。这对画来说是附加价值。原来我们学画纯粹是出于兴趣和爱好,走上这条路,也是出于兴趣爱好,出于对艺术本身的热爱。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改变,绘画突然体现了商业价值,这是后来发生的事情,知道自己喜欢的东西还可以成为商品。现在我觉得还是出于爱好来画画,商品价值是附加的。是另外一回事。我也不愿意在这方面投入太多的精力,而且不愿意被动适应市场。我自己想画什么就画什么,不要看市场而创作,当然有人喜欢是好事,我也愿意这样。
但对于你的作品能卖多少钱,也不是自己要关注的,也不是我能关注得了的。我同代的画家比我的价格要多一个零,都正常,各自在美术史上和商业上的地位不同,这个非常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说清楚的,尤其对于我来说,不是自己努力就可以改变,我也不愿意这样做,所以我也不关注这个事情。
主持人:您从80年代初就成名了,到现在30多年了,一直在创作,你的创作到现在进入到哪个阶段了?
何多苓:相对比较成熟了。因为,80年代一个阶段,90年代就是一个改变,改变就是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到现在,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一条路,这样就肯定下来一些东西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开始进入一种相对成熟的时期。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个画法就不一成不变了。我肯定是要变的,而且我觉得我还会有进步,这是一个很高兴的事情。不管是从技巧还是题材,大的小的方面,哪一方面只要有进步的话,自己都是很高兴,说明这个事还是可以做下去。
主持人:现在你画画或者说生活的那种心情比80年代应该好很多吧?
何多苓:心情都是一样好,只不过更冷静了,80年代更狂热一些,学习的阶段,也吸收一些新生和外来的东西,那个阶段肯定要狂热得多,现在比较冷静,平时也像上班一样,每天都去画,画的时候也心平气和,经常想别的事情,跟别人聊天,很自动的就画画了。画了几十年的画了,现在自动转化为手的动作了,跟大脑的思维没有直接联系了。
第二也是因为人到这个岁数,我没有刻意的学习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自然而然,平时那么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加上自身的变化,还有一些综合的效应,肯定会产生一种绘画的心态。这种心态,现在说来就是一种比较平和,虽然有时候还是赶画,赶展览,但现在心态比80年代平和, 90年代因为在不断的变化,想的更多一些。现在好像完全手自动画画的时候多一些,题材也相对固定一点。比起前两阶段,我还是喜欢现在的阶段,这个状态是最好的。
主持人:感觉是更放松、平和,而且也沉淀下来了。
何多苓:你说的对,更能够沉淀下来。
主持人:问您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做艺术家,让你觉得很快乐吗?如果你不做艺术家,会去做什么呢?
何多苓:我觉得首先做艺术家是最快乐的事情,因为你的工作就是你的爱好,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达到这个境界的,有很多人是盼望着下班,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什么时候下班,星期天也经常忘掉,工作就是我们的乐趣,所以作为艺术家是很幸运的,要被艺术所选择就更幸运了。我能够有幸从事这个职业,感到很大的欣慰。
要是不当艺术家,其实我原来是想当音乐家,自己学作曲。后来发现没有这个条件,后来又喜欢建筑,所以我要是不当艺术家,最大的可能性会当一个建筑师。这个是做得到的。至于经商这种事情就跟我毫无关系了,肯定是最不成功的商人。
【编辑:汤志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