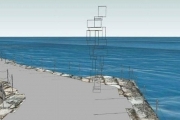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具象、写实性雕塑与时代的关系渐渐被大家所忽视.如何重新建立与时代的关系?重新找到反映时代精神的可能?重新寻回超越时代的精神力量?这始终是摆在雕塑家们面前的问题.
着眼国内,从艺术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雕塑教育长期以来存在着同质化严重的问题——训练模式大同小异,创作理念停滞不前.而在当今中国发展的时代命题和国际艺术语境中,对于从写生到写实,再到具象创作的实践方法和对于这一方法的认识,长期以来缺乏深入的研究与探讨.
鉴于此,经过两年多的策划,日前中国美术学院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邀请全国各高等美术院校的雕塑专业学科带头人以及雕塑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水岸山居会议厅,围绕"主题与形象——再写生"这一命题,回顾来路、总结方式、直面问题、重新出发.与会专家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和研究方向,发表专题讲话,对该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作为中国雕塑的未来之星,全国青年雕塑家创研班的学员旁听了此次研讨会.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在发言中再一次提到了中国近代雕塑史上那段发人深省而又振聋发聩的话语——"不雕菩萨,雕活人"."雕当代的活人,雕立于中国当代大地上的今人,在他们的身上稀存着中国人活生生的气息,蕴含着一种新时代的生气.塑造活人真人的生机生气,以此来变革死气沉沉的文化,勃发新创造、新时代的生机,这是鲁迅先生对青年的热望,也是他的热烈而悲慨的文化畅想."许江认为,鲁迅先生的这句话就是要以独到而直接的方式将振兴的希望落在当代人的生机生气之上.
雕塑的思维是立体的、宏观的、具体的、扎实的,雕塑家是实践者,对于创作有各自的理解和把握."主题与形象——再写生"的关键在于"再",在新时代,需要雕塑家用新的途径和方法来创造,表达新的形式、语言和观念,创造新的意义,反映时代变迁.
20世纪以来,西方艺术经历了从视觉到形式再到观念的范式转化(几乎与哲学中从主体化到形式化再到观念化的范式转化遥相对应).欧洲那些古老的学院,正在丧失她们与古典传统之间的联系,这古典传统不只是非凡的技艺,而且是形式的完满性,以及更重要的——精神的超越性.
我们今天应该如何重建雕塑的精神性?如果有人致力于恢复古典雕塑的伟大精神,我愿意向他致敬并且满怀期待.我相信,艺术的古典性恰恰是学院精神的根本.
在古典时代,雕塑曾经是古希腊人生活中最为核心的技艺.那时,"技艺"既是匠师的技术,又是自由人的艺术;在皮革马利翁的故事里,雕塑家的创造甚至成为精神和爱欲的具体化身.我们正在复制引进的帕迦玛祭坛的高浮雕可以说正是这种精神性的典范.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在柏林看到那组浮雕,现场的经验永生难忘.无需任何解释,我就读懂了《诸神与巨人之战》背后的主题——那是神圣与野蛮、光明与黑暗、秩序与混沌之间的战斗.然而,它的感人至深并不是由于主题,而是由于形象,来自巨大的体量、磅礴的气势,来自每一个形象的塑造、每一条线的刻划.这些浮雕让我相信,存在着一种无条件的伟大,不需要任何解释,不需要任何依凭,却能够震慑心神、鼓荡心胸,足以激发出我们无缘无故的爱、无条件的感动.
在中世纪,雕塑曾经矗立于哥特式教堂高耸入云的塔尖上,成为基督教世界宏大乐章的最强音.在文艺复兴时代,雕塑又成为新柏拉图主义理念的隐蔽所和化身.
在一首著名的十四行诗中,米开朗基罗写道:
伟大艺术家的每一个意象
都蕴藏在粗糙大理石的核心,
只有为优美意象服务的双手
才能把这伟大的意象索求.
米开朗基罗后期作品中逐渐融通了古典异教和中世纪的两种精神,他仿佛并不是在塑造,而是在用魔法之手将形象从大理石的沉睡中唤醒,将意象从岩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从一团混沌中示现出来.
当然,米开朗基罗最感动我的作品是《晨昏昼夜》.这件雕塑史上最伟大的史诗之作,用最物质性的雕塑探究的是最抽象的主题,是一天的晨光,然而却更关乎时间的超验性经验.在他本人的笔记中,清晰地表达了他的想法.他希望用这四尊塑像创造四种关于时间的意象,传达出四种不同的忧郁.面对这四尊雕塑的经验同样是永生难忘,直到今天还是欲说还休,欲辩忘言.对我来说,这才是真正的面对艺术的体验.
艺术家是以研究沉默事物为志业的人,雕塑家尤甚.作为沉默的事物,雕塑超越了文学化的叙事性,却始终在无言地诉说.或者说,不是对某一主题的言说,而是对无名的"示——现".我偏执地认为,能够用几句话传达清楚的,就一定不是艺术.艺术必须具有一种莫名性,一种让语言失效、让话语断裂的能力.对于真正的艺术,我们必须启动全部身心来"体——知"、"感——受".同样,只有真正伟大的艺术才能让我们以身相应、五感齐开.在这个意义上,艺术的创造需要的是身心发动,艺术的教育更需要情意直观.
20世纪初,"抽象问题"正处于哲学与艺术之间那场逆向历史运动的交汇点——当现代哲学开始全面祛除精神科学中的抽象残余之时,现代艺术却将抽象当作一个全新的创造性议程.那时,抽象依然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
100年前,马列维奇、罗德琴科、马雅可夫斯基、李西斯基、爱森斯坦、塔特林这些巴赫金意义上的"激进形式主义者"们,他们的梦想是发动一场美学政治的革命,他们带着重塑艺术自身的力量,以及重新发明世界观的雄心,试图建构一个新世界.这种激进的形式主义不仅创造了建构性的艺术,而且企图发动起一场感性结构的革命,重组我们的欲望机制甚至社会形式.
2011年春天,我在柏林看了一个展览,展出的是俄罗斯先锋派的作品,是1910年代初到1920年代末的俄罗斯前卫艺术.我非常惊讶地看到,有一幅我一直认为是《无题》的画——黑、红、白三种抽象色块,非常构成性的画面——其实是有标题的.它非但有标题,而且有功能.它是"罗沙——卢森堡纪念碑"的概念设计.现代艺术史叙述中把俄罗斯的构成主义、至上主义都简化为抽象艺术的不同风格和样式.在20世纪西方的艺术史论述中,革命者的纪念碑、苏维埃戏剧节的设计图纸都被"作品化"、"抽象化"了,它们被装上画框,作为欧洲抽象艺术的支流挂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墙上.它们的社会脉络被切断,它们的意义和功能被抹去,它们成为了《无题》.
这种"无题",是文化冷战中的"被无题".由于这种"被无题",曾经作为建构和革命的抽象艺术,在1930年代之后逐渐空洞化、装饰化,逐渐走向了它的反面.其中尤以雕塑界为最.在雕塑界,抽象几乎沦为了城雕领域"无目的的形式"以及任意附着象征意义的空洞载体.
100年过去了,20世纪初那种激进的"形式——感性"建构早已随着苏俄革命烟消云散.在冷战双方的意识形态操作中,这种革命的激进的形式主义、这种带着破坏精神的建构主义,甚至蜕化成了一种个人主义的自由艺术,在这条自由主义的艺术道路上,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庆祝无意义".然而我始终相信,那来自百年前的改变世界的能量,是世界史与艺术史中的一项未完成的计划.100年后的今天,这项计划的历史势能正在重新凝聚,那个被错过的观念、形式世界正等待着重新唤起.
最后我想谈一下当代雕塑.我认为当代雕塑的精神性建构应该从博伊斯自纳粹焚书的火堆中抢出林布鲁克雕塑画册的那一刻开始.那是20世纪雕塑史上的重要时刻.那一刻,博伊斯从林布鲁克深具古典意志的现代雕塑中获得了一种讯息——那是一种贯穿了古典与现代的精神性.这是现代向当代跨越和反转的时刻.从此之后,"雕塑"成为一个扩张的社会概念,成为一种"社会造型",一种激进的行动,博伊斯称之为"社会雕塑".
那么,最让雕塑家们感动的博伊斯的装置又是什么呢?对此,我想分享一个我个人的经验.博伊斯那些被称作"装置"的作品,让我想到1997年杭州滨江一个十字路口的晒谷场.那时候滨江还未开发,钱塘江畔还是大片农田,许多公路没有通车,农民可以在新修的十字路口晒谷.收获的季节,劳作之后,谷堆、工具随意摆放,这劳动的遗迹是如此随意、自然,却形成一种奇特的秩序感,更准确地说,一种"世界感"——在古希腊人的经验中,世界即秩序.这个晒谷场上的"装置"令我想起博伊斯,二者同样让人莫名感动.因为它本不是为审美而创作,它的产生,来自最为普通、日常的劳作.在劳作者的随意摆放与搭建中,确立起一种"任意的秩序".那是无数次随机与偶然凝聚而成的现场,所以才是命运般的存在.这劳作的遗迹,如同博伊斯行为发生后的装置现场一般,示现出一种奇特的仪式感,仿佛是一场祭礼,向沧桑岁月中无名的劳作致敬.
博伊斯之后,我们该如何讨论雕塑?这是个复杂的话题.我觉得可以有两种方向,一是朝向"社会雕塑",以艺术行动参与社会议程,雕塑作为这样一种操作,它的材料不只是物理材质,还包括心灵的材料.另一种方向则需要我们在生产与展示中破解传统雕塑的"架上"本性.实际上,在博伊斯的工作中,展览与作品之间是打通的、混淆的,作品与作品之间并没有明确的边界.艺术家展示出的,只是一些形象、一些物、一些空间、一些姿势、一些声音、一些体量,所有一切相互作用,共同发生.
我这里所说的,并不是希望雕塑家们都成为"后观念时代的造型艺术家",我相信,无论用何种方式创作,最至关重要的,是在这个极大丰富而又无比匮乏的时代,重新建立起雕塑的精神性.作为一种精神生产,艺术家所要"雕塑"出的不只是主题与形象,还可以是意象与时光,可以是公共空间与社会意识,最终极地,还可以是我们的自由、我们对世界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