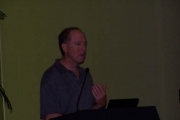“素画”研讨会现场
赵红尘:各位嘉宾、各位好朋友,我先开一个头。首先我代表香港美术馆,代表我本人欢迎各位来到香港美术馆参加赵红尘素画研讨会。非常感谢朱其老师,还有我的各位朋友,还有媒体界的各位朋友,还有曾馆长,香港过来的朋友。我的作品主要体现我对诗歌、对现实的一种理解,在这方面处于尝试、探索阶段,所以请各位过来给一些指导,希望我以后在前进的过程中把方向辨得更清楚、走得更好。非常感谢大家过来,谢谢大家!
潘维: 红尘画展至少我是每次都来的,四个阶段,最早的一个阶段就是他的“自由水墨”,这个“自由水墨”到目前为止还是我特别倾心的,他的色彩、他的大面积诗意、他的敏感。后面几个阶段就是因为油画的表现更加受到欢迎,其实是市场的欢迎,并不是美学的欢迎,这句话真的是我的一种想法。慢慢的进入到今天这个阶段,今天这个阶段,因为大家都已经看到他的东西了,我就不介绍了。“素画”重要在什么地方呢?重要在两个地方:就是第一次也许是站在“意义学”意义上,第一次用中性笔成为绘画艺术的一个具体工具。别的人我们都写字,偶尔有人也画画,我在写字的时候,也可以画一张,但是不是一个构成意义学上的产物。因此我说这是第一次,至少我们可以考证的是第一次,是从红尘开始的。这个研讨会并不意味着你们一定要谈红尘的这一次画,但是这次绘画是核心。
我最近也在家里写写书法,练一些毛笔字,因为毛笔是湖州产生的,也看一些帖子,但是临不好,因为这需要把心静下来,要静心,书法的艺术,按照我们古典的传统来说,必须有一个静心才可以随意。我还没有做到这一点,还没有在书法的轨迹上做得那么静心,前一段时间我在写书法的时候,我的朋友们觉得潘维你写得很好,为什么?他拿书法上写的一幅字,让我写了一幅同样的字,他认为我的字愿意挂在那边,为什么?我是意到点未到,点到意到才是真正都到了。因为“意”跟“笔”如果一体了,你的精神层面,你的技术层面,你的判断层面也一体了。我今天想表达的就是红尘的这个前所未有的素画,我觉得是他最舒服的时候,是他最打开的时候。他的笔到了“意”肯定到了,因为他是一个诗人,他的意识早就先行了。
笔为什么到?今天曾馆长说了一句话“当红尘这一笔画下去的时候,他是不用橡皮来擦的。这个难度如果没有天赋是难以抵达的。毕加索也配了一些插图,非常简洁的几笔。能够这么简单地几笔把它表现出来是太困难了。如果没有一种技术上的天赋,没有真正的技术,你根本抵达不了,但是红尘做到了。”
我有一个问题,是我个人一直想跟红尘交流的,他跟意识形态有关的话语的画,画革命的,画得非常好,我很喜欢,但是我觉得红尘应该开辟一条另外的路,而不是应该在这条路上走,因为这条路上在某种意义上人家已经把你堵塞了。这条路上不是红尘的必然之路,红尘应该按照他的那种大幅的,或者大跟小就是一体,红尘能够把大搞得这么完整,把小搞得这么精密,说明他的能量都是能聚合的,这是我一开始就谈的,红尘有大能量,能够聚合在一个地方,聚气在一个地方。因此如果红尘能够把这一块意识形态的东西跟当代接轨,而不是通过当代浮在现象层面上的那种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而是把意识形态的一种核心、美学艺术形态的核心,能够跟自己的东西把握起来,我觉得红尘探讨这个东西才是最重要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也就是我开始所讲的,他早期的对中国意象的、中国文化的那种绘画的结合,跟他的一种技术、跟他的一种丰富性、跟他的一种“大”相通起来。这样的话,我觉得红尘就会经过一个丰厚的基础之后,甚至他的一段困惑之后,迈上一个非常高的台面,因为我们绕了一圈之后,就是进入一个零之后,他不是回到一个原点,他是上了一个新的层面。一年四季,红尘已经完成四个季节了,一个新的广阔的东西,我觉得是属于红尘的,因为只有红尘这样的人,在我们中国诗歌界也不见得有,很少见到能够不停打开,就像奥顿这样的大师才会做到,红尘就有这样的一种优秀品质。我抛砖引玉,讲得太多了。

赵红尘作品
潘维:请朱老师先谈。
朱其:前两年我做过一个诗人的绘画展,像严力他们都参加了,那个时候还不认识红尘,很可惜。最近十年我是国内第一个做诗人画展的,直到民国,画家还在写诗、写小说,像上海美专、国立艺专,很多画家或艺术史学者都是文学家,比如滕固、倪贻德、傅雷等,艾青其实是上海美专毕业的,吴大羽的学生丁天缺在四十年代翻译过魏尔伦的诗歌。倪贻德的油画画得很好,他的小说、诗歌、散文都写得很好。陆小曼的水墨画也画得非常好,她的才气绝对不在徐志摩之下的,现在大家只注意她的诗歌,没有注意到她的绘画,其实她的传统山水、工笔画得非常好。但是49年以后,由于向苏联学习,绘画和文学就分开了,就是画画的不再写诗歌、写小说,写小说、写诗歌的人不再画画。我觉得最近十年这个传统又开始复兴了。上海的默默也在做观念摄影,上个月他还在锦溪镇搞了一个撒娇当代艺术馆,南京的海波也在做当代艺术中心,这个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像红尘的画,他是用那种诗人的本能在画,从绘画专业说起,他不是完全从技术道路过来的,他完全是从一种诗人的本能和对一种线条的感觉过来的,诗人进入绘画往往比较喜欢表现主义的风格,像芒克就是画梵高的风格。
我觉得赵红尘的自画像部分非常不错,用线条画的自画像,还有这批戴红军帽的老革命肖像,这两批作品比较有意思。2009年纽约的古根海姆美术馆做过一个“第三思想:美国艺术家凝视亚洲”的文献回顾展,介绍抽象表现主义、激浪派,包括垮掉一代的文学,他们在六七十年代受日本禅宗的影响,里边也展了几张凯鲁亚克的自画像。凯鲁亚克在写了《垮掉的一代》之后,他后来一直在研究佛教,他的第二部小说《达摩流浪者》的原型是中国唐朝的一个禅宗诗人寒山,他也喜欢画画,他画过一些自画像,我觉得红尘的自画像中的线条,笔线的走势风格跟凯鲁亚克有点儿类似。寒山在美国六十年代的知名度比在中国还要高。整个美国垮掉一代就受寒山的影响非常大,但寒山在中国的研究是不够的,台湾还研究得多一点。
潘维:因为他是宗教的色彩,禅宗的。
朱其:另外可能跟翻译有关,美国人翻译的寒山诗歌也许有加工成分,把自己的感受加进去了,寒山的英译诗,可能比寒山的中文原诗还要美妙,我也没有看过英译本。我觉得赵红尘的“怀念”系列红军肖像非常有意思,因为他画出了一种革命复杂的表情,或者叫“革命者肖像的精神分析”。美术界最近三十年对革命的表达实际上是停留在反宣传画的概念上,像王广义极其政治波普,只是简单地在嘲讽和丑化领袖形象,给毛泽东的脸画上红胭脂,或者给他穿一件花衣服,或者是给毛泽东打格什么的,这种对革命的表达停留在一个很简单肤浅的讽刺概念上,没有真正把革命者的人格内在特性表达出来,这个题材很可惜在近二十年被当代艺术给糟蹋了。我觉得中国革命是如此复杂,在中国的革命者身上,他们将人类历史上善恶两个极端的人性都集于一身。他们的身上既有最彻底的理想主义的一面,也有最功利主义的一面;既有天下为公的一面,也为了权力表现出最自私自利的一面;既有追求人类的善和正义的一面,也有为了推进革命而残酷无情的一面。人类历史上正邪两极的特性,完全集中在共产党这一代人的身上。国外有这样一个学科研究,叫做“革命的精神分析”,我们在学术研究和艺术表现上对中国革命的精神分析是做得不够的。
我觉得最近三十年的当代艺术和文学,对革命的人性复杂性的表现是不够的,当代艺术对革命题材的现代绘画,其实还是停留在一个后现代主义的简单的形式游戏,没有真正挖掘和反省中国革命的现代性。我觉得红尘作为一种诗人的敏感,他把革命者肖像的复杂性反而画出来了,他做到了美术界近二十年没有做到的事情,这个还挺有意思的。赵红尘的这些戴红军帽形象的脸有一种非常复杂的体验,一种革命者到了生命晚期的虚无感、荒诞感以及对革命的矛盾感受,都被表现出来了。这种面部表情就像丁玲晚年的一句话“总有禅机参不透”,她对革命充满了爱恨交加,爱和恨、崇敬和怀疑、自豪和痛苦,在文革后全都搅在一起。
这种画面接近一种精神分析的革命肖像,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政治波普等绘画基本上没有达到这个表现层次, 但我觉得红尘对革命现代性的表达对此是有超越的。我不太赞成运用后现代主义的反讽形式来表现中国革命和政治题材,这很容易变成一种从表面滑过的语言游戏,不仅不能让我们对中国革命和政治进行深入反省,还很容易让一种专制主义图像变成时尚视觉,使我们对毛的宣传画图像产生一种肤浅的游戏快感。我认为对中国革命及政治图像的处理应该持一种严肃美学的现代主义态度,赵红尘的这批画将当代艺术中对政治的后现代讽刺又往回拉了一些,使其重新回到一种庄重性的语言,我觉得这非常有意义,很多人都认为现代主义语言的庄重性已经过时了,但我觉得现代主义在中国还有存在意义,尤其是针对中国革命极其专制主义文化的深刻表现,现代主义还是具有语言力量的,这是后现代主义无论如何做不到的。
赵红尘的线条画,比如中性笔的线性非常随性、非常肯定,下笔非常有跃动感,这也是中国的一个文人传统。中国古代的文人一定是画家,文人具备两个特征:一个是阅读的书卷气,第二是毛笔字好,他一定是一个很好的画家,因为中国画本身就是由这两个东西垫底的,一个是关于对毛笔的控制,第二个精神上的气韵生动。气韵生动由三个知识背景构成:一是国学和宋明理学;第二是禅宗,唐宋以后中国的书法、绘画、诗歌都有禅宗的影响;第三是山水诗歌的文学以及园林的影响。中国历史上,诗人和书法、绘画的两栖或者三栖的人物非常多,像唐宋的王维、苏东坡,一直到明代的杨维桢、文徵明,文徵明的《园林记》写得非常好,他在《园林记》里边写到关于园林里假山石的质感,后人没有一个超越他的。中国当代艺术往后的一个阶段,我主张一种“新传统主义”,即从宋、元、明、清传统中转换出一种艺术观念,当代艺术要跟文化脉络接轨。当代艺术目前有一些价值混乱,可能有一部分特别西方化或特别后现代主义化的艺术,它被西方艺术界推介,在全世界出名,在市场上出名,它倒变成当代艺术的正宗了,反而以人文性、传统性为基础的当代艺术倒显得不正宗或者显得变成在野的艺术,这是有一定问题的。
现在像798的很多展览,包括像中央美院前个月开幕的“艺术院校实验艺术展”,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在那种装置、多媒体、观念艺术形式的展览上,你会很惊叹中国的年轻学生把外国的所有流派的语言都模仿得惟妙惟肖,难分国界,中国人的技术模仿能力是世界一流的。但是现在当代艺术有一个问题,它的人文性和传统性不够。这两个方面,我觉得恰恰是诗人出身的艺术家,反而是他的一个强项。中国当代艺术要有创造力,我觉得应该重新恢复他在八十年代的一种人文的精神力量。八十年代对传统的吸收是有欠缺的,这个现在可以重新认识和补充。我看赵红尘的画有一种亲切感,感觉他还停留在八十年代,没有进化到九十年代的后现代主义,但这也不见得是一个坏事情。
潘维:下一位请简宁老师。
简宁:红尘的开场白里有一个小小的语病,“我代表我本人”云云,用弗洛伊德的说法,这个语病透露了某种真谛,即作为艺术家的赵红尘的多重人格。
由于我的孤陋寡闻,我是很早就知道赵红尘是个优秀的诗人,很晚才知道他的绘事活动,上次这个素画的开幕式吓我一跳,赵红尘的绘画已经跻身于当代优秀的专业画家之列。
诗画同源、诗画同体有两个完全不同的传统,一个是中国古代诗人的文人画传统,另一个就是欧美20世纪初期的超现实主义的活动。朱其刚才说到王维苏东坡,这个我不提了。毕加索、达利、夏加尔、克里他们写诗,不常被人提及,我读过他们的一些诗,很多写得相当好。我想这两个方向的传统对红尘都有刺激,他也以自己的艺术实践向这两个传统表达了敬意。他的诗歌创作美术创作体现了他的创造能量。上次我开了个玩笑,姓赵的都很厉害,赵佶赵孟頫赵无极,现在又来了赵红尘,莫非他赵家氏族的基因不一样?
细致地评价、评说红尘的画超过了我的能力,这个应该留给朱其这样的批评家去做。我只谈我的一点感受,即现代性在很多专业画家那里是个目标,但在红尘这里却是个起点。这可能与他的诗人身份有关,他对意义的敏感和挖掘显然是独特的,深具人文的情怀。比如他这个素画,用纯粹的线条刻画人物形象和精神,虽然有国画的遗韵,但却是他个人的发明,他的线是现代性的线。在现代性这个起点上,向哪个方向走、走多远,我想可能是红尘现在的功课。
潘维:李笠。
李笠:我看赵红尘的画是近半年的事,但这次最为震撼。看他水墨画的时候,发现他把西方点彩、印象派的一些风格和中国水墨结合得很好。他诗人性格在画面表现很酣畅,充满生命的鲜活和个人的激情,跟后现代绘画没什么的关系。光做到这一点我认为已经很不容易了。这需要天赋。我在瑞典的时候也画过油画。严力去瑞典看过后指出了一些问题,以后我就再也没画过。这次看赵红尘的素画,发现他对线条把握得很好,让我想到毕加索,马蒂斯的寥寥数笔,生动勾勒出的那些人体。比如这幅画,很能体现他的个人风格和绘画语言。他能找到黑与白,简与繁的微妙关系,并能恰到好处地把它们表现出来。如果他在这方面继续发展,我觉得将来会了不得。他的画有诗的寓意,有心理的复杂世界,很耐看,就像古文人画,一般画家很难画到这个程度。
简宁:对不起,我补充一点,红尘的“素画”和水墨,从我自己审美感觉,比如我如果买画,我愿意买他的彩墨,如果看画,更愿意看他的素画。什么道理呢?就是艺术家的个人创造和艺术传统的关系了。我看 “素画”的线条,刚才朱其也说到跟老文人画的线条有些相似。我觉得有一点不一样的是红尘这个不是软笔画的线条,我第一次来看的时候就吓一跳,这是钢笔画吗?给我的印象就是像集成电路,集成电路电脑打开,后台里边的线路乱七八糟。我刚才说现代性就是从这方面过来的。我原来是学理工科的,从农村考上大学,学理工,为什么不接着搞那个专业呢?我觉得我搞不了,最难的一个课就是电子线路课,密密麻麻的线条,我的同学五分钟做完了,我的城里的同学五分钟做完了,我两个小时还没有接上头呢,后来我终于败退下来,我说的这个意思是在现代性这块我是败阵的一个学生,我对红尘的理解,用这种“素画”线条的方式来表达人物,其实是红尘个人的一个发明,这个发明本身在他的专业体系里怎么样,那是你后面的功课。对不起,插一下。
朱其:他的线条灵动性很强,一般外国人画不出来,因为里边有毛笔草书的训练,他的中性笔其实有一些草书的训练痕迹在里边,一般外国人画不到这种灵动性。
潘维:胡山老师讲一讲。
胡山:我跟红尘是非常熟悉的,有很多年的友谊。我基本见证了他从第一笔开始到这几年来他的几次画展,这是第五次了。从香港第一次开始,我全程地见证了他的艺术历程。红尘又有一批新作问世,我又一次感到震惊,但那震惊也是意料之中的震惊。这一次的画作,颠覆了他以前所有画作的面貌,全新的手法,全新的视角,全新的画材带给我的是全新的视觉感受。
一个画家在既有风格和画法被公众接受和肯定后,又迅速打破自己精心绘制的独特图境,以全新的形式呈现内心新的表达的勇气,这需要有坚毅和罕见的决心。
红尘说:“红眼是一种病,有时是眼病有时是心病,有时不知是什么病” 。我对“不知是什么病”感触尤深,它内里传达出的扭曲含义,是社会对人的一种折射。病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什么病,更可怕的是它还在以惊人的速度在人与人之间蔓延。红尘试图以最原始的绘画方式来揭示这种潜移默化的病态的流播,他就象一个为爱人编织毛衣的巧妇,那密密匝匝的线条不仅是耐心的考量,更是一根根诚意的表达。
对于“愤青”系列,可以说是红尘的“旧瓶”了,但这回却装上了“新酒”。说是新酒,却是带有陈酿的浓醇,朴实无华的细线品来余味尤深。“愤青”一词虽然是从“愤怒的青年”简化而来,但它却有着广义和狭义之分。著名的老愤青屈原,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而近代最著名的愤青则非早年的毛泽东莫属,他以其先进的思想和彻底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在当时的历史时期发挥出无可替代的作用。
相对来说,“怀念”系列更为纯粹。主角们默然的神情是对过往的追忆,还是角色内心的自省,更或是人与生俱来所具备的本能,答案就在画里。
如果说,红尘的《生命的色相》是以美的艺术特质来倾诉,那“素画”就明显地具有社会学的想象力,无论是“红眼”、“愤青”抑或是“怀念”,都是为了探究人与社会之间的种种关系,而作出的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绘画意识。经验告诉我们,人类的多样性构成了社会的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又构成了人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所以,多样性的阐释成为红尘关注现实生活的又一种可能。谢谢!
潘维:我插一句,我觉得有一些话至少站在我的角度来说,我看他的诗都觉得很恍惚。诗歌,我们都有学院、民间之分,那么谁是学院,谁是民间,到现在我都搞不懂。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搞懂。因为我从诗歌学上看,他们可能作为个体上都会认同,因为我现在有话语权,或者因为参与到那个都没有问题了,但是事实上,我从来也没有站在这个角度思考过一点问题,因为他就是一个汉语问题,就是一个你是一个诗人面对汉语的问题,我这句话稍微说得局限一点,不然我们用口语说话总是不可能像数学一样精确,这就是中国汉语的丰富性,也没有必要谈论那个。包括齐白石,他是民间的,还是学院的?这种都是“伪问题”,为什么一定要因为你曾经是这样的,就一定是那样的。贡布里希说了一句话“眼光都是文化给予我们的”,他首先关注的还是一个文化概念,当然他有非常明确的就是绘画传统本身的文化,但是我们毕竟视觉里面太多了,都已经面对过了,包括还有现代性的问题,我的诗歌,你们写作的人全部都知道,我的诗歌是当代最缺乏现代性的,我一直是写江南的时间中的那个江南,改变是另外一回事情,没有一个人说我的诗歌是缺乏现代的,他们每次要贴我标签的时候,要说我是先锋派诗人,我们浙江最近出了《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那本书里边,每一章节里都有我,很大的篇幅,今年他们南京的国家大课程,就是《新文学大系文学史》里边江南就两个人,一个是老车进去了,一个是我进去了,但是我一直搞不懂这一点,何为现代性?我们活在现代,我们能够没现代性吗?有一句话:“笔墨当随时代”,我说你们如果有一个人敢说我笔墨不随时代,他能够把时代的列车给顶住,这个人才是真正的艺术家,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大师。
简宁:林散之有这种东西,我看了一下午,我觉得林散之有这种东西。
朱其:我补充一下,有关美术学院的学院派,我在八大美院的讲座都说过,就是中国的学生虽说都是美院毕业的,实际上都不是学院派,为什么?因为我们连一个学院派的课程体系都没有。文史专业还好一点,中国的大学文科还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西方化体系,美术学院实际上既没有西方的知识体系,甚至中国艺术本身的传统体系也没有。
潘维:朱其我插一句,在我的眼里是有学院派的,就是中国古往今来的大师们,他们就构成了学院派,他们成立,别的东西不成立。
朱其:不是说在挂了美院牌子的学校毕业出来就一定是学院派。国内的美术学院缺乏一个道统,比如美术学院的课程,中国艺术的传统部分主要是教文人画和佛像为主,稍微再讲一点古代建筑和书法,但中国真正的美术传统,还得教碑刻、金石、篆刻、玉玺、陶瓷、玉器、明清家具等等,这部分知识,整个八大美院找不出几个老师可以系统教的,能够系统教的都是在江湖上,根本就不在八大美院里边。西方体系是不是就系统呢?西方课程也不系统,六十年代以后的艺术基本上课本上没有。所以美院不存在学院派,而且学院派这个概念,在1949年以后跟徐悲鸿的写实训练和政治意识形态捆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影响力,实际上在二十世纪后期,世界的当代艺术的实践,从来就不在学院系统,而是在一个二战后的社会运动里产生的。
张小云:红尘的画,所传达出来的一些理念、观念,甚至里头的隐喻,我甚有共鸣。无疑,红尘的画,在我看来,它散发着这种“不合作”的强烈信号。比如,在红尘的画作里边,不论是《红眼》系列,还是《怀念》系列,甚至于他的《愤青》系列,我感受比较多的是作品中不断出现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行为、状态。它们跟我体味到的周边现实比较接近。而这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更可能贴近现实。“不合作”基本上是采取一种比较果断的做法,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更接近事实本身。这个“眼”不管是《红眼》,还是像这幅油画上的“蓝眼睛”,他们总有一只眼是不愿意或者说没法合上的。你看他的素画,大多数画里边有一只眼是睁开着的。为什么要睁眼?不什么没法安心地“怀念”,为什么让你非“红眼”不可?所以我说,红尘看到的感觉到的,可能更接近事实本身。刚才朱其讲了他的那些红军系列的画所传达出来的感觉,我也深有体会。
10多年前,或者更远些,许多人被忽悠去学各类功法,其背后有点“原因”。比如说,那时候医保还不普遍,不完善,许多人担心老了之后身体出了问题怎么办?于是各种让大伙延年益寿的“生命信息科学”就应运而生。那个时候相声作品里头“革命几十年,一回头到了解放前”的台词被传成流行语,很能说明问题。因为那个时候许多人就生活、健康没有保障,这就给那些借群众健身植入他们想要的目的以可乘之机。红尘的那组《怀念》系列画里,那里边的“红军”们各种表情各种神态,正是我提到的类似当时这种背景的反映。人是很奇怪的,你一旦被理念植入,你的活语权就被掌握在别人手中。潘维提到的“话语权”的话题,其背后是有力量的动因。红尘画里“红军”们充满的彷徨、思考、无奈、愤恨等等,是对这种力量的“不合作”,甚至是抗拒。从红尘笔下戴红军帽的这些人的表情上——恰切地说,红尘的作品,唤起了我们对社会进程的相关感觉。我自己边看着画,边闪现着我的“社会色彩”体验:小时候我一直认为1949年以前的天是暗淡的,后来是阳光的,而现在更多的是阴沉,我也讲不清楚从何开始变成这样的色彩,有时甚至感到是墨黑的。感谢红尘的画,他让我不断地唤回社会色彩的感觉。
看红尘的作品,我还有第二个感爱,就是他的诗上功夫和诗外功夫。“功夫在诗外”虽然是老调重弹,但以此观看红尘的诗、红尘的画好,是最为恰当的。两个月前看完素画展后,我送潘维去机场。在去机场的路上,潘维告诉我说,红尘是这些年才大量投入绘画创作的,我当时最大的感触就是这句“功夫在诗外”,套用在他的绘画创作,就是“功夫在画外”。
向卫国:处身于饕餮时代,人们的艺术口味早已被败坏无疑,继而产生的必将是大量的艺术素食主义者。因为当今号称多元的艺术世界,从另一个层面看,无非是混乱局面的另一个说辞。当此时刻,人们会思念什么?或者不如说怀念什么?从人们的餐桌上也许就可见一斑,粗粮素食、农家野菜,这些过去时代的弃物,如今成了最受追捧的“座上宾”。
这一时代的变异,敏感的艺术家焉有不知之理!问题在于,社会的变异如何转化为新的艺术表现方式和艺术经验?绝不是每一个艺术家都能够轻易地找到新的艺术语言,有效地表现这种社会的和个体内心的双重巨大变化。它对艺术家的要求不仅仅是艺术的能力,还有思想的能力,它同时考验一个艺术家对艺术本体领悟的深度和对艺术语言的创造力。所谓艺术本体,不是纯粹的观念问题,也包括艺术传统,也就是艺术家要通过对传统的研习,认识艺术的本源及其发展的奥秘,从而在变化中掌握艺术的本义。诗人艺术家赵红尘无疑具备这样的综合能力和条件。自从三年前由诗歌领域入侵艺术领域以来,他就不断提出新的艺术主张,对当代艺术观念造成一次次的冲击,其中最重要的,一是“画诗主义”,一是“素画”的发明。
由于赵红尘从诗人到画家身份的转变,“画诗主义”很容易被简单地理解为艺术的跨界行为,这是不对的。首先,作为画家的赵红尘,依然是一个诗人,而且永远是一个诗人,在他的艺术观念中,无论诗画,其本质都是诗,也就是说,诗歌也好,绘画也好,只是诗的两种形式,站在它们背后的是共同的“诗意”。所以,“画诗”,不是以诗入画,也不是以画释诗,它只是“诗”——是诗的一个种类,而不是画的一个种类。当然要把它看作画的一个种类也无不可,但这是站在次一级的艺术观念上来理解,而不是艺术本体意义上的。我们在此谈论这个问题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研究画诗主义,而是想先弄清楚一个有思想的艺术家的根本艺术理念,这样才能谈论“素画”的问题。
由上述分析,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赵红尘在艺术深层次上是一个本质主义者,他理解的艺术本质就是诗(或诗意);在艺术的浅层次上,或者说在艺术的形式区分和横向的种类划分层面,他是一个反本质主义者,也就是说,在这个层面以及更低层次上,一切都是相对的、可变的,并不存在任何金科玉律。这就是他发明“素画”的根本的合法性所在。
首先,“素画”并非绝对的新发明,因为有传统的“素描”为其父本。“素描”在艺术创造中的存在已有漫长的历史,但它只是作为艺术家的一种练习方式而存在,从来没有人把它理解为一个画种。但另一方面,也没有人能够绝对地否定它作为一个新画种的可能性。
其次,“素描”为什么长期没有被承认为一个画种,原因就是它过于简单,尚处于未完成状态。所以,“素画”要想成为一个新画种,就必须对“素描”进行发展。从赵红尘已有的100多幅“素画”来看,它们虽然保留了“素描”的“素”的特点,全部用黑、红两色(部分加了蓝色)中性笔完成,只有线描,没有色块,但的确可以明显地看到对素描的“发展”:首先是用笔。中性笔是发明时间还很短的一种新的书写工具,方便实用,特别适应当代的快餐文化,目前还没有人将它用于严肃的绘画艺术,但这并不等于它就不能用于绘画。同时,将传统的以单线线描为主的“素描”复杂化,大部分作品都以线的方式将画面排满,远看几乎已接近色块的效果。这是使“未完成”趋于“完成”重要一步。
第三,在“素描”基础上,加入个性化的思想元素和艺术语言。比如,其“红眼”系列中加入了“红眼病”的人性化因素和画家之前在“愤青”系列中使用过的“一只眼睁一只眼闭”的特殊艺术语言或符号;而在“怀念”系列中则将这一艺术语言再次发展为“双眼闭”的新语言。个体发明的艺术元素的加入,显然使艺术作品的内在结构发生某种质的变化,同时也可以起到使传统的“素描”趋于完成性的“作品”的作用。
第四,也是最关键的,“素画”从艺术角度看是对传统“素描”的发展,但从观念的角度看,完全是“笔墨当随时代”的产物,特别适宜于当下这个时代的特点。赵红尘深研《老子》,十分清楚“见素抱朴”在这个一方面极度贫乏,一方面又在思想、文化和艺术消费等多方面极度奢糜的饕餮时代的意义。其实不仅是老子,孔子也曾说过“绘事后素”的话,这是他对“素以为绚兮”的阐明。有意思的是,孔子正好也是用绘画来阐明“素”与“绚”的关系的。总之,对于“素画”的发明,我们不急于断言其将来是否真的成为一个重要画种而被广泛地采用,至少在当代自有其时代背景、思想观念和艺术历史的机缘。
【编辑:曹茂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