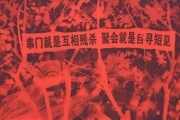这个名字、这个人
“侵阶藓拆春芽迸,绕径莎微夏荫浓。”——郑谷 ①
在同代人中,周春芽一直看起来相当年轻。
也许每个熟悉他的人都忘记了,“春芽”这两个字所含有“春天的绿芽”之意,这个名字一方面令他的外貌长期滞后于实际年龄,另一方面也令他的作品中持续涌现着旺盛的生命力。他随和大度,乐于帮助年轻人,不断地为当代艺术开辟新空间,也热心操办各种集体活动,因而在成都一向享有很高的声望。
在艺术家圈子里,春芽算得上是个生活习惯很好的人,不吸烟,不饮酒,喜欢喝茶,读画读帖之余经常四处游历,朋友很多。他结了三次婚,画面上的符号也一直在变化。为追求完美,他不断变化,因为自信,他也不怕变化。多年以来,一系列的作品充分说明,他内在的一切始终都是非常稳定的。
春芽其实不是个爱赶时髦的人,他的艺术风格经常与圈子里流行的时尚有着不小的距离。在同龄人中,他很早就有机会出国留学,但完成学业后马上就返回家乡,没有留在国外。他很早就见识了西方最新潮的艺术样式,但没有盲目跟风。装置盛行的时候,他固守绘画;前卫鼓噪的时候,他学习古典;题材至上的时候,他钻研形式;波普风靡的时候,他用挥洒和涂抹坚持自己的表现……
谈到坚守绘画的态度时,春芽会显得有些认真,他曾说:“绘画的价值在今天这个时代很有局限,绘画本身也变成了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不过,正是因为难,绘画才特别有价值!今天的画家还在用传统的媒介工作,但表现的是当代人的经验,可以表现很刺激的东西,绘画不是很弱,可以很强。当代绘画的流行,对于整个中国的视觉艺术来说,应该是个贡献,是个进步。”
表现主义和写意
“要说的话太多,还不如相对沉默。”——崔健 ②
1986—1988年,春芽赴德国留学,在表现主义、新表现主义的大本营里受到震撼和熏陶的同时,却因一个偶然的机缘唤起了他对祖国传统民乐的强烈共鸣。当时,孤身在德国学习的他,接到国内两个从事民乐演奏的朋友寄来的一盘录音带,他们想托春芽帮忙到欧洲发展。一首古筝演奏的《塞上曲》穿越时空,令他感叹动容,在异国他乡,他听到了属于中国人的特殊情感,感受到了心灵中某种强大的东西被激发起来。于是,他写了一封长信劝那两位朋友不要来欧洲了,身在国外,他却更清晰地发现了自己的精神故乡,知道了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1989年1月,春芽回国后先到了北京,看到了大家热火朝天地忙着筹备现代艺术大展的气氛,没等展览开幕,他就坐火车返回成都,在秦岭那漫长的隧道里,迎面开来的另一列火车正载着四川的一大帮朋友与他擦肩而过。
其实,春芽在德国的时候早已见识了装置、行为、录像和摄影的能量,但他最钟爱的却仍然是油画,回国后,在见证了“85新潮”谢幕礼的同时,他也遭遇了1990年代初大陆现代艺术最为沉寂的年代。那个时候,他买了“元四家”、“明四家”、“四僧”、“四王”以及黄宾虹等大师的画册,开始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到对中国传统文人画的深入体验和潜心研究中去了。与此同时,延续着在德国听《塞上曲》的感觉,他开始系统地感受和认识中国古典音乐:古琴、古筝、琵琶……《寒鸦戏水》、《高山流水》、《出水莲》、《秦桑曲》、《渔舟唱晚》……
在德国学习的时候,他见识过以基弗、巴塞利兹等人为代表的新表现主义艺术的巅峰状态,当时就觉得那是一种表现内心现实的语言,非常直接,也非常真实,与过去接受的程式化学院教育相比,他为那种炽烈的真实而心动不已。但是,春芽没有立刻模仿那种属于他人的语言,而是把对真实表达的向往深藏于心。
1990年代初,在开始对传统国画的研究之后,王蒙、八大山人和黄宾虹的风格都令他心驰神往,中国传统水墨艺术所呈现出的广博大气与细腻精微,在那些大师的笔下近乎完美地融为一体。笔墨方面,那已经是难以企及的写意经典,在叹为观止的同时,春芽似乎看到了用油画再现那种辉煌的可能。
“表现主义”和“写意”,这两种来自不同时空的文化概念,在春芽的油画作品上看似偶然却顺理成章地会面了,这样的会面,造就了他延续至今的一系列作品,更确切地说,造就了春芽的独特语法。
语言和语法
“章法屡改,笔墨不移。不移者精神,而屡改者面貌耳。”——黄宾虹 ③
语言和语法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多年来困扰中国当代艺术的问题。
由于视觉艺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一直被当作政治宣传的工具,中国大陆的艺术家们至今都很难摆脱“主题创作”的情结,在意识形态化和商业化的双重压迫下,内容大于形式的作品相当得宠,语言大于语法的现象无人质疑,“画什么”似乎永远比“怎样画”重要得多。如今,连许多有名的艺术家都不清楚语言和语法孰轻孰重,甚至在创作中严重倒置着二者的关系。
语言,其实并不是很重要,一个艺术家的语言往往有很强的阶段性,正如黄宾虹把“章法”和“笔墨”比喻成“精神”和“面貌”的关系一样,语言本身其实也只是被表达对象最表面的外壳而已。艺术语言可以通过学习来获得,也是可以被引用、借用和戏仿的。
语法,是艺术表达最稳定的内核,是创造者一以贯之的表达方式,是代表艺术家个性最充分的证据。一个成熟艺术家的语法应该有相当大的难度,有独特的神秘感,甚至有生而知之般的天赋特征。有了稳定而极富个性的语法,用任何语言表现任何言说对象,都不会有问题了。
1980年代初,在春芽步入其创作年代的早期,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新印象主义(点彩派)和野兽派都曾经是他着意模仿的对象,在他当时所描绘的色彩异常强烈的西藏风景中,来自高更和西涅克等人的影响显而易见。在1990年代中期,他所描绘的“黑根一家系列”基本成型时,作品中仍然有德国表现主义的影子,但借助学习和模仿,春芽最终调和了来自西方的表现主义和中国传统水墨艺术的写意手法,开创了个人风格,把最初借用的语言融会贯通,成就了自身的语法。值得注意的是,与不少尝试直接用油画工具材料画水墨的艺术家们不同,春芽原本并没有接受国画训练,他的表达仍然归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油画体系。
春芽的语法是自然流露的,是恣肆奔放的,是充满生命活力的。平时,他有和朋友们一起吃饭喝茶聊天的习惯,嘻嘻哈哈,淡定轻松,一旦进入工作状态,便闭门谢客,独自一人面对画布,精神上剑拔弩张,容不得半点干扰,哪怕是巨幅作品,也必定要一气呵成。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气息连贯,神采飞扬,笔笔相扣,淋漓酣畅。如果用中国水墨画的标准来衡量的话,春芽的许多作品已经达到了气韵灵动,张驰有度,笔法、墨法、章法俱佳的境界。
山石、红人、绿狗、桃花
“夫画,天下变通之大法也,山川形势之精英也,古今造物之陶冶也,阴阳气度之流行也,借笔墨以写天地万物而陶泳乎我也。”——石涛 ④
石涛的这句话,是论说“无法之法”时发出的一声感慨,在他看来,艺术无非是借用笔墨形式表现天地万物的形象,万变不离其宗的目的是“陶泳乎我也”。这是中国古代画论中少见的直接有效的说法,比倪瓒的“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 ⑤更进一步,石涛把“法”上升到第一位,“笔墨”和“天地万物”也只是借用的对象而已。曾经困扰视觉艺术界多年的题材与形式之争,在这样的大智慧面前就显得很无聊了。
从“山石”到“桃花”,这些依次排列并相互交叉的外在艺术符号看似毫无联系,却说明着近20年来周春芽作品内在脉络的演变轨迹。对于春芽来说,作品中所表现的对象有时属于刻意选择,有时则是因缘际会,题材对他来说不是绝对重要,他十几年来一以贯之的个性表达才是最重要的,在1990年代中期,他的语法已经基本成型,符号、题材、内容……已经不是他最重要的考虑对象。
1990年代初,为了磨练画面肌理和构成趣味,春芽开始以一组表现山石的作品入手,发掘蕴藏在这种半抽象形态中的审美特征,为此,他曾多次驾车奔赴四川盆地周围的山区观察石头的形态。2000年前后,去苏州和扬州的数次旅行,又使他对太湖石的形象产生了浓烈的兴趣,他甚至认为:“太湖石以其历史感、坚硬、浑厚、复杂、恐怖、血腥和优美为一体,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物体”。不久,一组组红色的男女人体在山石所搭建的舞台上登场了,他们以最原始、最本能的肢体语言坦荡直白地表演着性与爱纠缠交织的图景,画面上散发出浓烈的欲望气息。其实,对太湖石的欣赏品评,历来是中国园林艺术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文人皇帝宋徽宗甚至因为极度痴迷于“花石冈”而最终亡了国。春芽那绵延了十几年的石头系列,其实是以形式实验的朴素动机为开端的,新千年到来之际,这种实验却成就了他在民族美学的语境下确认自我身份的语法。
尽管春芽曾解释说“绿狗的出现是一个偶然”,但那个名叫“黑根”的德国狼犬却成为自1995年之后近10年之间春芽作品中最重要的题材。出现在他作品中的“黑根”展现出了比人类更直接,更缺少矫饰和伪装的天然生命状态,一举一动中表露出的情感令人熟悉而又惊奇,春芽也乘势把所有的喜悦、愤怒、顽皮、郁闷都假借“黑根”的形体动作倾泻挥洒而出。“绿狗”与“山石”和“红人”不同,春芽在这个系列中是以近似传统文人画的方式来对待“黑根”这个符号的,在典型的文人画中,山水花鸟都是非常程式化的符号,但古代文人们却在对某种单一形象长久反复的歌咏描绘中,表现出了形式语言最朴素、最细腻、最微妙、最多变的魅力。今天,我们反观春芽笔下的“绿狗”,亦当作如是观。
桃花的题材,春芽在1990年代末期的作品中已有尝试,但仅仅停留在为快感而试笔的动机上。2005年春,他去成都郊区的龙泉驿踏青时,漫山遍野怒放十里的桃花阵给了他实实在在的震撼。后来,爆炸式的大片桃红色花朵开始次第绽放在画布上,笔触暴力而格调温情。可能绝大多数人都会把春芽作品中的桃花叙事理解成在“桃花源”里交了“桃花运”并邂逅了“人面桃花”的情节,但他们往往会忽略另外一个重要事实:桃花是艳丽的,却也是脆弱的,短暂的花期瞬息即逝,绿肥红瘦之后,令人徒发伤春之感慨,并喟叹人生之须臾。已经“知天命”的春芽,在面对人生季节的转换时把激情交欢的“红人”们画在桃花树下,在寓意“人生得意须尽欢”的同时,也显示着古代春宫中“花下做鬼亦风流”的潇洒,已故香港著名音乐人黄霑先生的一句歌词恐怕最能说明这种心境:“跟有情人,做快乐事,别问是劫是缘” ⑥。
生命意识和文人审美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东风。”——崔护 ⑦
文人画最终没落的缘由相当复杂。一方面,是由于长久封闭的国门被外国列强的坚船利炮敲开,西学东渐之风盛行,国人膜拜进化论,不以国粹为荣的现象使然,但这终究是外部原因;另一方面,文人艺术自身的单调与重复,在从北宋至清末的近千年历程中锐意进取逐步减少,创造逐渐变为程式,古雅最终流于枯淡,缺乏昂扬勃发的生命意识,却也是内在的事实。
经历了多年对文人艺术的潜心研究,春芽始终对传统充满敬意,他认为传统代表着完美,但当代人仍然可以从另类的角度从传统中汲取养分并开创自己的风貌。在借鉴传统的同时,他在创作中一直不自觉地流露出对生命意识的持续追寻,从他对作品中符号的选择,就可以看出这种处处洋溢着激情的性格脉络,生命的原始冲动,在从“山石”到“桃花”的漫长旅程中始终闪耀着欲望的光芒,朴拙、淋漓、鲜艳而刺激——这便是春芽独特的语法。
然而,在这直接而放浪的表象下,春芽的系列作品里却持续透露出一个敏感心灵对传统中国文人审美的虔诚礼赞——刺目的色彩,时时追随着审慎的造型,迅疾的用笔,每每保持了沉着的节制。山石的表面、红人的轮廓、绿狗的造型、桃花的姿态,既隐藏着丰富的质感和肌理,又浮现出率真的构思和技艺。
近年来,春芽常常以惊人的勇气对自己的画面发起一轮又一轮挑战,向观看者们展示出他对色彩和造型成熟的把握能力。在“桃花”系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把水墨艺术的意蕴成功地运用到当代油画的意象之中,这已经不再是工具与材料的简单转换,而是性格和气质的内在生长。尽管用色的冶艳和下笔的爽利仍然是春芽被公认的最具标志性的语言,但其背后的语法已经开始呈现出文人审美的浑厚张力,即使不借助任何标志性的古典主义文化符号,他作品中轻松飘逸而又极富诗情的东方意味仍然给人以深刻印象。除了画画之外,春芽也开始尝试着把绿狗做成雕塑,把太湖石造成房子,在物质材料的切换过程中,他再次充分地显露出平淡天真、率性而为的幽默感,无论是对质感的把握还是对空间的经营,都证明着春芽式的语法在不同艺术品种中生机勃勃的成长。
文人画的高峰,已经随时代的流转而渐渐远去,但文人式的审美意识,仍然在当代人那充满生命力的语法中盎然延续。桃花漫天,碧空如洗,春芽正用独特的话语续写着当代艺术的传奇。
李旭 2006年11月1日写于上海忻康里
【编辑:虹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