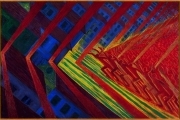布鲁斯·瑙曼(Bruce Nauman)能让那些不待见当代艺术的人连翻好几个白眼。随手一翻他暗黑的目录,不难看到这样的作品:打翻的咖啡、往空走廊里吹气的工业用风扇、背面刻着一个秘密的钢板、造型扭曲的长条霓虹灯、艺术家往自己睾丸上涂抹黑色颜料的录像截屏。这些作品仿佛出自一个怪人之手,沉醉在自我的艺术世界中无法自拔,开了一个又一个谈不上任何美感的恶劣玩笑;然而,在看似简单的表象之下,解读瑙曼的作品别具挑战——听听艺术家在1973年的一幅平板印刷作品中的怒吼,他用镜像的全大写字母写道:“衰人请注意。”(PAY ATTENTION MOTHERFUCKERS)
“布鲁斯·瑙曼打开了太多可能性,”凯西·哈尔布里希(Kathy Halbreich)评价道。哈尔布里希带领团队策划了艺术家的大型回顾展“布鲁斯·瑙曼:消失的行为”(Bruce Nauman: Disappearing Acts),继瑞士巴塞尔的 Schaulager 美术馆之后,展览近期到达纽约,在 MoMA 与 MoMA PS1 双馆齐齐开幕。“如果你对语言感兴趣,你绕不开瑙曼;如果你对录像感兴趣,你绕不开瑙曼,他是最早使用便携式摄影录像机进行创作的艺术家之一;如果你对新技术感兴趣,你同样绕不开瑙曼,即使他不是史上第一人,至少也是其中先锋;早在‘行为艺术’一词出现之前,瑙曼就深谙行为艺术之道了。” 哈尔布里希介绍道。同时,策展人还指出,瑙曼的涉猎甚至触及极其小众的媒介。“我至今认为,瑙曼的全息影像是这类媒材的创作中唯一值得一看的。”
布鲁斯·瑙曼,《人类本性/生命死亡/知道不知道》(Human Nature/Life Death/Knows Doesn’t Know),1983。 © 2018布鲁斯·瑙曼/艺术家权益协会(ARS),纽约。图片致谢: ©博物馆协会/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
正如塞缪尔·贝克特在戏剧《等待戈多》中刻画了两个角色对造物主的等待,瑙曼也常常在作品中探索人们如何无所事事地等待着“意义”的到来。(哈尔布里希写道:“生命就像是等待顿悟的过程,而顿悟可不会天天报到。”)某些情况下,获取答案的方法不过是审查自己的身体或者工作室的角落和墙壁。追寻确定性是一个美丽、奇异、充满敬畏的过程,最终的结果将是注定的失败——艺术家们恰巧都享受这个过程,也在瑙曼逾五十年的创作生涯中长久回荡。过去五十载,人类的原始冲动(以及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产物)带领瑙曼广泛涉猎各种材料和媒介,进行艺术实验,也使他成为了美国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
在哈尔布里希看来,瑙曼对世界的贡献远超艺术领域——他教导着人们“该如何去生活。”1979年,为了躲避艺界尘嚣,瑙曼搬到了新墨西哥州小城佩科斯(Pecos)。1989年,他又搬到了一个位于加利斯特(Galisteo)的偏僻牧场,今天依然跟同为艺术家的夫人苏珊·罗森伯(Susan Rothenberg)生活在此处。在这处地产上,瑙曼的生活与创作无缝衔接:他曾拍过一个自己反复骑马绕场的录像;还拍过一个建篱笆的录像,影片末尾,一个邻居走了过来,对艺术家的建造成果指指点点。
布鲁斯·瑙曼于新墨西哥州的工作室。摄影:Jason Schmidt。图片致谢摄影师
“对瑙曼来说,好的作品融汇着一日劳动的工作成果,这个概念至关重要,”哈尔布里希介绍道。策展人认为,瑙曼对寻常世界的持续探索让他不为“观念艺术家”这一标签所局限——即便他切切实实把艺术从实物中解放了出来。瑙曼身兼多重身份:雕塑家、表演家、后极简主义者、光艺术家、画家、摄影师、动态影像艺术家……自1960年代起,瑙曼运用并革新了上述所有媒材。在他极度活跃又变幻无常的艺术实践中,意义又何从而来呢?
1960年代,二十来岁的瑙曼就读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他当时正在经历重大的创意瓶颈。据艺术家回忆,直到自己意识到工作室中的一切发生都能被归入“艺术”,创意瘫痪顺利解除——创造艺术的过程变成了艺术本身。瑙曼拍下了自己在工作室里四处移动的录像:他调整或检视着各种材料,来回走动,盖印章,朝着一个墙角撞击,将肢体以各种形态冲突或依附于墙体、形成一座座雕塑……“创意瓶颈之于瑙曼,就像画布上的丙烯底涂料之于画师;作为艺术家,那就是你的起点,”艺评人彼得·普拉根斯(Peter Plagens)曾经如是评价瑙曼。瑙曼把创作中的困惑变成了主题和素材。
瑙曼的录像极度日常、几近平庸,但他深陷其中,将其定义为“对时间的结构化处理”;录像不断演化,后来发展出了引导观众的说明书。《身体压力》(Body Pressure, 1974)便是这样一幅指南海报:要求观众用身体“非常用力地”挤压墙壁,并想象一个复制人在墙的对面同等大力地施加反作用力。这种跟自己的臆想化结合是某种情欲化邀约——感受你跟周遭空间的联系,跟自我身体的联系。(在指南尾部分,瑙曼警告道:“这个练习很可能会唤起性欲。”)遁入想象空间之前,观众-行动者有必要联想一番瑙曼多年前创作的《带照明的表演盒子》(Lighted Performance Box, 1969):长方形金属盒子跟平均身材的成人大小相仿,鼓励观众看着盒子想象自己在里面表演。装置的灵感来源于瑙曼小时候跟祖父学来的魔术。
“每个伟大的艺术家都是一名魔术师,”哈尔布里希在回顾展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道。瑙曼的魔法路数无常、攻击性强,有时甚至令人不适。瑙曼喜欢摆弄玄虚、喜欢制造迷障来混淆观众的期待,他的冷幽默时常是黑暗的、戏谑的。相关例子不妨参见:1987年创作的四轨道录像,其中的小丑做着各种低俗下作的举动;或一个五指全都是拇指的石膏手模;或一个描绘群交场面的霓虹灯箱——闪烁的灯光描刻着机械持久的抽动。
布鲁斯·瑙曼,《全是拇指》(All Tumbs),1996。© 2018布鲁斯·瑙曼/艺术家权益协会(ARS), 纽约。图片致谢艺术家及纽约 Sperone Westwater 画廊
布鲁斯·瑙曼,《七个小人》(Seven Figures),1985。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
瑙曼钟爱吊诡之物,跟马塞尔·杜尚等20世纪初的前卫艺术家一脉相承,擅长挑衅,爱玩文字游戏。在1967年《ARTnews》杂志的一篇采访中,瑙曼承认道:“我估计,我的作品一定跟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有着某种联系。”如果说这两个流派专注于暴露人类本性的混乱成分,瑙曼则聚焦于消解语言的肯定性及稳定性——世界上无一语言能够幸免。“当语言开始破裂,刺激就来了,”瑙曼如是说。艺术生涯伊始,瑙曼便在霓虹灯箱、刻字石灰条,以及张牙舞爪的全大写印刷标语中肆意施展着文字游戏。
语言的暴力性也是瑙曼的创作议题之一:字词语句能够轻而易举地扭曲现实、颠倒黑白。人们常识中,符号应具备信息传达的作用——在艺术家手中,它们化作诗意的、残暴的、机智的谜语,混乱了语言的教导意义。瑙曼1972年的作品《逃脱恐惧,乐趣来自背后》(Run from Fear, Fear from Rear)由暧昧的红色和黄色霓虹灯组成,为观众打开开放解读,它佐证着一个事实:只消替换一个字母,意义就会发生剧变。装置影射着人性中令人不安的真相——恐惧带来的情欲,以及个体对彻底丧失底线的顾虑。闪烁的霓虹灯装置《提琴 暴力 安静》(Violins Violence Silence, 1981—1982)关乎冲突和征服,道出文字游戏中邪恶又别具韵律的愉悦感。
布鲁斯·瑙曼,《一百个生与死》(One Hundred Live and Die),1984。© 2018布鲁斯·瑙曼/艺术家权益协会(ARS),纽约。摄影:Dorothy Zeidman。图片致谢艺术家及纽约 Sperone Westwater 画廊
布鲁斯·瑙曼,《我的姓氏在垂直方向上呈十四倍扩张》,1967。© 2018布鲁斯·瑙曼/艺术家权益协会(ARS), 纽约。摄影:Tim Nighswander/Imaging4Art
布鲁斯·瑙曼,《逃脱恐惧,乐趣来自背后》,1972。摄影:Nathan Keay,© MCA Chicago。© 2018布鲁斯·瑙曼/艺术家权益协会(ARS), 纽约
瑙曼对边界及二元观念的破坏正是《七美德/七宗罪》(Seven Virtues, Seven Vices, 1983—1984)的主旨。其中,“忠贞/淫欲”、“希望/嫉妒”、“正义/贪婪”等反义词成对出现在石灰条的表面,互为重叠的设置让每个词语都难以辨认。再一次,词语成了混淆是非之物,丧失了明晰启迪的作用;在一堆纠缠的字母中,观众需要费上一些功夫才能让它们回归秩序。(人们在分解两个词语中获得的快感不言自明:明晰、结构和分类恢复之后让人如释重负。)
语言承诺着可读性,却常常背叛这一承诺,它难以呈现自己的完整本质。在霓虹灯装置《把我的名字写在月球表面》(My Name as Though It Were Written on the Surface of the Moon,1968)中,瑙曼将自己的名字扭曲、拉伸;《我的姓氏在垂直方向上呈十四倍扩张》(My Last Name Exaggerated Fourteen Times Vertically)同样运用了对签名的抽象化处理:蜿蜒的霓虹条跟医院仪器上的心率图有些相似。在这些作品中,艺术家不仅拒绝接受对身份的固化演绎,也隐喻着艺术家签名的脆弱性——这一符号恰恰是艺术世界对价值和作者性的认证。
艺术史传统趋于把艺术家包装成英雄伟人,瑙曼对此呈忤逆之态。“用对立式平衡的姿态走路”(Walk with Contrapposto)系列启动于1968年,其中,艺术家在工作室里别扭地踱步:一侧的胯部向前移动,另一侧的腿往后延伸,模仿着希腊雕塑中(不合常理的)理想男子形象。2017年,瑙曼对这个系列进行了重新演绎:透过3D眼镜,观众将看到年逾古稀的艺术家再次用相同方式艰难移动。屏幕从中间断开,艺术家上身和下肢分别运动,进一步凸显了不协调的姿势。在两块节奏错置的屏幕中,瑙曼的步态格外松垮,带有讨喜的“非艺术性”,他那笨手笨脚的牛仔形象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布鲁斯·瑙曼,《对立式平衡研究》,2015/2016。© 2018布鲁斯·瑙曼/艺术家权益协会(ARS),纽约。图片致谢艺术家及纽约 Sperone Westwater 画廊
通过《绿马》(Green Horses,1988)一作,瑙曼似乎有意打破神秘的“牛仔附体”,效果却适得其反。在这部将近一个小时录像中,艺术家策马穿梭在旷野。戴着宽沿帽的瑙曼看起来十足像一个牛仔,重复的动态让“西部”的背景叙事呼之欲出。图像不时翻转,人马位置互换,空中搅动的马腿成了画面中心。跟瑙曼的镜像字符系列有所类似,这个简单的翻转动作正是作品的关键之一,其意义在于,在艺术跟前,现实做出了小小的“让步”;在此,有必要援引艺术家本人关于倾斜镜头的解释——“这样一来,看起来我对(现实)施加了作用,并使其发生了改变。”
《绿马》或许也论述了每日劳动的道德价值,这部作品的中心思想是谦逊,而非描绘英伟的艺术家形象;此外,它还强调了马匹作用于骑手的奇技淫巧。瑙曼向来亲近动物,在创作生涯中时有涉猎这一主题,相关作品包括:各种鼠类录像;以及看着就肉疼的《旋转木马(不锈钢版本)》【Carousel (Stainless Steel Version),1988】——钢结构支架拖着几只发泡胶材质动物在地面打转。
布鲁斯·瑙曼录像《绿马》截屏,1988。© 2018布鲁斯·瑙曼/艺术家权益协会(ARS), 纽约。摄影:Ron Amstutz
布鲁斯·瑙曼,《旋转木马(不锈钢版本)》,1988。© 2018布鲁斯·瑙曼/艺术家权益协会(ARS),纽约。图片致谢匹兹堡卡耐基美术馆
行为作品《放过土地》(Leave the Land Alone, 1969/2009)同样传达着瑙曼对自然的敬畏,艺术家用飞机拉烟在空中写下了题中标语。有人认为,这件作品影射了瑙曼对大地艺术家的批判,后者的创作方法便是在土地上(强行)留下印记。关于该作品的解读,哈尔布里希在展览目录中写道,它更像是“一道不要糟蹋地球的命令”。瑙曼的创作议题涵盖种族、性别、艺术史,他为多元解读留足了空间,虽然冲突不可避免,但永远乐趣无穷。
展览目录的作者之一,艺术家/艺评人尼古拉斯·圭格尼(Nicolas Guagnini)对瑙曼的《黑球》(Black Balls, 1969)进行了深度剖析。这件便是前文提及的录像——艺术家往自己的睾丸上涂抹黑色颜料。圭格尼认为这是一件抽象表现主义之作,透露着关于种族的焦虑,以及艺术家作为白人男性的弱势感。在《Artforum》杂志中,另一位艺术家亚库比·夏特怀特(Jacolby Satterwhite)解析道:“艺术家对自己平庸的白人男性身体发出拷问——其尺度、其身份、其与艺术家生活周遭的关系。”
自我身体以及身体对空间的占据是瑙曼的长期关注,然而,瑙曼对让自己的身体彻底消逝也有一种奇特的偏爱,回顾展中的数件作品都探索了这一主题:艺术家本人的四肢和头骨石膏模——带着用膝盖印出来的空腔;脑袋石膏模——上面有一条裂缝;抵在头骨和肩膀之间的胳膊呈自我消解的姿态——表达着瑙曼对自我肯定的拒绝。
布鲁斯·瑙曼,《五位著名艺术家的膝盖蜡模》(Wax Impressions of the Knees of Five Famous Artists),1966。© 2018布鲁斯·瑙曼/艺术家权益协会(ARS),纽约。摄影:Ben Blackwell
然而,在另一些作品中,瑙曼的禅意特质被偏执和焦虑抵消。在声音作品《滚出我的思维,滚出这个房间》(Get Out of My Mind,Get Out of This Room,1968)中,带有喜剧色彩的神经质呼吸声冲荡着空房间,绝望的命令语句间歇出现。1994年的作品《双层钢笼》(Double Steel Cage Piece)称得上是幽闭恐惧症患者的噩梦,在众目睽睽之下,体验者可以走进笼子并穿越其中的狭窄过道。瑙曼的好几件空间装置都萦绕着类似的氛围,使被束缚的身体曝光在窥阴癖视角之下,让人分外难受。《卡塞尔走廊:椭圆空间》(Kassel Corridor: Elliptical Space,1972)由两堵弯曲的墙体组成,中间留有一条小走廊:如果想体验这件作品,观众需要问工作人员寻取钥匙(与此同时,走廊两端的观众可以围观其中体验者艰难的行走过程)。作品《走廊装置(尼克·怀尔德装置)》【Corridor Installation (Nick Wilder Installtion), 1970】含有若干条走廊,观众于一条走廊中的影像将被监控捕捉,并在其他走廊中播放,被偷拍了的人对此并不知悉——通过剥夺人类对自我影像形式的控制权,作品激发出层层的焦虑。
在瑙曼的理解中,国家和政府监控显然不是导致存在焦虑的单一原因,个体的力量也不可小觑。圭格尼在瑙曼更为喧闹激烈的作品中看到了跟监控工具同样黑暗的人性,他将其描述为“暗黑轴心”,并写道:“这种风格后来由保罗·麦卡锡(Paul MaCarthy)和麦克·凯利(Mike Kelley)发扬光大:低俗、性、重复、死亡。” 不妨带着圭格尼的解析看看瑙曼的四频道录像作品《小丑折磨》(Clown Torture,1987):小丑们在封闭空间中作出污秽幼稚的举动——坐在马桶上、在地上撒泼打滚、尝试把什么东西粘到天花板上。至于标题中的“折磨”的承受方,很难判定到底是录像中的沉迷邪恶无法自拔的小丑,还是现场观众。不管答案为何,瑙曼准确提炼出了所有人内心深处的变态和原始性。
布鲁斯·瑙曼,《双层钢笼》,1974。© 2018布鲁斯·瑙曼/艺术家权益协会(ARS),纽约。摄影:Jannes Linders,鹿特丹
布鲁斯·瑙曼走廊装置(尼克·怀尔德),1970。© 2018布鲁斯·瑙曼/艺术家权益协会(ARS),纽约。图片致谢 Friedrich Christian Flick Collection I Hamburger Bahnhof,柏林
通览上文提及的所有作品,将它们联系起来的纽带是瑙曼对人类心理和经验极限的不断挑战,艺术的极限也由此被不断刷新。“近观瑙曼的作品、深究其中议题,你将感受到追寻自由的强大力量,这就是艺术家如此重要的原因,” 哈尔布里希说道。这样看来,追寻自由的过程必定充满艰难困苦:失败、不确定性、劳役、道德困境——想要追寻自由,你不能逃避,而是要心甘情愿地朝它们走去。